有一个好的“故事核”,才能写出生活的质感 ——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许廷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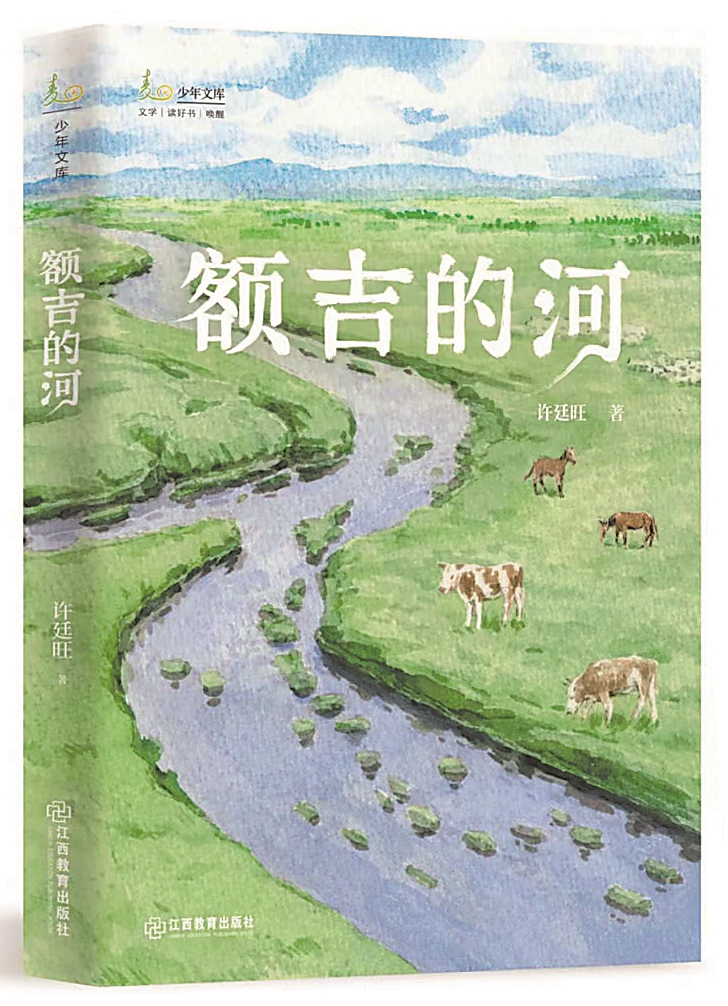
《额吉的河》,许廷旺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24年9月
记 者:许老师好,祝贺您的长篇小说《额吉的河》获得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翻开这本书,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目录很特别。上中下部每一章节都用一句话作为小标题,连缀在一起,像一首诗、一篇散文,也像一段生动的故事。“额吉”与“河”这两个关键词反复出现多次,或可视为作品的“题眼”。这样的艺术处理背后有何深意?
许廷旺:“额吉”与“河”既是作品中描述的人物形象、自然风景,更是一种意象。玉萍的妈妈顾医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经常带着三个孩子去弄堂附近的小河,希望有人收养他们。她坚信小河把这个消息带走了,坚信在陌生之地有人收养三个孩子。天下的河是相通的。玉萍做了马背上的医生,夜诊回来,看到家附近的小河,联想到弄堂附近的小河,这条小河从南流到北,从上海流到几千里外的内蒙古大草原,印证了妈妈的想法:母爱如河,源远流长。“额吉”既代表着亲人对孩子的关爱,如宝力皋、银花夫妇和另外两对夫妇;也代表着社会层面对孩子的关爱,如苏木达、阿力玛老师;更代表着国家层面对孩子的关爱,如旗长。旗长这一形象只出现了两次,却起着“点睛”作用。关于小标题的设计,感谢你读得很仔细,也符合了我和编辑的初衷:哪怕在小标题上也应具有文学色彩。
记 者:小说以“三千孤儿入内蒙”的真实历史为创作题材,本身已具有一定的叙事难度。故事主人公是玉萍、玉香、玉山姐弟三人,三个主要角色的人物性格、成长经历和人生轨迹互有交叉、互相嵌套,又为小说情节的铺陈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增添了另一重挑战。您是如何应对这种难度与挑战的呢?
许廷旺: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应该像成人文学那样,既要描写出生活广度,也要有深邃思想,更要有艺术上的追求。不能因为是儿童文学,面对读者是未成年人,自动降低文学水准。最近几年,我的创作一直秉承这一理念。要想达到这一效果,得更注重作品的结构,我往往会采用三条线索:主线索、副线索,在主副线索中暗藏的第三条线索。这样人物性格、成长经历和故事情节互有交叉,互相嵌套,作品就有种厚重感。当下,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品是线型结构、线型情节,不是说这种作品不好,但这不是我所追求的,更不是我想要的。回过头来再说《额吉的河》的结构,它不是简单地分成上、中、下三部分,而是每一部分开篇都有一个1500字左右的情节,这个情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把每部分的最后情节前置。初读可能会有小小的障碍,但读起来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想,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一本百科全书。这部作品的背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怎么写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我来说有较大的难度。尤其是儿童文学面对的主要读者是未成年人,如果处理不好这一背景,就会让小读者产生割裂感、陌生感,甚至有认知上的隔阂。所以,在创作之初,我就采取了历史背景的“虚写”,这种处理方式并不代表没有历史感,而是通过很多细节表现出来。文学作品源于现实生活的再创作,当我们读作品的时候,有时候会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认为作家写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甚至忽略了它是虚构的艺术作品。之所以会有这种错觉,原因很简单,就是细节起着作用。细节描写越细致、越逼真,故事情节也就越真实。就《额吉的河》来说,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记 者:此前,我常常能在与“三千孤儿入内蒙”有关的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中,读到内蒙古牧民为养育“国家的孩子”付出的辛劳与汗水,为以民族大爱回报“国”与“家”的历史佳话而感动。但《额吉的河》让我读到了另一种视角,那就是这些孩子们复杂而幽微的心理活动。您为何选择以孩子的“负面情绪”作为展开叙事的切入点?
许廷旺:无论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最吸引读者的首先需要有一个“好故事”。成熟的作家不仅仅要写故事情节,还要写到自然风光、民风民俗、文化历史,更要写出人物表达情感的方式等等。确切地说,一部作品要有一个好的“故事核”,这样才能写出生活的质感,写出人的精神特质,也就是文学的特质。我在做阅读推广时,曾有小读者提问:是否可以把人物的性格设计成活泼、可爱,以幽默、风趣的情节切入?我回答说,这是另一个故事,或是另一个类型的故事,不是我想写的。显然,以孩子的“负面情绪”作为叙事的切入点,基本确定了故事情节的走向,与前面我说的有个好的“故事核”是完全一致的,也是确定作品方向的一个关键因素。另外,以这一点切入的叙事,也更具有故事性,能让我塑造的人物形象、性格更具有张力。
记 者:我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期待总是阳光与温暖的,在读到姐弟三人两次失去父母至亲的时候,觉得实在太过残酷和沉重,由衷地希望银花和宝力皋夫妇能够健康长寿地陪伴他们直到长大成人。您认为,作家应该怎样面对和处理所谓的“禁忌”书写?
许廷旺:儿童文学发展到今天,就叙事方式来说,用“千姿百态”形容,一点儿不为过。我也曾创作过轻松、幽默的儿童文学作品,后来我的创作逐渐转型,创作内容大多是凝重的,或者说有凝重的倾向,自然风格也就显得凝重。曾有编辑开诚布公地给我提出这一问题:话题沉重。我不否认,或许每个作家追求不一样,我更适合具有沉重感的创作。既然有了这种选择,像“死亡”“疾病”这些敏感话题是无法回避的。就像成人文学有两大永恒主题:爱情与生命,既然写到“生命”主题,死亡、疾病就是绕不开的。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有很大区别,如何让小读者从心理上易于接受,往往更考验作家的写作水平、技巧。同时,还要考虑作品的内容,既要有利于人物形象的成长,也要考虑读者心理承受能力。
记 者:小说的结尾,玉萍已从上海都市的孤儿成长为内蒙古草原上“马背上的医生”,可以说,她的成长链条很完整。不过,您并没有给玉香、玉山写一个明确的结局,“留白”给读者带来了想象的空间,也让他们的成长处于“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这是为什么?
许廷旺:玉萍来到草原半年后,与妹妹、弟弟重聚于一个家庭;6年后,三个孩子成为地地道道的草原孩子;又两年后,玉萍成长为“马背上的医生”,这是玉萍的闭环成长。但故事中玉香、玉山的成长是留白的,是希望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少年的成长永远在路上。成长的“进行时”恰是成长小说的特点:孩子的成长处于进行时,成年人的成长也处于进行时,比如《德伯家的苔丝》《嘉莉妹妹》《简·爱》等作品,写的就是成年人的成长。当然,这都是成人文学作品,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但《额吉的河》中,孩子与成人都在故事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不断成长,这种成长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的;既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孩子与成人彼此搀扶,共同从“稚嫩”走向“成熟”。
记 者:草原是您特别偏爱的题材,《男孩与草原雕》《送绝影回家》《最后的木屋》《雕花的马鞍》等作品都围绕草原与少年的故事展开。与此前的作品相比,《额吉的河》作为儿童文学主题创作,显得较为特殊。近年间,主题类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盛行不衰,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您认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主题创作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许廷旺:确实,近年来主题类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很盛行。如果在创作上把握得好,坚持得好,是件好事。但如果创作直奔“主题”去,忽视了作品的“文学”性,最终创作之路会越走越窄,内容也必将越来越乏味。换句话说,主题出版考验的是作家。作家面对主题类创作,尤其是对一个成熟作家来说,一定要坚持创作理念,坚持艺术追求——首先它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时,还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被流行裹挟,泥沙倶下,最终被湮没。
《额吉的河》出版后,被认为是主题创作,我不反对。但在我的脑海里,压根就没有“主题”这一想法。我的创作规律和走向,都是沿着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这一既朴实又具有高度的准则来创作的。哪怕是具有主题性的话,比如“国家的孩子”,在书稿中都没有出现。
说到这里,我还想简单谈谈主题创作背景的处理问题。有人读《额吉的河》,就提到了作品背景的缺失。我想以海明威和陀思托耶夫斯基为例。海明威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战争为背景的,他做过战地记者,如果在创作中写战争,没有谁比他写得更详尽。遗憾的是,他却只字未提。当初,编辑看书稿,如果他不说明,编辑对故事发生的背景也感到一头雾水。今天,我们读他的作品,如果不借助资料,很难把握作品的准确历史背景,但这并不影响读者认为那是好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背景是1861年俄国宣布废除农奴制,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普通人纷纷涌进彼得堡。但陀翁却惜墨如金,只借助了一个次要人物的一句话点明背景,而且还是译者加了注释,才让读者了解的。从这两位作家的创作看,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可以虚化、弱化。从事主题创作的作家,要牢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