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文艺》2025年第3期|温新阶:土榨坊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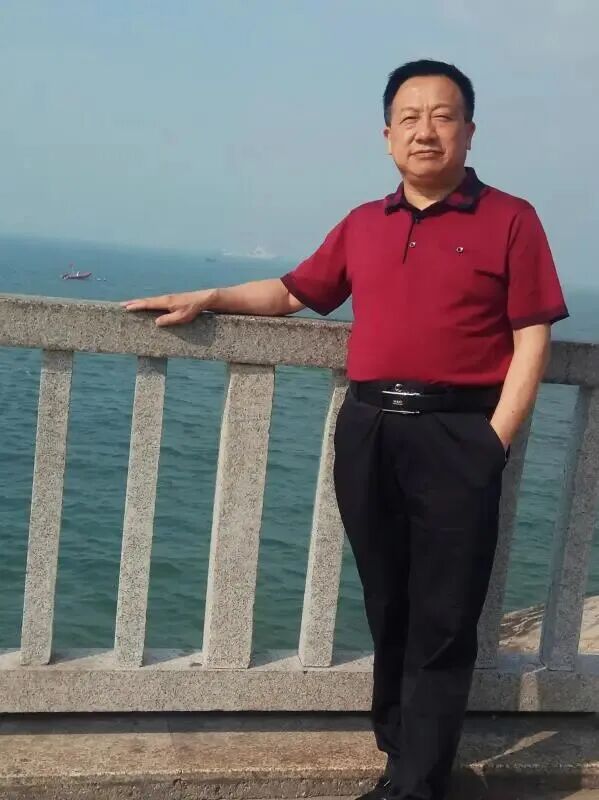
温新阶,湖北长阳人,土家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宜昌市散文学会会长,宜昌市文化名家。出版散文集、小说集多部,有多篇散文、小说被《小说月报》《散文选刊》《北京文学》《作品》《读者》《中外文摘》等刊物选载,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湖北省屈原文艺奖等多种奖项。
土榨坊的岁月
文 | 温新阶
我在璞岭陈家湾醒来,曙色依稀。
这里鸟的叫声跟城里不同,没有拘谨,没有心猿意马,叫是因为想叫,想叫就不要犹豫不决。雄鸟的求偶声,更是酣畅淋漓,一遍一遍,重章叠句。雌鸟张不开翅膀,双脚立在栎树的树枝上有些摇晃。
越清澈的水,水声越是清脆,没有杂质,如纯铜的钵镲,音色纯正悠远。水边有水车,木制的,有了些年头,浸泡得沉重,转动的声音厚实缠绵。不需要用水车提升水位,橡胶水管,就是一条可以胡乱折叠盘桓的水渠,上下起伏,随心所欲,水车不过是一个点缀,一个怀旧的符号,在过分安静的村庄里,一个动态的标志。
翠绿的白菜,匍匐在田垄上,这是我最爱吃的青叶白菜。我不喜欢包成白色的白菜,拒绝了周围的青山绿水,孤芳自赏,鹤立鸡群,甜絮絮的味道不被我的味蕾接收。田垄上有几棵鹅儿肠,细密的圆叶,青色的藤蔓,吸了白菜吃剩的养分,微胖、嫩绿。上好的猪草,现在也被人惦记,洗净,不切,下到腊肉火锅里,腊肉的香味包裹着鹅儿肠淡淡的土腥气,构成颇接地气的美味。
白菜旁边是芫荽、菠菜,还是幼苗,不是真正的乡人还不一定能认出它们来,很多植物幼年跟成熟期长相不一样,印证了世界的丰富多彩。
老屋开门了,门轴在门臼中转动的声音柔和而有起伏,这是我期盼的声音。我们住在儿女们的洋房里,矗立在树林和菜畦之间的洋房,似如穿着狐皮大氅的贵妇人坐到农家火塘里,格外引人注目。老人不住洋房,住在旧房里,虽是土筑瓦盖,也拾掇得个干净整洁,昨天晚上,还去老屋火塘里烤火喝茶,听老人讲璞岭旧事。
肖国政肖老跨出门槛,手里端着一瓢喂鱼的饲料,门口水塘里是他养的鱼,喂鱼是他每天早上必做的功课。还要把羊拉出去拴在长满青草的坝子上看它们大快朵颐,他脸上浮起笑容。
最重要的事是安顿好老伴。老伴张廷秀是上世纪50年代长阳县简师毕业的,那年月,算得上知识分子了。知识修养是最好的化妆品,张廷秀端庄秀丽,气质高雅,是栎树林子里的一棵白杨。却曲曲拐拐地没有在三尺讲台书写人生的卷子,双脚一直在璞岭的土地上奔走,做过村干部,村干部也是农民。同是农民的肖国政个子高挑,丰神俊朗,尤其是脑瓜灵活,手脚勤快,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按东北人的说法,肖老特稀罕张廷秀。年轻时宠着,现在病了,更是疼着。热好牛奶,准备好早餐,还要给她泡一罐热茶。张廷秀爱茶,爱喝茶,爱侍弄茶。我们昨天在老屋的火塘里听肖老讲人生往事,她在小孩子写字的磁性写字板上写了一句话:人要是不生病该多好,我的茶叶可以卖万把块钱。女儿肖远翠老师把磁性写字板拿给我们,一个生病的人,她的梦还在田畴上,还在茶园里。
安顿好一切,肖老要到榨坊去。榨坊就在他的屋后,原先是生产队集体的。那时,肖老为集体打榨,生产队记工分。后来联产承包,队上的保管室卖了,榨坊也要卖掉,几个人想买,肖老近水楼台,把榨坊买了下来。
没有人记工分了,背菜籽来换油,一斤菜油收一毛五分钱的加工费。一年下来,千把块的毛收入,彼时的乡村,也算高收入了,还有菜饼可以换些零碎小钱,实在换不掉的,是上好的种烟肥料,菜饼养出来的山烟,烟叶子都是香的。
忙时种地,闲时打榨,肖老忙得用辫子搭桥,他乐呵。自己做自己的主,不看别人脸色,只要舍得花力气,种瓜会得瓜,种豆当有豆。肖老不是吝惜力气的人,他贩过木材,种过白肋烟,开过经销店,还是远近闻名的焗匠(鄂西对厨师的称呼),啥能赚钱,他都舍得把力气的网往那撒。有时捞着了大鱼,有时网拉起来,一网白生生的阳光。
自从榨坊买过来,没撒过空网。都说肖老菜籽炒得合适,油香油纯,出油率还高,都来肖老的榨坊换油,不光是璞岭人的菜籽都来了,山下也有人不顾路途遥远把菜籽运到了肖老的榨坊。
不论远近,人来了,都有一杯茶,一匹叶子烟,一年下来,喝了几斤茶,抽了几把叶子烟。肖老不心疼,烟,自己种的,茶,自己煸的。力气上的功夫就不是功夫,人气,人缘,是最值钱的。
肖老炒菜籽灶前的茶罐依然煨着,几把叶子烟依然在梁上吊着。来榨坊的人渐渐少了,打榨时举起撞秆时那悠长而又力敌千钧的吆喝声渐渐变得稀疏,炒蒸菜籽芳香的弥漫也日渐淡薄,房顶瓦缝里很少飘出炊烟了。
商品油摆上了山村店铺的货架,方便,简单,再不用种植本就收入不高的油菜籽。乡村的春日,很少见到金黄的油菜花,春天的味道淡了,像一罐续过几道水的现茶。
榨打得少了,肖老的日子依然有声有色,种地,采茶,养羊,喂猪。儿子姑娘四个人,给他们每人喂一头猪,腊月里,都回家杀年猪。火塘里柴火熊熊,鼎锅里煮的猪肉香气四溢,稻场上,刚杀的猪睡在腰盆口上,杀猪佬把开水浇在猪身上,三个壮汉手执挦毛的刨子“噗噗噗”地刮毛,腰盆蒸腾的热气冒过高高的柿树,然后不见了踪影。杀了猪,再宰羊,每人一只羊腿,今年是前腿,明年换后腿。
肖老坐在李子树下,拆猪大肠上的护肠油。前些年,这护肠油可是好东西,丢两三颗在生锈的锅里,炝炝锅,再煮一锅萝卜白菜,那个香,隔三间屋都闻得到。现在,没人再吃这护肠油,拆下来,给母猪发奶。
吃过杀猪饭,孩子们带着鲜肉走了,剩下的,熏腊肉,那是肖老的事。一块块抹盐腌制,然后挂到火塘里的横梁上,砍来柏树枝生火,柏树枝熏的肉格外香。根根横梁上挂满了猪肉羊肉,总是让人联想到那些年乡镇的食品所。
肖老像一株上了年岁但依然苍劲挺拔的辛夷树,站立在陈家湾,枝叶青翠,繁花灼灼。
一个初冬的深夜,肖老听到汽车的马达声由远及近,最后来到了自己的稻场上,然后熄了火。在外的儿女没说这几天要回来,会是谁呢?
肖老打开了大门,车上下来一个人。
“您就是肖国政肖师傅吧?”来人浓浓的荆州口音。
肖老把他让进火塘里,他说,他打听了好久才打听到肖老这里还有一副土榨,他是来找肖老榨油的,1000斤菜籽就装在车上。
“我是戊寅年生人,榨还在,打不动了。”
“我晓得,您是戊寅年冬月十七出生的,公历就是1939年元月7日了。您虽然八十几岁了,可是您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每年还打一二十个榨。我这几百里寻来,您不好意思打发我走吧。”
肖老是个随和的人,菜籽留下,人也留下。白天跟肖老在炒菜籽的灶里烧洋芋吃,马尔科的洋芋,一碟腌球白,一碟辣椒酱,吃得大汗淋漓,那份舒爽,难以词叙。晚上,肖老才有时间正儿八经烧饭吃,拿出老焗匠的手艺,那饭菜让荆州人开了眼界。
1000斤菜籽,五个榨打了三天,荆州人离开陈家湾时,飘起了雪花。他刚离开,肖老发现他在窗台上多放了几百元钱,肖老连忙打电话说油装错了,要他等一等。肖老叫了邻居骑着摩托车去追赶,在村委会赶上了荆州人,把多给的钱塞给了他。
“这是饭钱哟。”
“我不开馆子,不卖饭菜。”肖老说完,跨上摩托车走了,雪花落了他满头满身……
荆州人来陈家湾打菜油的事一下子传遍璞岭上下,很多人知道卖的商品油有的是化学浸出,即使物理压榨的那菜籽也没有炒没有蒸,压的生菜籽,哪里有土榨榨的油那样醇香哟!
肖老的土榨名声越传越响,我们得到消息稍显缓慢,一听说便慕名而来。
昨晚吃了肖老做的饭菜,喝了邻居家酿制的土酒,然后,听肖老讲故事。火塘里,火光熊熊,一屋人,安安静静,只有肖老抑扬顿挫的声音,间或夹杂着柴禾燃烧时炸裂的响声。
窗外,秋风的手掌拍打着窗玻璃,屋内,暖流充溢着每个角落。
听着故事,就总想着土榨打榨的情景。一种古老的工具和方法将植物种子的精华压榨出来,去烹调生活的滋味,总觉得神奇。土榨榨油在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时光流逝到了明代,土法榨油技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应星在其著作《天工开物》中就记载了楔子式榨油机,这种工具一直延续到电动榨油机问世。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食品的追求,纯天然、无污染的土法榨油重新受到青睐。当然也有所谓的专家为某些油脂加工企业站台,发表文章说土榨榨油达不到卫生标准,对健康不利云云。
于我而言,土榨榨油不单是满足我的物质需求,更是一种精神慰藉,一种文化回甘。小时候,在偏僻的乡村,可以玩耍的地方实在有限,响潭园供销社和榨坊便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尽管榨坊打榨时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巨浪让我有着几分害怕,但又像小孩子放鞭炮,一边是害怕,一边是希冀,在害怕和希冀的交替中,我去榨坊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商品油来了,电动榨油机来了,响潭园榨坊的木榨被一个景区买走了,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像一只没有绳索的气球,在空中漫无目的地飘飞。
也有人来买肖老的木榨,还要他去景区表演打榨,肖老拒绝了。穷得卖家物,这名声肖老背不起。表演,他不会,他只会脚踏实地地本色生活。
感谢肖老,让我可以接续几乎逝去的童趣,可以再次打开昔日乡村的图谱。
渴望见到的东西伸手可及,就有些迫不及待,我早早地起了床,没想到肖老也起得这么早。肖老的早起肯定是因为习惯,应该不是因为激动。
安顿好老伴,肖老往屋后的榨坊走去。只要打榨,他的早餐午餐必定是在炒菜籽的灶上烧洋芋,自在,享受。
86岁的老人,抬头挺胸,走得气宇轩昂,我跟在他身后,右脚赶左脚,勉强跟上他的节奏。走到门口,趁着肖老开锁的当儿,我往后一瞅,覃总一干人也都来了。
一栋土筑瓦盖的房子,原来有楼板的,二楼是面铺,山墙上开了门,轧好的面条用竹竿挑出去插在木架上,在阳光下,麦子的芳香顺风飘逸……
肖老买下这栋房子,他不开面铺,也许为了更好地施展榨油的拳脚,他把楼板揭了,铺楼板的横梁锯了,山墙上的门也封了。偌大一栋房子,都是打榨佬的天下。
生火,是第一件事,干枯的杉毛,还有划篾后剩下的篾簧都是好引火柴。一根火柴就点燃了,干栎柴丢进灶里,就有了呼啦啦燃烧的响声,弥漫的烟雾渐渐散尽,只有灯光照耀下,还有烟尘的分子活跃着。
炒菜籽,是榨油的第一道工序。掌握火候很重要,菜籽炒好了,油香,出油率高。炒嫩了,油不香,炒老了,油会苦。
柴火燃烧,肖老用木铲子翻动菜籽,菜籽跟铁锅摩擦的声音有些粗粒,富有质感,一缕一缕的芳香在榨坊飘散。房子太大,嗅觉的捕捉若断若续。
也许屋里灯不是很亮,也许灯光下的观察不真实,肖老不时撮起一把菜籽走到大门口,用手捻开菜籽,然后凑到鼻子下嗅一嗅,查看火候。
菜籽终于炒好了,肖老熟练地把传动皮带挂上了粉碎机,开始粉碎菜籽。我小时候在响潭园看过打榨,那时没有粉碎机,菜籽是用石碾碾碎的,牛拉着石碾转动,人跟在后面把被碾子挤压到碾槽边缘的菜籽扒拉到碾槽中间,还要随时观察牛的屁股,看见牛屁股往外鼓动,连忙拿了撮箕跟在牛后面行走,把牛拉的屎接住。肖老的榨坊原来也是有石碾的,购置了粉碎机后,嵌在地上的碾槽挖了起来和碾盘一起堆在墙边。
粉碎好的菜籽粉还要加热,用篾片做成的一个半球形的物件覆在放了水的铁锅上。肖老把一张包袱铺在篾片半球上,把菜籽粉均匀地铺在包袱上,灶中栎柴哔哔剥剥地燃烧,洋芋早已烧熟,香气四溢。肖老没有时间食用,放在灶门口保温。
热好了菜籽粉,接下来要踩饼。
踩饼的是张昌军,也是76岁的人了,跟肖老是郎舅。鄂西有谚云:除了栎柴无好火,除了郎舅无好亲。这一对郎舅虽不是亲的,一副榨上搭伙干了几十年。榨还是生产队里的时候,就是他俩打榨,肖老买下了榨坊,老搭档一起邀了过来。几十年的光阴,感情的累积,胜过了亲郎舅。
张昌军一家人都会打榨。两个儿子在小学读书时,每每放学都要到榨坊打一站,时不时会吃到烤得锅巴金黄的洋芋,还吃到过香喷喷的烧板栗。吃着、玩着、看着,就把打榨学会了。一副榨养不活太多的人,肖老和张昌军两人种田养猪喂羊带打榨,可以过个涝有太阳旱有雨的惬意日子,张昌军的两个儿子远走他乡,打工挣钱。
张昌军扫出一块干净的水泥地面,拣了两个铁打的饼箍摞起来,挽了一把糯谷稻草铺进饼箍,肖老把热好的菜籽粉一包袱提起来倒进饼箍里,张昌军又把冒在外面的稻草抈回来盖住菜籽粉,然后用脚使劲踩,每踩一下,身子往下一蹲,踩实的菜饼码在一旁,一个厚重的杂木圆饼压在最上面的菜饼上,防止稻草翘起来。
饼踩完了,开始装榨。张昌军拿起菜饼竖着装进榨穴里,肖老坐在榨对面的一把小木椅上,协助张昌军把菜饼放正,一块紧挨着一块,不留空隙。阳光从肖老背后的窗子照进来,头上、肩上光泽闪烁,他的脸,在阴暗里,真实、果敢,张昌军从还没装饼的榨缝里看过去,这张脸,他看了几十年,从锐气蓬勃到暮年沧桑,虽然皱纹多了,依然充满跟时间抗衡的自信,眼中的光芒似乎更加睿智,可以参透世事的书页。几十年前,他就跟着这位老哥打榨,老哥有技术,有胸怀,有在艰难环境下铺展锦绣的决心和能力。一样的付出,收入一碗水,老哥总是把大半倾倒于他盃中。现在打一个榨400元的工钱,老哥给他开220元,用老哥的电,烧老哥的柴,老哥只得180元。他说,一个粑粑平半分,柴钱电费我们再摊。老哥不依,我落下的菜饼也是钱。他知道,不像几十年前,菜饼是好肥料,现在不同了,商品肥多简单,哪个愿意掏心费力用饼肥哟。张昌军再说,老哥不搭话。
饼装完了,装得严丝合缝。张昌军再看不到老哥的脸了。他把一块块铁桃木的木块卡进榨头没装饼的地方,再塞进几块楔子,铁桃木的楔子头上箍了铁箍,防止被撞杆撞裂。
要打榨了,张昌军手把着吊在房梁上的撞杆,前进几步,按着撞杆尾部,把撞杆头子翘起来,冒过木榨顶端,然后后退,再后退,让撞杆尾部翘起来,接下来,碎步向前,一前一后蓄积起来的重力势能转化为巨大的动能,“咣”的一声,撞杆撞击在木楔上,平时像一头巨狮卧在那一动不动的木榨,随之晃动了一下,然后继续匍匐在泥土之上。张师傅前进、后退、再前进,撞杆一次又一次撞击在木楔上,就听见了菜油滴进了油盆里的淅淅沥沥的声音,亲切,圆润,富有质感,渐渐地金黄的菜油从木榨到油盆形成了一条连绵不断的油线,琥珀般的糊状液体,从油盆中心向四周荡开,浓稠的潮汐只涨不落。
我小时候见过的撞杆比这个更为粗大,牛皮缆绳吊在房梁上,打榨人前进后退,再前进,再后退时借着惯性一股脆劲将撞杆举过头顶,然后一声巨喝,跑步向前,将撞杆重重地撞击在木楔上,排山倒海,天摇地动,菜油滴入油盆的声音有几分畅快,也有几分壮烈。张师傅说,那叫鹞子翻身,我们榨坊过去也打过鹞子翻身,那是一顿吃得完升把米的壮年时代,几百斤的撞杆不要说吊在梁上,就是抱着跑也不在话下,岁月不饶人,现在只玩得动这老鼠子尾巴了。
张师傅现在用的撞杆,一头粗,一头细,细的一段被削成尖锐状,俗称老鼠子尾巴,又叫一炷香,倒是很形象。
一榨油200斤菜籽,打了几个小时,淅淅沥沥的滴油声渐渐变得稀疏,最后归于平静。两颗电灯泡无精打采地垂在那,似乎有了几分睡意。灶里的炭火被白色的灰烬覆盖着,给人一种熄灭了的假象,一堆洋芋躺在灶门口假寐。作为观众的我们将离开观众席,虽然是甲级票,演出告一段落,两位主演示意我们离开,他们将要用膳。用膳的过程不让观瞻,一碟稀辣椒,一盘泡菜,那些烧洋芋匆忙地剥皮,有时并没有剥离干净,就喂进嘴里,这是乡下人吃烧洋芋时的常有情形。在响潭园榨坊里我还见过洋芋的奢侈加工方法。去皮的洋芋开水中煮两开,筲箕沥起,倒进炒菜籽的铁锅里,文火,从油盆里舀来一缸子菜油,翻动洋芋,顺着锅边滴一圈菜油,滋滋的声音和缕缕油香在榨坊萦绕。不一会,再翻动洋芋,再滴油,直到洋芋炕得身体浮肿浑身结满金黄的“痂”为止,那是我见过的最诱人的炕洋芋。我问过肖老,做过这样的炕洋芋没有,他说,跟师傅学打榨时做过,多两撞杆,就有了炕洋芋的油。自从自己执掌榨坊以来,再没有做过一回。能多打几撞杆多滴几滴油,他都让给换菜油的农户,在肖老这里打油,秤旺提子满。
我们的午餐安排在洋房里,约肖老和张师傅一起去吃,他俩坚持不去。吃过他们的烧洋芋午餐,还要把菜饼从榨里卸下来,在粉碎机里粉碎,再蒸热,再踩饼,再榨一道,下午,还有一个榨,夜里才能弄完,他们说后面的跟刚才的工序一样的,叫我们不必再来观看。
我知道,因为我们的观看拍摄,影响了两位师傅的速度,不然,一天两个榨,太阳还没落进山坳,就收工了。肖老就可以去坝子上牵羊,回来还可以和婆婆做一顿可口的饭食,不至于中餐晚餐都要洋房子里的儿女们给母亲送过去。儿女们做饭买的菜多,老人未必吃得心安,未必吃得落肚熨帖。
下午,我们继续去看打榨,是在榨坊外面的窗子里看的,没有了我们的干扰,没有了相机手机的拍照,两位师傅置身于自己的“场”,酣畅淋漓,恣意而行。
肖老一边蒸菜籽粉,一边哼起了山歌:
割草不割蛇茅草
过桥不过独木桥
砍柴不砍夜蒿树
嫁人不嫁打榨佬
单衣油得像皮袄
张师傅张口接了过来:
姐儿爱上打榨的
上顿下顿没油吃
初一说是没开榨
十五油瓶忘了提
只有一身好力气
张师傅一边唱,一边用力往下踩,他的歌唱得很有节奏。
两个人一唱一和,菜籽粉蒸完了,饼也踩完了。
不一会,听到了撞杆撞击木楔沉闷的声音,张师傅的吆喝响亮清脆,充满了力量,甚至有几分野性的张扬和释放。
我们慢慢退了出来,慢慢离开榨坊门口的场坝,穿过那片竹林,回望那栋土筑瓦盖的房子,瓦缝里有缕缕炊烟漏了出来,四周群山逶迤。一栋栋房子散落在群山之间,榨坊,是其中的一栋,有些苍老,有些落魄,跟四周的房舍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但是,它依然顽强地坚持,顽强地挺立,因为有两个老人尤其是肖老似乎还没有感受到人生的苍茫暮色,没感到疲乏,没感到力气总在远处张望的无助,他还有本钱跟时间抗衡。
我们走到老房子的稻场里,又来了两辆皮卡,车上都是装的油菜籽,他们肯定是慕名而来,方圆几百里只有这一副木榨了,越稀少越是会激起人们亲密接触的欲望,越稀少也越是容易找到。这自然是好事,有更多的人能够匍匐到土地之上,去品尝菜籽油最本真的味道,能嗅到来自自然本身的芬芳。而对于肖老和张师傅而言,能够每天诵读纸张已经发黄的书卷上的文字,能够再一次踏上青春跋涉过的道路,那份快乐,只有他们自己懂得。
只是,时光总是无情,有一天,肖老、张师傅以及那副土榨终将逝去,人们对土榨菜籽油眷恋的缆绳将系于何处?
我们离开了陈家湾,离开了璞岭。车上的菜油壶摇摇荡荡,油香一缕一缕沁入心脾,我们身后的莽莽群山,伏在林子之间的榨坊,还有精神矍铄的肖老和张师傅,总是叠印在我们记忆的屏幕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榨上榨下的岁月,不会忘记他们平凡真实却又熠熠生辉的人生!
车越开越远,夕阳,在我们身后的林子里悄然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