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追寻中国乡村精神之变” 孙惠芬长篇小说《紫山》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长篇小说《紫山》研讨会于2025年10月17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国出版集团主办,辽宁省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辽宁出版集团、春风文艺出版社承办。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电影局局长杨利景,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辽宁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东平,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春风文艺出版社社长单英琪,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吴良柱等领导参加了会议。著名评论家白烨、孟繁华、贺绍俊、潘凯雄、梁鸿鹰、彭学明、岳雯、刘琼、王国平、张晓琴、丛治辰、崔庆蕾、谢锦、徐晨亮、韩春燕等参加了研讨并发言。会议由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周景雷主持。
与会专家一致肯定《紫山》是孙惠芬近些年创作的高峰。小说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辽南乡村的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为主线,围绕乡村的人情人性、情理道德以及历史纠葛等诸多线索,细密深入地讲述了中国农村中那些有追求的农民,他们怎样在城镇化进程与灵魂拷问中完成自己的精神超越。作品细腻描绘了时代波澜中乡村的烟火图卷、浓郁的风俗传统,人性与情感在束缚与挣脱中散发的光芒。《紫山》是一部从人的道德难题和精神困境入手,讲述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中乡村人内心蜕变的精神史。
会上,评论家们的研讨集中在文学如何讲述乡土、新时代如何书写山乡巨变、文学如何表现乡村人的精神世界、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作家的责任与使命等重要母题,充分肯定了作者的文学探索与创新,肯定了作者持续追寻中国乡村精神之变,以呈现乡村人心灵史的方式见证山乡巨变,记录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艰难历程等方面的重大收获。
杨利景代表主办方之一辽宁省委宣传部致辞,他认为孙惠芬是一位有韧性的作家,她对文学的热爱是一以贯之的,她的创作始终扎根于辽南大地的精神土壤。《紫山》是孙惠芬调动她一生乡土生活经验和文学创作经验,耗费巨大心血完成的诚意之作。这部作品的突出价值在于她对中国农民群体精神生活的高度关注和深度开掘。《紫山》聚焦主人公的道德难题和精神困境,在人性的幽微处进行深度解剖,以三天和三十年这样的特殊结构,向其精神世界进行深度探索。在当代文学农民形象塑造中,在以粗粝和憨厚居多的人物图谱中,增加了与众不同的一笔。
臧永清代表主办方之一中国出版集团致辞,他讲到孙惠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朋友,合作已近三十年。多年来,她持续书写着她所关注的中国乡村,新作《紫山》,体现了她对时代山乡巨变的敏锐捕捉。她将辽南地域文化对人的塑造与束缚,融入叙事肌理,以敏锐的观察和细腻的讲述,使小说对乡村情感、乡村伦理的呈现与探讨,对人性挖掘和精神探索的深刻表达,达到了令人欣喜的高度。作品在重建乡村社会的精神秩序和信仰信念、激活古老乡土文明生机的同时,记录了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艰难历程。此外,《紫山》上下卷独特的叙事结构,让《紫山》跳出了传统的乡土书写模式,以心灵史的方式记录辽南大地的社会变迁,也使它成为解读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优质样本。
吴义勤代表主办方之一中国作家协会致辞,他认为孙惠芬是当代非常独特的作家,她的作品在整个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特别是农村题材小说中是非常独特的。《紫山》是她创作道路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从题材来讲,它是中国作协攀登计划的一个重要收获。《紫山》写中国农民的罪与罚、自我拯救、自我救赎的故事,揭示了农民灵魂的深度,这一点是读完之后非常感慨的。从人物形象刻画讲,这些人物有很强的典型性。冷小环、三叔、汤立生等这种人物灵魂之间互相的拷问、撕裂,都是很有精神深度的人物。此外,作品探讨中国民间的宗教,这是中国人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东西,也牵扯到对人物救赎的问题,把握得非常好,跟农民的生活和精神结合得非常紧。这是一部非常饱满的作品。
单英琪代表出版方之一春风文艺出版社致辞,她讲到孙惠芬始终以乡村为精神故乡,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乡土视角。在《紫山》中,她以更加成熟的笔触,记录故乡的变迁,探讨乡土文化的未来。她以难得的独立和内心的宁静感受时代的声音,以纯粹和真诚的力量探索文学的艺术形式和使命,以悲悯的目光关注小说世界内外的人物。《紫山》回归了乡土题材写作的缓而不疏的慢节奏,这明显有违当下的阅读习惯,但必要而可贵。这种近乎执着的耐心,绵密的写作,既是作者内心的需求、对文学本质的尊重,又是善意的呼吁。
白烨认为,孙惠芬最大的特点是有定力、有自己的节奏,所以作品出来质量都很高。这部《紫山》首先是一个“爱”与“耐”的当代传奇。借用萧军文章的话,“‘爱’和‘耐’是分不开的,只有真正的‘爱’,才有真正的‘耐’,反过来说也应该如此。且不管你爱的是什么。”《紫山》里面的三个人,汤犁夫、冷小环、汤立生他们的故事是“爱”与“耐”的当代传奇。其次这是一个有关“罪”与“罚”的自我救赎。汤犁夫和冷小环两人的爱恋,按照中国的传统道德是违背情理的,这使作品在爱与无奈的主题之外又隐含罪与罚的主题,救赎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作品的高妙之处是,尽管写到宗教思想、传统文化,但是两个主人公由自省、自立走向自我救赎,而且在自我救赎过程中参与到打黑除恶的过程中,反倒发生了积极的社会作用,这既使这个作品有相当的时代气息又有了精神,这是这个作品的一个特色。
孟繁华认为,孙惠芬的《紫山》在当下农村题材的创作里,是一部需要认真对待的作品,无论对作家孙惠芬还是对当下文坛都非常重要。原因就在于孙惠芬不仅处理了外在世界的事物,处理了可以看见的事物,更重要的是,她更处理了人的内心情感领域,处理了我们“看不见的事物”。这是文学首先要承担的功能。在乡村题材领域,我们要表达这个时代的“山乡巨变”,但还要表达那些“不变”的事物,比如人的情感世界的丰富、迷茫、复杂和矛盾,对人性的关注等。《紫山》有大众文学的元素,但它不是大众文学,它的“三角恋”关系,只是小说故事的外壳,而小说真正要讲述的,还是关于人性的深度、复杂性和丰富性,并对人的终极关怀一直深情瞩目。她超越了自己个人的创作,《紫山》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作家孙惠芬。
贺绍俊认为,《紫山》是一部关于心理剖析和精神救赎的小说,而且小说的结构非常特别。小说分上下两卷,孙惠芬在上卷专门进行心理剖析,将三个被剖析的人物置于一个闭塞的时空里三天。这三个人物,一个带着巨大的心理创伤而死去,另外两个带着对死者的巨大愧疚进入到下卷。在下卷里面孙惠芬讲述这两个人物怎么完成精神救赎。不同的叙述笔调往往对应不同的叙述内容,从这里可以看出孙惠芬在叙述上的成熟和老练。此外,孙惠芬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所有的历史宏大叙事都有自己的判断,她不是从宏大和公共的立场去解读,而是从人性和具体的角度,通过对三个主人公的心理剖析表现出她对很多宏大历史的特别眼光,很值得我们研究。
潘凯雄用四个字概括这部作品。第一个字“爱”,是故事的起点,汤立生、汤犁夫和冷小环三角之间的爱,既很复杂又很微妙,这是这个故事的一个主线,后面是由主线引发的。第二个字“缠”,这里面有人物外在关系上的相互纠缠,也有社会关系和这些人的纠缠,同时更是这几个主要人物内心的自我缠斗。第三个字是“熬”,这里面由“爱”和“缠”引发的种种煎熬,包括生命的煎熬、情感的煎熬、生存的煎熬等等,上半部分主要是生命和情感,下半部分是生存。第四个字是“超”,超越自我,超越情感,超越过往。就长篇小说本身创作来说,把城乡、男女这个基本母题用将近50万字的篇幅表现得这么深刻、细腻,应该说在这些年的文学创作里面是非常难得的一部作品。
梁鸿鹰总结了孙惠芬创作的几个特色:一是她主要围绕乡村社会的情感伦理和信仰问题展开,在她的作品中总能看到她对乡村女性婚姻、家庭情感困境有很多关注;二是叙事手法非常独特,比如亡灵叙事(《后上塘书》),还有非虚构(《生死十日谈》),另外方志在她的叙事当中也有很大的作用,《紫山》叙事是从慢到快的节奏变换;三是情感表达里面,人性本质捕捉得细腻,通过日常细节来刻画,这是非常突出的;四是城乡二元的视角在她的很多小说当中都是贯通的,既关注乡村的伦理困境,也关注城市底层进城的农民工。《紫山》中还有一点很新鲜,主人公汤犁夫的援建非洲经历,建立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此外,孙惠芬聚焦人的水平的提高和价值的呈现,无论是启蒙也好,人的精神建构也好,或者面对城市工业文明的冲击也好,这部作品给予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
彭学明提到,《紫山》他读了两遍,第一遍主要读故事,第二遍主要读语言,并分享了四点感受:第一,这部作品有真切的人间情理。上卷呈现的主要是人间的情理,当汤立生无意中发现妻子冷小环与自己敬重的大哥汤犁夫有婚外情而难以承受自杀时,这并不是婚外情,是柏拉图式的那种恋情,他们没有越位,但是他自杀了,这一场生死展现出这种情理。第二,有深切的社会法理。若是上卷主要呈现人间情理,下卷主要呈现社会法理。当汤犁夫看到宫占魁像土皇帝一样破坏环境而与之争斗时,当开发峨山侵占国家资源时,汤犁夫不畏强权螳臂当车式的英勇,当冷小环被陷害入狱,汤犁夫和刘广大相救等等,这些都是法理的真实呈现。第三,有广袤的时代肌理。在这部作品里面不但是见人间,也见时代。第四,有丰盈的艺术腻理。一是人物高度集中,二是事件的高度集中,三是心理描写细致入微,纤毫毕现。
岳雯认为《紫山》这部小说有很多讨论空间,比如它的反潮流,人对伦理、道德、命运的承担等等。她主要探讨了《紫山》上下卷之间叙事节奏、表现方式等的不平衡。认为当下的时代是一个压缩现代性的时刻,压缩现代性意味着当代史的空间既是前现代的,又是现代的,而且还是后现代的,当我们同时经历这些压缩的现代性的时候,我们会把不同的经验放在一起。但特别有意思的是,孙惠芬做的是一个接合而不是融合,接合是这两块直接拼接在一起,融合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接合是当下面临的一切困难、焦虑、矛盾、纠结,是我们心灵上所接受的所有考验的来源,这就造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紫山》不是一个当下我们能够很熟悉的结构上很圆融、很均衡、很完美或者艺术上很平衡的文本,它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有太多困惑,这个困惑恰恰是一个作家非常诚实的的面对时代加诸到我们身上各种困难。她很佩服孙惠芬对自己艺术的执着追求以及对于我们时代的诚实面对。
刘琼说她特别欣赏的是,这本书里孙惠芬坚持了一个原则,也是一个好的气象,就是让文学写作回到人学。孙惠芬从《歇马山庄》到《寻找张展》到《紫山》,她的笔触始终聚集在东北大地辽南土地上心灵世界丰富的人的地域文化特征。此外,她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原生态历史的进程,她选择一个侧面,不厌其烦的娓娓叙述乡村生活的时空样态,像一个丰茂的雨林一样密集的呈现方式,当然阅读的时候会有点透不过气,但这是她选择的写作方式,从心灵内部、人的内心来进入,从内心的困境来反映外部的环境,这确实是很好的探索。
王国平认为,孙惠芬对于乡村生活、乡村社会运行的逻辑非常熟悉,她写出了中国式乡村的伦理。虽然小说写的是三个主人公的内心生活,但却与时代生活、公共生活、社会生活交融在一起,所以这是一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书,也是向内用力、向外敞开的书。孙惠芬的非凡之处还在于在无助、无奈、惶恐的极限体验中,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读这部《紫山》,透过文字可以看到乡土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面貌,以及中国人身上的性格和品质。
张晓琴认为《紫山》是一部为苍生立传的作品。第一,孙惠芬这个作品的独特性在于,她貌似写两个人、三个人,貌似书写个体,实则是非常宏大的叙事。第二,《紫山》中的人物和孙惠芬本人一样,都在进行漫长地找寻,都拥有坚忍的力量。第三,小说中色彩刻绘与信仰呈现是紧密连接的。紫山之紫不仅是高山呈现的色彩,更意味着小说人物的精神和作家写作的双重超越。小说结构上卷是阖,是非常拘谨的,读者和主人公都被抛入极端处境中,小说结尾由阖走向开,由死走向活,孙惠芬自己肯定是有信仰的,她的信仰就是写作本身,她以写作为苍生立传。
丛治辰认为,《紫山》是一部在技术上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小说,让他又找到了特别重视小说技巧时代的长篇小说的特征。在书写整个事件,围绕三天的时间,有一种似真似梦的手法。其次,小说上卷之所以写的妙趣横生,因为作者在不断地隐藏,不断提出真相又掩盖一部分真相,悬念设置让小说具有可读性,但这种“吞吞吐吐”又写出了三个人的性格。再次,对三个人物的描写“各自为战”,三人虽同处一室,但他们各自内心独白的展现使他们都非常孤独。这部小说的野心,小说看上去是聚焦人,但是在高度凝聚个人的同时,又使得时代以小说技术的方式而不是以小说内容的方式,从小说的叙事方式、叙事节奏、叙事结构等呈现出时代的另一面,时代不是以具体事件呈现的,时代是一种精神气质。
崔庆蕾认为,孙惠芬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探索,我们一直把她定义为一个写乡土的作家,但实际上乡土只是孙惠芬作品的一个叙事装置,她要探索的东西特别多。《紫山》是非典型的乡村叙事,是内叙事加外叙事相结合,而且内叙事来带动外叙事的小说。这个作品最深层的叙事动力来自于几个主要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在这个主线之外尤其在下卷中展开写辽南的乡村生活、伦理道德等。其次,小说人物都具备精神的张力,而且这种张力来自于不同类型,他们都有一种精神的裂度,但是他们又都有自我整合和安放方式,这些人物都带着生命的痛感,这种冲击力既冲破小说中所写的乡村的传统观念,也冲击我们既有的文学观念,尤其对乡村女性的认知,这是这个作品特别重要的贡献。
谢锦评价,孙惠芬是中国文坛少有的努力而执着、认真而细致的作家,一直用尽全力在大时代的喧嚣中用自己的笔书写中国乡村社会的各种转型之痛,既看见时代缝隙处的锐利,又有能够照见人性寒凉面的悲悯,她的小说就是小切口、大景深。《紫山》写出中国乡村沉甸甸的现实重量,写出三个心在远方身在沉潦的主人公在时代中的悲剧和自我救赎,是一部有分量的长篇佳作。关于上下卷在结构等方面的不平衡,她觉得这部小说的好恰恰在于此,有些作品看似不完美之处,恰恰有时候是小说最动人之处,因为作家在此刻无法解决、无能为力,这个地方正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徐晨亮谈到,这部小说是谈内心的问题、精神的问题、灵魂的问题。文中第二章关于峨山的描写很有意思,“峨”字是一个“山”一个“我”,有“用我眼看山山就有了我”的比喻。这部小说努力书写的就是人物的内心世界,既是我,又是山,所以紫山也是我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挖掘人物精神世界和灵魂世界的时候会有大我、小我,或者是向内、向外这样的说法,但是在孙惠芬这个小说里面,大即是小,小即是大;内即是外,外即是内;山即是我,我即是山。《紫山》就像一面镜子,它不给你答案,而让你看到所有都在向外求,而真正的平静只能向内求。
韩春燕认为,孙惠芬的这部小说在当下现代化进程中,乡土写作面临创作困境的时候,提供了一些新的写作经验。在看待城和乡的问题上,在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之间的相互联动、相互转化,包括时代和个人的联动,外在景观、生活图景与内心的联动等方面,她也提供了新的写作经验。此外,在如何处理大和小的问题,孙惠芬以小撑起大,以蜻蜓之墨撑起重大的时代历史变革,她也提供很多有益的经验。孙惠芬和乡村的关系从来没有断过,她这种情感也是其他乡土写作者可能没有的。

研讨会现场
会上,作者孙惠芬表达了对各位专家学者与会议主办、承办方的由衷感谢。她说,她特别高兴也特别忐忑,虽然是历时十年的心血之作,写作中,也努力在作品思想性的挖掘和艺术性的打磨上下功夫,但她知道,与她心目中的经典作品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也存在太多的不足。现在,在刚刚过去的一上午时间里,聆听到各位老师对作品的阅读意见,让她温暖,让他收获巨大,忐忑的心绪在持续的温暖中,盈满了感激之情。
最后,孙惠芬分享说:“一直觉得,文学之所以抚慰人心,是说它可以从人性的幽暗之处进入,在体察人类普遍的爱与恨、孤独与脆弱、恐惧与罪恶的同时,让你看到救赎之光,本性之爱,人类永不消失的对精神故乡的找寻。为此,我愿意在未来的时光里,孜孜以求,永不懈怠地向伟大的文学经典学习,向人类精神世界更深处探寻!”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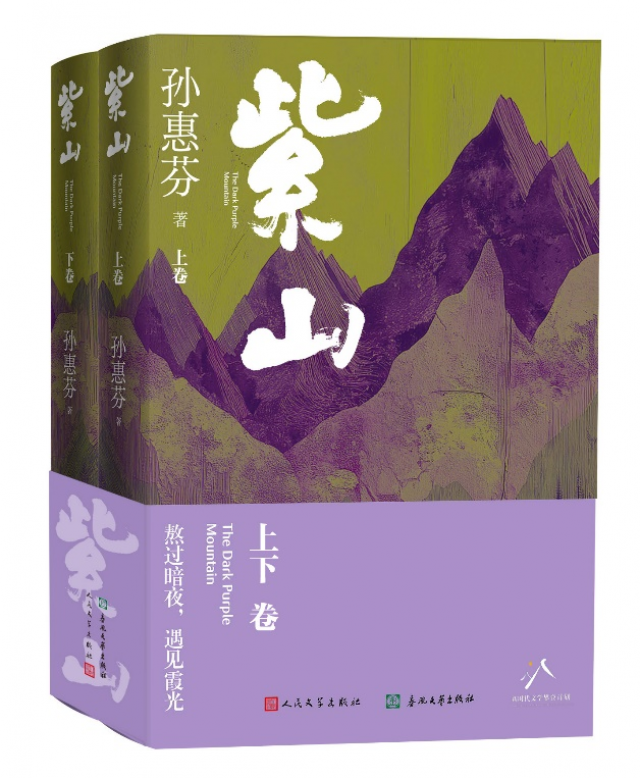
熬过暗夜,遇见霞光,鲁迅文学奖作家孙惠芬的最新长篇力作。
小说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辽南乡村的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为主线,围绕乡村的人情人性、伦理道德以及历史纠葛等诸多线索,细密深入地讲述了中国农村中那些有追求的农民,他们怎样在城镇化进程与灵魂拷问中完成自己的精神超越。作品细腻描绘了时代波澜中乡村的烟火图卷、浓郁的风俗传统,人性与情感在束缚与挣脱中散发的光芒。这是一部从人的道德难题和精神困境入手,探索人类精神超越如何发生的农村题材小说。
作者简介:

孙惠芬,1961年生于辽南农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孙惠芬文集》七卷,长篇小说《歇马山庄》《吉宽的马车》《上塘书》《寻找张展》等七部,童话一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女性文学奖、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等,三次入围茅盾文学奖。2002年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语、法语、蒙古语、日语等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