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 | 《不舍昼夜》:通向自我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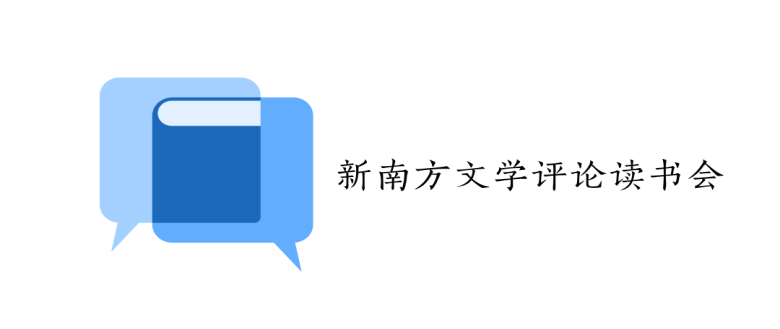
“新南方文学评论”读书会由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申霞艳发起,成员包括爱好评论写作的研究者及青年学子。读书会密切关注当代文学前沿问题、关注本土文学发展,是新南方文艺评论创意写作联盟的首席工作坊。
申霞艳(主持人):这次读书会共读我们广东作家王十月的长篇《不舍昼夜》,我想这次阅读对我们也是通向自我之路。王十月是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今天很多人会觉得打工这个词不高级、不平等,试图换成劳动者、工人文学之类,但我觉得打工是一个充满动感、充满能量的命名;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指认,对一代人心灵代价的指认。打工文学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流动与“脱嵌”,见证人往海岸、港口周边聚集,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革新。《不舍昼夜》是王十月对自己打工身份的确认,也是打工文学的升级迭代。主人公王端午通过打工体验了多重生活,见识了一个广阔的世界,通过阅读改变了命运,并不断自我反思。小说在人物、细节、城乡空间及时代对比,主角对西方文学、哲学经典的阅读转化,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人格的多重结构与中国传统的鬼魂叙事结合,父子代际传承,女性成长,自我诘问与身份认同等等方面均有所思考,值得分析,下面请大家各抒己见。
刘志珍:身份的再造与自我认同危机
《不舍昼夜》中,王端午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自由,渴望确立起“完整的自我”,却总在现实与理想的错位中作困兽斗。在尽显人生的荒诞与虚妄的同时,透视出小人物绝境中挣扎的生命光亮。小说别出心裁地设置了弟弟王中秋这一“缺席的在场者”,以对中国民间鬼魂附身传说和西方现代心理学人格理论的糅合,指涉王端午隐秘的自我认同危机。对弟弟死亡罪责的主动认领,使他产生强烈的罪感意识。弟弟由此成为他难以超克的心魔,亦是其精神自我,一个阻止他肉身下沉、堕落的自省装置。王端午希望逃离乡村和父亲,及其象征的暴力、野蛮。但县城并非理想的乐园,他与师兄李飞的冲突,既蕴含着城市对乡村的傲慢与偏见,也与其孤僻、不合群的性格息息相关。弟弟则宛若其成长引路人,道出王端午受害者表象背后的自卑心理,劝说他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不愿复刻父亲、师傅人生的王端午,怀揣梦想、激情和抗争命运的执拗,踏上南下深圳打工的冒险之旅。但初到广东的他不仅被卖猪仔,还因没有边防证被挡在关外,成了城市“三无人员”、盲流,于失序中迷失自我。在活着与尊严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以盗用李文艳身份的方式,入职名匠广告公司。名利双收的他,始终面临世俗之我和精神之我的剧烈冲突,难以挣脱良心的谴责。这在他得知真正的李文艳自杀后,体现得尤为明显。冒名顶替被告发后,他选择辞职去开书店,并将名字改为王端,企图重新确证自我。但这实则是一种回避现实的消极策略。而从王端改回王端午后的流浪,则具有某种自我放逐意味,也可谓一场自我辩解的“行为艺术”。在彻底抛开世俗的考量,决定说出埋藏心底的秘密时,生命的戛然而止,预示着他终将无法实现灵魂的救赎与安妥。其身份再造凸显出打工青年的无奈与酸楚,也以自我的不断扭曲、变形,映射出个人与时代、社会间深刻的失调,改革开放的历史图景亦随之铺展开来。
邱雯意:“知识”的角色及其时代性
《不舍昼夜》聚焦王端午一生对人文知识的学习与输出。改革开放初期,“卡门”式的自由和存在主义哲学为王端午带来启蒙,促使他走出乡村、南下深圳,在赚钱之余寻求更广阔的学识和有意义的生活。人物在不同时代下的知识输出,成为历史现场的鲜活写照。小说中两类不同的“读书会”形成显著对比。1989年的县城文化宫读书会是知识分子表达公共理想的场所,体现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激荡。进入新世纪,西西弗斯书店书友会则是交流阅读体验的空间,同时也承办新书发布会,其文学属性更为突出,展现出市场经济发展下文化空间作为精神栖息地的重要意义。另外,小说有意设置两个颇具象征意味的“说书”场景:90年代,年轻的王端午流浪深圳,在书摊上谈论第欧根尼和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其“说书”姿态闪耀着知识所赋予的尊严。而听众对“文化人”的敬仰与善待,象征着那个时代对具有稀缺性的学问的推崇。而到了互联网时代,王端午在直播镜头前畅谈存在主义与传统文化,知识化身为打造网红标签与“割韭菜”的策略。然而,依托网红模式传播的知识不得不走向标签化、娱乐化,其掀起的流量无法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向自身,只能成为互联网上昙花一现的猎奇景观,极易遭受网络狂欢的反噬。小说中“流浪大师王端午”的热度迅速衰退,知识的标签很快被其婚姻谣言覆盖,折射出了互联网时代下知识的脆弱与悲剧。
张昀菡:未选择的半个句号
纵览《不舍昼夜》,王端午的一生总在不断追逐,却也不断回顾未选择的另一条路,这是他所有遗憾和圆满的源头。作者有意放大了王端午人生的所有选择与交接点,让他一生迷失在小径分叉的花园中,幻想自己的另一种可能:如果参加了高考、如果入关找宋小雨、如果进了菲林画房、如果和老曾一起投资……改革开放前后,时代的变换不可预测。因此王端午即将推石上山时总是失手滑落,在往后的人生中,错过这些关头的他也在接受当下的同时频频反顾,幻想可能画下的另半个句号。
他灵魂的挣扎也未曾止息。从李文艳、王中秋、王端到王端午本人,主角换过数个身份,在其中纠缠、交融,最终回归自我。故事的最后,历经跌宕的“流浪大师”王端午终于决定鼓起勇气直面内心,说出心底的秘密,让喧闹的灵魂归于平静,却又在临门一脚时被死亡阻挡,只来得及画下半个句号。他赎罪的理想随之消逝,再次成为即将攀上山顶前滚落的顽石,随着生命的消逝彻底落入山崖。但西西弗斯神话之所以能流传后世,正源于那无可回避的缺憾,与凡俗个体不舍昼夜的努力。正如王十月原本拟定的书名《凡人传》,人之所以为人,也在于这些灵与肉的缺憾,所有未选择的路相互交织,才能汇成一个个不完满、却完整复杂的“凡人”。
郭雨欣:在常与无常的张力中感受生命的荒诞
王端午中学辍学,打工是他的生存之道,他在深圳为了过关坐黑车却遭遇抢劫,不得不流浪回家,规律的生命轨迹因而被打破,但王端午的不甘心驾驭着更大的欲望,使他成为了李文艳,原先靠体力维持生计的秩序崩解,凭知识赚得体面生活的生存方式成为新常态,可一封举报信又改变了“李文艳”的生命轨迹……这些事例是王端午游走于常与无常之间的佐证,他在身份转换中感受生命的荒诞与恩典,以顺无常的姿态接纳流动,完成了对主题的自我言说。
《不舍昼夜》无意解答人生该往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也不进行廉价的说教,而是坦然放弃对高深意义的追求,揭开生活稳定性的假面,展示个体在秩序与混乱之间的挣扎,从而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书写:它不向人提供形而上的标准答案,而是以真实可感的生活体验让读者窥见生活的荒诞,在接受无常中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方兆和:过一种文学人生是可能的
《不舍昼夜》表面书写了一个普通人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实则深刻探讨了文学与生命的关系。它让我们思考,在漫长的一生中,文学到底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当下,“理想主义”似乎沦为某种嘲讽,这部小说却以鲜活的故事证明,过一种“文学式”的人生,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值得追求的。
在主人公王端午一生的每一次重要选择中,文学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王端午本来只是一个出生在农村的青年,他通过四姐了解到了《卡门》,第一次领悟“自由”的涵义;《麦田守望者》坚定了他走出农村的决心;《存在与虚无》开启了他对知识的启蒙;《卡夫卡传》支撑他熬过最艰难的打工岁月,并重新审视与父亲的关系。在从名匠广告公司辞职后,一直以来对文学的热爱让王端午选择开书店,并采用“西西弗斯”之名。他与妻子冯素素的相知相恋,同样根植于文学的共鸣。而王端午在重病一场后选择放弃一切踏上流浪之路,是因为《荒原狼》的感召。甚至他最终在流浪中成为网红“流浪大师”,其独特魅力也源于对文学的深邃理解。
文学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文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代,这部作品或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它告诉我们文学绝非生活的点缀或消遣,而是在无常的人生中,真正可以带给我们对抗虚无、坚定信念的力量。王端午的一生都在追求文学,实际上他早已将自己的一生活成了文学。
伍常旭:《不舍昼夜》中的乡土情结
《不舍昼夜》中提到了许多西方书籍,但却始终能感受到浓烈的中国式乡土情结。王端午的内心始终与故乡紧密相连,即使晚年开始流浪,目的地也仍是故乡。这片他曾经拼尽全力逃离的土地,最终却成为他心中“精神自由”的象征。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着“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正如路遥在《人生》中安排高加林最终回归乡村一样,王端午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对乡土社会的眷恋与依赖。
此外,小说设置了家族中的“反叛者”形象。纵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家》中的高觉新、《白鹿原》中的白灵,他们大多年轻且思想与众不同。《不舍昼夜》中的四姐以及王端午,与父亲发生冲突、并选择离家出走等行为,契合“反叛者”形象,展现出个体与传统之间的矛盾。
乡土社会中人情与自然的融合碰撞,也在《不舍昼夜》的环境塑造中得以显现。小说中改革开放前后的深圳,充满奇幻、暴力、血腥、奋斗与遗憾。秩序仅存在于王端午打工的场所,脱离工厂后,他则开始流浪,在“无序”中寻回生命的自由。但“无序”并不意味着冷漠,当他在生病、饥饿之时,仍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王端午于秩序与无序之间挣扎的过程,同样深埋着乡土的淳朴与野性。
马褀宸:从“弑父”到“寻父”
王端午的一生是一场未完成的“弑父”,也是一场漫长的“寻父”之旅。他在青年时期逃离父亲,却在中年活成了父亲的模样;他的儿子也远渡重洋,以同样的方式逃离了他。这种父子关系的循环,既是中国文学“弑父情结”的延续,也是当代人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寻找自我的精神困境。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弑父”往往象征着对旧秩序的挑战。但王端午的弑父是不彻底的——他逃离了父亲,却无法逃离父亲的影子。当他“赋闲”在家,像父亲一样漫无目的地游荡,甚至在江边长椅上过夜时,惊恐地发现自己正沿着父亲的轨迹行走。这种循环暗示着单纯的逃离,并不能真正斩断父权的枷锁。
更耐人寻味的是,王端午的儿子王快乐以留学美国的方式“弑父”,完成了他当年未能彻底实现的逃离。然而,这种逃离同样充满矛盾——当王端午临终时,儿子未能归来,正如他当年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父子之间的疏离与缺席,构成一种宿命般的轮回。王端午的出走也并未带来真正的解脱,他的流浪更像是一场自我放逐。但或许,这种放逐本身就是一种“寻父”——不是寻找具体的父亲,而是寻找自己与父辈、传统、乃至自我和解的可能。《不舍昼夜》中的父子故事超越了简单的反抗,揭示出父子关系中最为深层、柔软、难以道出的复杂情感:恨与爱、逃离与回归、断裂与延续。王端午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不是彻底“弑父”,而是在循环中理解父辈,并在这种理解中找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