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写小说 新作《心曲》出版 徐运祥:摄影的尽头是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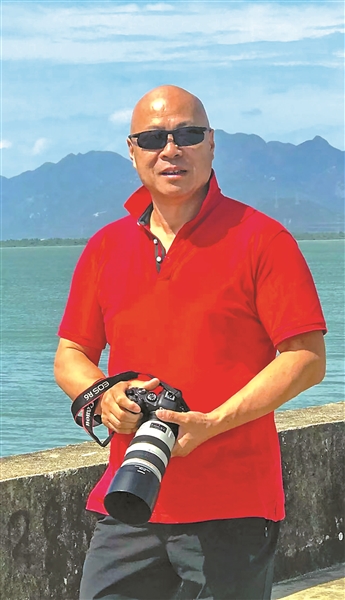
徐运祥的人生经历颇为丰富。大学期间,他主修英语专业,毕业后曾从事翻译工作,之后成功转型,成为一名知名摄影师。如今,他担任亚洲“一带一路”国际摄影大联盟副主席及香港国际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除了深耕摄影领域,徐运祥还致力于文学创作,于2022年推出首部长篇小说《随风而去》。近日,他的新作《心曲》正式问世,小说聚焦于三位女性的生命故事与内心世界。
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徐运祥笑称,《心曲》出版后,身边的女性亲友纷纷“先睹为快”。“我知道她们都很好奇,一个光头八尺男人笔下的女性会是什么样子——是否在某些方面与她们相似,或能否在某一个瞬间引发共鸣。”令他欣慰的是,许多女性朋友读完之后甚至向他热情“催更”:“你能不能先放一放其他事,赶紧继续写,把她们的故事讲完、讲透?”徐运祥坦言:“每次听到这样的催促,我心里都一阵发热。”
是否能够了解女性 根本在于是否付出“真心”
《心曲》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沈阳、伦敦和杭州,讲述了三位女性——王奕桐,一个天赋异禀的小提琴手;李红梅,一个来自湖南山村的善良女孩;言自芳,一个中医世家的大家闺秀——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困境和抉择,以及她们在追求爱情、事业和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坚韧和勇气。
徐运祥表示,《心曲》中人物的经历其实就是现在很多青年人刚刚走过的路。之所以选择讲述女性故事,并且是三位女性的故事,与他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
1985年冬天,徐运祥带领一个八人技术团队前往比利时,由于是技术培训项目,周期较长,中餐馆便是大家常去的地方。“在这里我听到女人们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好好生存,让自己有好的未来。刚毕业不久的我羡慕她们有机会和能力在海外发展,她们却羡慕我即将踏上回国的归途。那段时间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女性旅居海外的故事片段,渐渐汇聚到我心里,成了《心曲》的基本原材料。随着后来十几年多次往返于欧洲,这些故事不断在我心里发酵沉淀。”
直到有一天,徐运祥读到了一则故事:一千五百年前,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中,一具乞丐的尸体正在路边腐烂。一位路过的少年王子目睹这骇人景象,开始深思人生的无常。他最终决心离开王室,走入旷野,寻找一条自救与救赎人类之路。多年后,他走出旷野,成为释迦牟尼佛,向世界宣讲他所悟得的解脱之法。而那具腐烂的乞丐尸体,也在不知不觉间,为世界最大宗教的诞生贡献了一部分力量。徐运祥说:“读到这时,那些埋藏心底的遥远故事突然再度鲜活。她们的经历如此真实、动人,如果我不去讲述,那些感动我的瞬间将缺少一道道绚烂彩虹,我决心要把她们的《心曲》唱出来。”
尽管创作情感丰沛,但徐运祥坦言这部37.7万字的小说不仅依靠内心涌动的情感,更需依托整体结构的搭建与细节的反复梳理。“小说中每个角色都背负自己的使命,分析人性的优弱点,需要作者具备极大的耐心和知识储备。如何借情节映照人性,成为创作中的挑战与亮点。否则故事就会流于表面,如同隔靴搔痒,无法触及内心最柔软之处,更谈不上让读者共鸣。要实现这种效果,作者必须从日常生活中捕捉发光、对作品有益的细节。”
对于小说人物是否有原型这个问题,徐运祥表示,小说中虚构的角色其实是众多女性特质的集合。比如某个角色的穿着,可能来自街上偶遇的一个路人;她戴的帽子,或许出自某次会议前排陌生女孩的形象。如此种种。因此,小说中每个人物穿的都是“百家衣”,吃的是“百家饭”,过的是“百家日子”。
问及作为一名男性作者,他是否真正了解女性世界?徐运祥坦承,从古至今没有人能知晓女性的全部真实。“不是盲人摸象,就是管中窥豹;不是流于表面,就是过度辩证。”但他并不认为这就意味着无法走进女性的内心,“这一点要用我母亲的话来解释才最恰当。她曾说,只有‘真心换真心’,才能‘八两换半斤’。是否能够了解女性,根本在于是否付出‘真心’。如果没有真心,所谓的了解就像水中浮萍——叶子虽大,根却很细。只能远观猜度,永远探不到花的深处。”
母亲的话是人生中最亮的灯 垒成了《随风而去》和《心曲》
在《心曲》中,徐运祥写道,“献给1985年的自己”。他解释说,那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的关键时期——农村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城市综合改革逐步启动,对外开放持续扩大,科教文卫体制改革也同步推进,这一切共同构成了1985年社会变革的主基调。
于他个人而言,1985年同样意义非凡。那一年,23岁的徐运祥因公首次踏上欧洲的土地,一切都是崭新的,所见所闻如梦似幻。“当地朋友看到我手里拿着法国法郎、比利时法郎和荷兰盾,就告诉我,到2002年整个欧洲就会统一货币,再也不用携带这么多种现金。那时,我觉得2002年遥不可及!”这段经历让他打开了眼界,原本平静的内心泛起了波澜。回国后,报刊对经济特区报道中所用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话,更让他倍感振奋。“1985年发生了很多事,但思想上的天翻地覆,对我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值得永远纪念。”
徐运祥开始小说创作,也深受母亲的影响。“母亲的话让我至今念念不忘——不是一句,而是很多句,她的话语就像我人生中最明亮的灯。每当我和姐姐、弟弟聚在一起,总会情不自禁地复述母亲的‘语录’,我们在笑声中潸然泪下。这些话如同砖石,一块块垒成了‘一楼’的《随风而去》,‘二楼’的《心曲》。”
父亲早逝之后,徐运祥与姐姐、弟弟的童年仿佛一瞬间跳入了中年,“母亲也在一夜之间既当妈又当爹,在双重角色之间不断切换。她见到煤油灯下睡眼惺忪、无心学习的我,总是心疼地开导:‘学问学了是你自己的,别人拿不走!’等我结婚生子后,她又提醒:‘孩子吃什么好吃的,你都先吃一口,这样他才会孝顺,以后端起碗就想到爸妈吃了没有。’她让我明白,孝顺是一种日常的修炼。”
徐运祥说母亲非常明事理,她始终关心每一个孩子的心理平衡,不让任何人受委屈。甚至在生命最后的那个星期,她仍坚持从广东返回西安,她说:“要折腾,就都折腾一下,不然我不在了,他们会难受的!”她所说的“他们”,指的是不在身边的姐姐、弟弟,还有那些她始终放心不下的孙子们。“母亲节俭了一辈子,就连身后事也留下一句名言:‘金棺玉葬,狗吃一样。’母亲过世让我成为孤儿的同时心智一下也变得成熟,许许多多的不舍变成了思念。于是我拿起笔将模糊的记忆拉回到了眼前,不让《随风而去》变成遗憾,把所有的感受谱成《心曲》。”
摄影和小说写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是不同的艺术传播方式
作为著名摄影师,徐运祥在构思小说里的场景或人物时,会先在脑中“构图”或“取景”吗?徐运祥认为,一个成功的摄影师需要炼就一双“摄影眼”,对光线、阴影、纹理、瞬间以及构图等等极其敏感。“假如在马路上遇见有人突然停下,双手对某物勾画出一个框架,不用问,这人是人文摄影师。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他勾勒出了别人无法识别的结构,没有这种能力是无法拍出深刻的作品来的。”
徐运祥认为,这种能力的培养对于小说的创作,有着巨大的帮助,比如他在《心曲》中有一段描述言自芳的美丽:“高远痴痴地望着言自芳的背影,没想到言自芳还要扭身回来,只见一张标准的瓜子脸上忽闪忽闪一双大眼睛。高远看到这双大眼睛,就觉得自己内心一股自卑感油然而生。不像是他的杯子被言自芳打烂了,而是他打烂了言自芳的杯子似的。”徐运祥解释说:“用内心的自卑感来刻画言自芳的漂亮,避开平铺直叙无力的夸赞。摄影艺术是对比的艺术,大小对比,明暗对比,美丽与邪恶的对比,等等,无处不可对比。小说借鉴对比的形式让自卑感对比美丽,既轻松又深刻。”
在徐运祥看来,摄影和小说写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两种不同艺术传播的方式,是相互成就相互兼容的。“我曾经发表过许多图文并茂的作品,如《清泉石上流》《刹那间》《异海拾贝》等,都是用文字的方式进一步向读者传递摄影作品深层次内容,这种说明式的设计让观众收获了视觉和精神双重收获,让摄影更好地被理解消化。”
在写作时,徐运祥说很多摄影理论和实践会不自觉地从他脑中跳出来,试图影响小说的方方面面,“这就是硬币有字的一面受到有花一面的影响。同时,当你试图拍出有价值有震撼力的照片时,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写过的字字句句都会不自觉地在影像里找到,这就形成了别人眼里的高度。”
法国著名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瞬间美学”理论对徐运祥影响很大,“布列松是被誉为当代世界摄影十杰之一的抓拍摄影大师。我走进‘瞬间美学’的世界也是受了布列松等大师们的影响,拿起相机‘捕捉’那些‘决定性瞬间’。照片的即时性对时间有特定的要求,一张好的照片要创造历史是需要经得起时间和空间考验的。经过漫长岁月的沉淀,依然能够唤醒人们的良知,触动人心柔软的才是好照片。”
在徐运祥看来,写作则恰恰相反。它需要将沉淀在记忆里的闪光点“捕捉”到眼前,用各种各样的写作方式传情达意,试图说明白一个问题,讲清楚一段故事,将过去或激动或沉重的情感拉到写作者的笔下,让它们熠熠生辉。“摄影和写作相似的是,它们都源自对现实生活的冲动和热爱,进而想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想法,小则感动自己,大则警示天下。可无论哪一种都是感动中的瞬间,只是‘捕捉’的工具不同罢了。”
摄影和写作是互补的 相辅相成的
从摄影师到写作者,徐运祥说并不是决定写作,就放弃了摄影,而是摄影不能完全满足他对内心真情实感的抒发,“这两个技能都要提高,不能互相取代。摄影传播速度快,小说成书速度慢。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不会入心入肺写书出版的。”
徐运祥认为,摄影兼具客观记录与主观表达的双重属性,“不管这种客观记录发生在什么时候,在面对它的时候,观众感受的都是现在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会因为照片的历史性而改变,都是当下的感受。而文字就可以打破这种局限性,用‘从前呀……’回到过去,用‘再后来呀……’描绘愿景。这种一言千里的灵活性是摄影无法替代的,更不要说对内心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了。不过摄影的直观呈现也可让文字表达黯然失色,好的照片不需要言语表达就能让人情感升华,人们的情绪波动高下立判。”
而对于主观表达,徐运祥表示,一张照片是摄影师本人对外界的影像感受,“每一张照片都是局部的,不全面的,一张或几张照片不会囊括了高深莫测的哲学内涵,不然摄影比赛为什么有‘组照’这个组别和‘故事’这个栏目呢?就是希望用更多的照片向大家分享摄影师要表达的深层次内容;而文字表达能有效地避开这些缺陷,可以用比喻、递进来表达文学张力,用夸张、排比、反问加强语气等等,这些功能摄影是望尘莫及的。”
徐运祥笑说摄影的尽头是文学,“用镜头是无法完全表达感情和故事的,只有用文字才能完整地呈现摄影所要表达的情感内容。小说能够将固定的照片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再创作,用文字描述出照片背后的故事,也许讲出来的故事见仁见智,可都是对照片的进一步解读。”
始终保持创作灵感 需要主动建设和维护“灵感生态系统”
在《心曲》脱稿以后,徐运祥说自己开始撰写第三本长篇小说《菲佣艾米丽的故事》(暂定),这本书讲述一群背井离乡的菲律宾女青年到香港谋生活的历程。
对于多年来始终保持创作灵感,徐运祥表示,这是所有创作者终其职业生涯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始终保持创作灵感并非指望‘灵光一闪’的偶然事件,而是一套需要主动建设和维护的‘灵感生态系统’。”
对于如何建设和维护“灵感生态系统”,徐运祥有四个建议:首先是输入,“持续为你的“灵感水库”蓄水。灵感不会从真空中产生,它是对已有信息、体验和情感的再组合。因此,持续高质量的输入是获取灵感的根基。”其次是将输入转化为属于自己的灵感,“输入是原材料,需要加工整理才能变成灵感。”第三是建立持续创作的实践体系,“灵感是脆弱的,必须通过实践将其固化。不要犹豫,有了‘快感’就记录下来,写小说的话就用文字写下来,摄影就拍下影像。”第四是保护难能可贵的创作心流与能量,“心流是一种心灵的再揉搓,我们要管理好。”
总之,徐运祥认为,多年来保持创作灵感,靠的不是魔法,而是一套科学的、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像海绵一样吸纳,像工匠一样处理收获的知识,像运动员一样输出自己的能量,像园丁一样保持自己的初心。
徐运祥表示,他从事的翻译、摄影师、小说家这些工作都需要专心和坚持。“做好一个工作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共同支撑。这就像建设一座大桥,不是一个桥墩就能完成支撑任务的,需要许多桥墩才行。”也因此,对于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徐运祥的建议是不要追求“博而不精”,而要追求“一专多能,融会贯通”。“不需要在每条路上都成为第一,但需要一条主路来定义你的身份,并让所有其他道路都成为这条主路的丰富补给线。‘精’不在于你会多少种技能,而在于能否将各种感悟融会贯通,最终在你选择的核心领域创作出富有底蕴的作品来。所以,做一个斜杠青年又何尝不可呢,热爱多种艺术是幸福的事。”
而作为亚洲“一带一路”国际摄影大联盟副主席,他认为当下摄影行业的发展趋势对创作者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和机遇呢?徐运祥表示,今后几年的摄影行业发展趋势是技术迭代加速(尤其是AI)、创作回归人性化表达,以及商业模式更加多元化,“这意味着摄影人需要成为‘多面手’,既要拥抱新技术,也要强化个人独特的创意和视角。总而言之,摄影行业,技术是强大的辅助工具,但‘人’的洞察、创意和情感连接才是核心竞争力。成功的摄影人,将是那些能拥抱变化、不断学习并用独特视角讲故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