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韬:十年来内蒙古儿童文学中的童心润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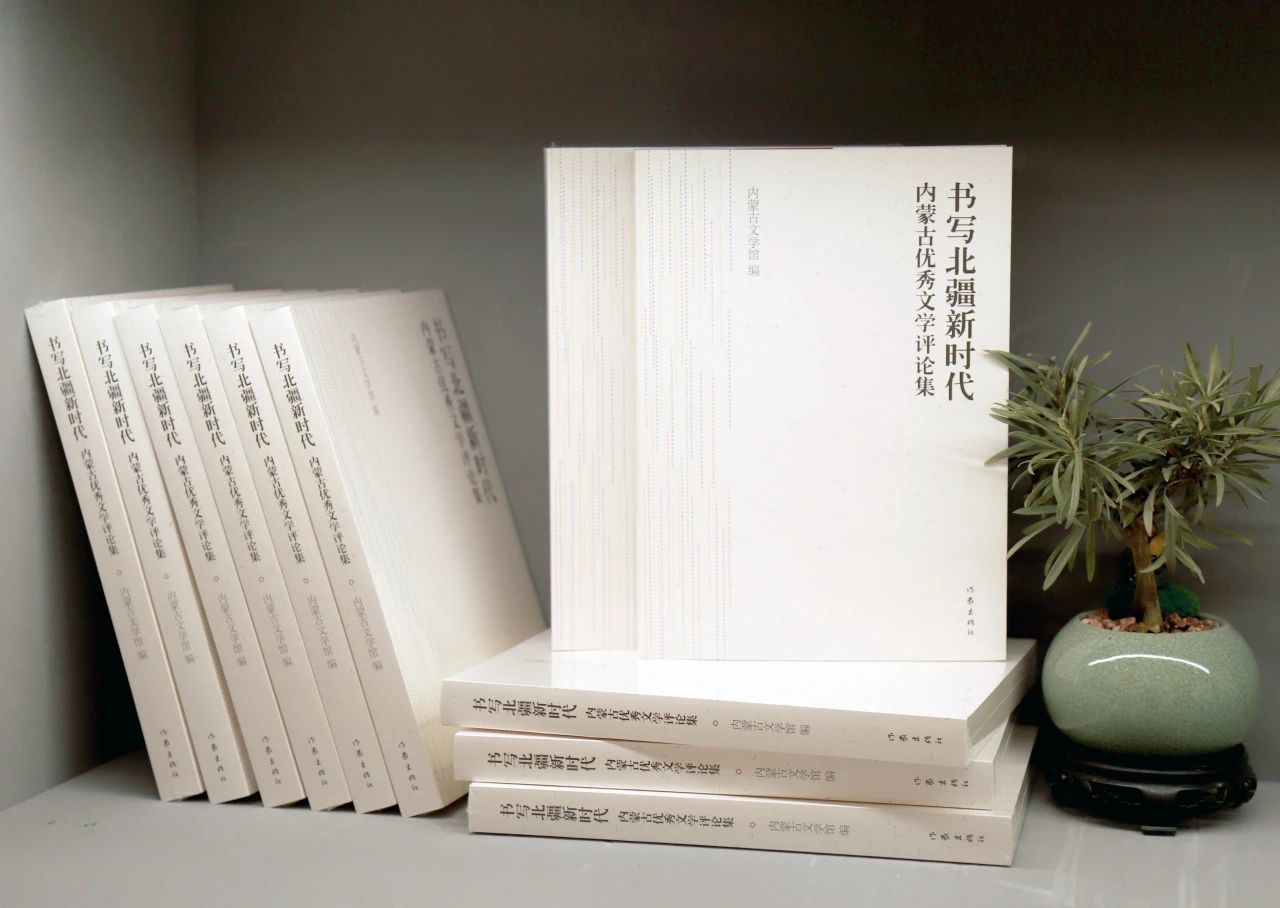
“春发其华,秋收其实”,伴随着祖国的成长,内蒙古儿童文学迄今已走过了七十多个年头,其间曾涌现出一批富有草原特色的优秀作家,如专写儿童文学的杨平、杨啸、力格登、乔澍声、鄂·巴音孟克、张我愚、石·础伦巴干等。新世纪以来,韩静慧、许廷旺、贾月珍、夏桂楣、吕斌、杜拉尔·希然、童话(王雁君)、刘金龙、马端刚、权蓉、何君华等,以及耕耘多年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张锦贻,纷纷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儿童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以鲜明丰富的创作特色和高质高量的作品产出屹立于文坛。面对文学与现实的交叉影响和消费与媒介文化的综合作用,新世纪内蒙古儿童文学在三个艺术层次——少年文学、童年文学、幼年文学,一方面继续立足于内蒙古本土的现实情境来书写“草原式童年”,通过文学隐喻的方式言说着内蒙古多民族儿童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发展,塑造新时代的民族品格,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大力提升童年的文化含量,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去探究更宏阔、更长远的文化图景及精神家园。近十年的内蒙古儿童文学,在紧贴现实,积极呼应国家文化政策的前提下,自觉呼应草原文化空间中的多民族主体意识,打造了一个个既具有草原民众的特有气质,又凸现出现代儿童个性的多民族儿童形象,这其中,作为“人”的内质的“童心”的多方面塑造与映射,得到了充分发展和表现。
一、守护自然——纯真的映照
发生在草原上的动物小说一直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近十年内蒙古儿童文学的主要类型,既是对儿童文学热门题材的深度参与,同时也极大保留了内蒙古文学的草原文化特色,呼应了时代的生态主题。近十年的内蒙古儿童文学中,“严格定义”上的动物小说,即以动物为主角的成长小说数量更多,多为富有地域和民族色彩、以草原动物为主角的传奇冒险故事。在这类故事中,动物往往和人有着紧密的现实和情感关联,体现了草原民众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与动物结成的亲密关系。“许廷旺动物小说系列”中,《牧羊犬阿立斯兰》讲的是外形粗糙、丑陋、疯狂的野狗阿立斯兰对人类充满了敌意,但经过老年夫妇的耐心感化,成长为一只尽职尽责的合格牧羊犬,默默守护着老人的羊群。这个系列中的《野驴嘎达苏》《牛魔卓力格图》也是类似的故事情节,其他像许廷旺的“台来花草原动物记”和《头羊》等也讲述了狐狸、头羊、牧羊犬等草原动物如何成为人类可靠助手的艰难成长历程。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的何君华的短篇小说《乌珠穆沁的傍晚》(又名《军马穆仁》)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来自科尔沁的军马穆仁“我”的经历,“我”先后换了三个主人,始终尽忠职守地服役于每一个主人,直到退役的最后一天。这些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多以内聚焦视角描写动物的内心感受,讲述出身于草根的底层主角靠着从草原汲取而来的粗粝、坚韧、执着的良好品质,在与利欲熏心的坏人进行一次次斗争的过程中,同时在善良的人们的帮助下,最终获得生命的质的飞跃的故事。动物主角在人类的恶意与善意之间迷茫徘徊,但最终被那些拥有美好品质的人类所感化,成为出色的牧民帮手。在野性与家畜性之间摇摆的动物品性两面性的描写使动物的丰富内心得到了更全面的展示,呈现了刚柔相济的微妙美感。动物的“野性”与儿童的“玩心”有着内在的一致,动物们最终回归人类,暗喻着儿童的被规训过程。善恶二元对立的成人世界的设定,也为儿童成长带来了规避恶人的危险提示和善意感化的美德培养。
还有一类是人与动物题材小说,近十年的内蒙古儿童文学主要呈现为一个蒙古族儿童和一个幼小的草原动物共同历险的成长故事。许廷旺的“《儿童文学》伴侣”系列《黄羊》《野狼》《苍鹰》《雄豹》有着相似的情节构架和人物设置,都是以民国时期内蒙古东北部的草原和林地的土匪与土匪之间、土匪与牧民之间、牧民与牧主爷之间的复仇与宽恕的故事为主线,夹杂着人与动物之间忠贞不渝的深厚情感的建构。夏桂楣的“北方原创动物小说”讲述了草原儿童宝音和动物们共同历险和互助的感人故事。何君华的《阿莱夫与牧羊犬巴图》中,草原上最瘦弱的孩子阿莱夫和草原上最瘦弱的牧羊犬巴图互相扶持,牧羊犬为了保护羊群而对狼群紧追不舍,多日后,它出现在了阿莱夫身边,他们终于战胜了怯懦,获得了勇敢的美好品质。李美霞的《阿如汗的马》讲述了草原上的小伙子阿如汗被他的小马驹一步步治愈的故事,人与动物一起成长、互相治愈。这些作品以动物小说为载体探讨人与自然的情感与现实纠葛,引导读者对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与未来走向进行思考。人与动物在相互争夺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渐由对立走向依存的构想,寄托了作者对草原和谐生态的美好期冀。
无论是动物主角小说,还是人与动物共同为主角的小说,都体现了儿童与动物在心灵结构上的相似性,即心灵的纯真,这无疑指向人类成人世界复杂性与功利性的对立面。儿童和动物都是人类世界中体力和智力方面的弱者,在互相扶持的过程中,儿童也在动物身上学会了成长,明白以弱胜强的关键在于团结、坚强、互助、善良等人类美德,这些故事为儿童心灵的成熟提供了有益的文学濡养。故事中的动物往往是一些家畜如牧羊犬、马、牛等,它们无法脱离人类世界独立生存,以帮扶人类为自己的生存准则,这依然体现了一定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原则。还有一部分小说则超越了这样的思想局限,认为动物拥有人类无法企及的自然境界,人必须向动物学习,或与动物互相依存,或化为动物,才能实现心灵的宁静。贾月珍的《我是熊》中的林根庆干脆化为了“熊人”,在“熊体”中找到了心灵归宿。何君华的《父亲的眼泪》中的父亲,则因母亲的不理解而选择变成了家里羊圈里的羊继续陪伴家人。部分小说在人与动物的互相濡养方面持悲观心理,认为人与自然的终极对立终究不可弥合,夏桂楣的《巴特尔与小驯鹿》中,巴特尔收养的小驯鹿茸花儿始终不肯喝人类世界的水,最终渴死,它的母亲在孩子死后也自杀身死。这些作品都显示了内蒙古儿童文学领域的动物小说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对于充斥着钢筋水泥和商业气息的城市中的少年儿童来说,内蒙古的儿童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新鲜的文化窗口。这些充满了异域风味的神奇草原故事,不仅大大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也以草原文化特有的苍茫诗意、淳朴人情和野性气息,拓展着他们初出茅庐的审美体验、认知视野和精神世界。
二、向外探险——好奇的萌动
萌芽于19世纪西方儿童文学的少年探险小说,则以其精彩绝伦的探险故事充分满足和释放了儿童的梦幻激情和游戏精神。近十年的内蒙古儿童文学作家们充分利用本土独有的本民族生活积淀,开掘内蒙古特有的历史和文化宝藏,将草原文化放飞到了想象力的极致。
内蒙古儿童文学中的探险类故事中,一类以曲折情节见长,一类以奇幻想象见长。在前一类写作中,许廷旺依然贡献良多。新老两代牧民在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方面的冲突与谅解、狗和羊等家畜对人的忠贞情感、狼和天鹅等野生动物与人之间若即若离的爱恨交织、人与野兽之间无数回合的争斗与依存……许廷旺的动物小说发挥了他高超的叙事能力,在人与动物一次次的搏斗回合中,安全之后,危险接踵而至,读者沉浸在过山车式的阅读体验中不能自拔。除了动物小说,许廷旺根据长时期流传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传说,以及上世纪40年代日本鬼子入侵以来的传闻,写出了“冒险奇兵”长篇系列小说,这些作品都以小主人公林不几为主角,结合了时下大热的推理悬疑叙事手法,同时添加了很多蒙古族历史传说和风土人情的内容,大大增加了小说的文本可读性、民族教育性和思维锻炼性。许廷旺的探险故事以线性叙述模式讲述故事,契合了信息时代的快阅读方式,和当下儿童文学中热门的柯南系列动画,以及“凯叔讲故事”的口袋神探系列有异曲同工之妙,并延续了其在动物小说中表现出的极高造诣,在悬念的营造方面,尤其深得推理破案、历史探秘、野外探险等通俗文化元素之大成。此外,在内容方面,许廷旺将历史与民族传说进行了合理编织,将现实和想象、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融合了起来。儿童靠智力打击罪恶,极大满足了儿童对自身智慧力量的自信心,有助于强化儿童的道德意识,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实现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和提升。
在以奇异幻想为特征的儿童文学中,《爱丽丝漫游仙境》、“哈利·波特”系列等是世界范围内成功的儿童文学力作。近十年内,蒙古儿童文学在人与动物神思交流的奇思妙想方面,依然有不俗的贡献。曾著有儿童心理成长小说《小豆芽心灵成长》系列、少年励志小说《天使补习班》系列、《咕嘟咕嘟冒的童话》系列,获得过内蒙古文学奖第11届“索龙嘎”奖的贾月珍,与张娜合著的《小偷的花园》是一个关于爱和分享的温馨故事,讲的是杏花村里的女孩小瓶子循着杏花瓣来到院子里,遇见了神秘的黑爷爷,在黑爷爷的花园里,她发现他并不是村民所说的小偷,而是一只温暖的老黑熊,黑爷爷的魔法花园才是真正的快乐花园。马端刚的《迷失在玩偶城堡》(2013年获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里,艾玛同学参加夏令营,因一块捡到的石头而获得了上天入地的超能力,于是,他和几位同学在游戏空间里开始和坏蛋见面过招,最后,艾玛居然因为救了小魔王而和对方冰释前嫌,成了朋友。卢瑞彬(笔名:安白、默涵)的玄幻儿童长篇小说《聪聪救母遇险记》在网络连载之后获得巨大的点击量和欢迎度,并在2013年荣获全国榕树下第二届儿童长篇小说大赛佳作奖。小说借用沉香救母的情节灵感,讲述从小和妈妈相依为命的12岁的聪聪,为了给妈妈治病,在找药之旅中结识好友,排除困难,获得成长的故事。
介于幻想与真实之间的探险游戏,既能满足儿童将想象付诸行动的愿望,又能纾解儿童在现实生活中的紧张与压抑,在想象性地应对和解决成长道路中的困难和考验的过程中,自身主体性得以逐渐建构。
三、探寻自我——心事的懵懂
近十年的内蒙古儿童文学创作中,“成长小说”“校园文学”“家庭伦理小说”主要以中学生(也有部分为小学生而写)为阅读对象,更贴近生活肌理,在表现少年与成年之间朦胧年龄段的“少年心事”方面,达到了对儿童心灵的深度探询。在与父母、老师、同学、朋友建立交互主体性的同时,儿童自身的主体建构完成了最后一步,为其迈向成人生活铺垫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近十年的内蒙古儿童文学在传达正能量和爱国情怀,培养中小学生健康身心和优良品性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如春风化雨般能够寓教于乐的作品。韩静慧曾出版“神秘女生”系列和“罗比这样长大”系列,在校园文学、成长小说领域用力颇深。她的作品往往以蒙古族少年从草原走进城市的经历为题材,展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里,校园中不同民族不同家庭少男少女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在《一树幽兰花落尽》中,牧区女孩朵莱转学到北京的私立高中读高一,在适应新生活的同时,也发现了班里各个同学光鲜生活的另一面。不同的家庭氛围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性格,而来自内蒙古的朵莱,虽然一开始被大家嘲以“土气”“老实”,不久却以阳光简单、乐观善良、勤奋上进的性格和大家打成一片。“进城”的朵莱就像一面“照妖镜”,映照出了城市少年的种种“出格”行为,如追求名牌,故作老成,以“幼儿园就有初恋”为自豪,也会尝试网恋和早恋。小说使用对比手法,以温和的讽刺语调再现了当下城市少年校园和家庭生活中的社会现象,如城乡隔阂,贫富差距,师生、父女之间的代沟等。这些作品在表现儿童生活时以正面表现为主,即使涉及负面现象,也往往用美满结局一笔带过。
近十年的内蒙古儿童文学创作中,作为儿童文学的传统主题,亲情主题依然占据重要位置,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新变,呈现出了新的思想意蕴与艺术内涵。亲情对儿童而言,既可以是温暖的源泉,也可以变为压力的源头。“温暖亲情”“代沟”“家庭压力”等主题纷纷呈现,侧面体现了内蒙古儿童文学对中华民族家庭伦理传统美德的着意颂扬。父母不仅关乎亲情,部分少数民族作家还将少年的亲情追索之旅与其民族认同进行了巧妙的联结,显示了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寻根文学”的新向度。晶达的《塔斯格有一只小狍子》把小男孩追认自己的达斡尔民族之根与体认父爱的过程进行了同一化处理,他认识到了爸爸一家作为坚守在森林里的达斡尔族人的珍贵品质,内心真正认同了自己的名字和民族,塔斯格的达斡尔族认同仪式与父子认同仪式同时完成。韩静慧善于塑造鲜活的女性形象,用曲折励志的人物故事将古老的民族传统技艺和美德的传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塞罕萨尔河边的女孩》、《额吉的荞麦地》、《锔盆女孩》都是类似的主题。其中,在曾获2017年冰心儿童文学图书奖的《塞罕萨尔河边的女孩》中,塞罕萨尔河边的蒙古族女孩宝迪出生在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阿爸不允许她继承家业,她只好自学擀毡,并在阿妈的帮助下很快入门,终于得到了阿爸毫无保留的悉心教导,成长为蒙古人擀毡手艺的优秀传承者。这部小说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蒙古族青少年的人生样态,他们身上既有着老一代蒙古人的执着和坚韧,又有着新时代赋予的创新意识和革新精神。儿童文学是引导新时代儿童关注民族传统风俗和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如韩静慧的《小河马卡拉游中国:星星落在草原上》就有多样的生物物种介绍和丰富的蒙古族民俗介绍。通过这部小说,小读者会对鼠兔留下深刻印象,它的小小体格、能打地洞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要素。此外,卡拉上的第一节课,老妈妈请他们品尝了蒙古族食品,比如炒米、奶豆腐、奶皮子、黄油、炸馃子,还详细介绍了奶茶的制作过程和注意事项。还有孩子们上课时学到了蒙古包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哈那”“套瑙”“乌尼杆”,分别指的是蒙古包的支撑木架、屋顶和连接哈那套瑙的棍子。孩子们下课时热衷玩的游戏是草原上孩子们喜欢的活动,那就是“撞拐”,就是“每个人都把一条腿抬到小肚子那里,再用双手抓住,用另外一条腿蹦来蹦去,撞击其他人,最后谁没被撞倒,谁就是胜利者”。
随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儿童离开家乡走进城市求学生活,近十年的内蒙古儿童文学的作家们一方面不再用过去的刻板眼光去观照儿童的生活,而是从新的时代高度来关注、关怀已经在城市里的民族儿童的思想、情感,致力于深入表现少年儿童的心理细微处;另一方面,内蒙古作家又能充分利用自己独有的本民族生活积淀、地域文化优势,开掘本土历史和文化蕴藏的同时,不忘进行民族文化的传统教育,将多民族文化传统延伸到更为多样的艺术领域。
结语
在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论断,将美育置于重要的地位。对祖国花蕾心灵的浸润与滋长,事关国家民族的未来,如何才能在当今网络游戏与短视频盛行的精神环境中突出重围,任重而道远。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界、出版界和教育界对面向儿童的阅读推广活动越来越重视,内蒙古儿童文学以突出的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成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十年来的内蒙古儿童文学,尤其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对峙挤压与和谐共处提供了多样的文学素材和艺术经验。目前,内蒙古儿童文学已经具备了较为充足的创作梯队,如何站稳优势立场并突破固有的创作阈限,在需求持续增长的市场机制和扶持力度加大的政府政策的大环境下继续拓展艺术边界,推动艺术创新,将是下一个十年面对的挑战。儿童文学目前是一个较热的市场需求,出版社采取签约方式与作家签订系列出版的合同,使得作家缩短了出版周期,但也失去了文学创作的必要沉淀期,使得某些创作出现了雷同、模式化的趋向,儿童文学作家还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和体验积淀更为深厚的艺术涵养和人生阅历。内蒙古儿童文学应该继续丰富动物文学体类,深化草原民俗文化韵味,加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发扬生态文明精神,保持原有的文化阵地和品牌特色。此外,相较于全国各地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元态势,内蒙古儿童文学应继续在创作内容上超越原有的草原和民族类型题材,挖掘更丰富的民间、历史文化资源,在此基础上尝试探问更为宏大的人类文化难题。在儿童文学的批评方面,老一辈的儿童文学批评家张锦贻已经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示范,未来需要更多的青年学者关注内蒙古儿童文学,发表、出版更多的专门针对儿童文学的研究论文尤其是论著,形成创作与批评的良性互动。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儿童文学的故事情节还应是吸引儿童注意力的核心要素,作家应该在悬念的引人入胜、形象的丰富有趣、语言的生动鲜活等几个方面继续铺垫功力,为儿童成熟世界观、良善心性、坚毅品格等健康人性的形成铺垫精神力量。
作者简介
云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华多民族文学和思潮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