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君:我能写到今天,跟自身那种倔强的性格、执着的信念有关
作家东君近日推出了最新小说集《无雨烧茶》,“烟雨、新茶、悠长的老巷、从前的河流;董老太太、唱词先生、陶庵三老……”从这些介绍语中,我们可以读到的是浙南老城新旧更迭之下,依然有一群隐没于烟火日常、匀速生活的人。他把自己当成文字匠,所写的是“遥远的现实”。评论家张定浩说东君小说里的“旧”是有生命力的,“不仅仅是怀旧、符号化,而是在其中。那个‘旧’鲜活存在于生命中,其次有痛感,意识到很多东西在不停地消逝,不可避免地被忽略、被改变。”也如评论家李伟长所评价的:“看似优雅、看似温和的背后有着极其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构成一个小说家坚强自我的部分。”
从十来岁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从对“作家”这个词幼稚、肤浅的理解,到经过几十年,东君一直在深化对小说的认知,更在不断地跳出自己的创作舒适圈。他说目前准备尝试一种反惯性写作,“这么干,就是跟自己较劲,或者说,是让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较劲。”

作家:东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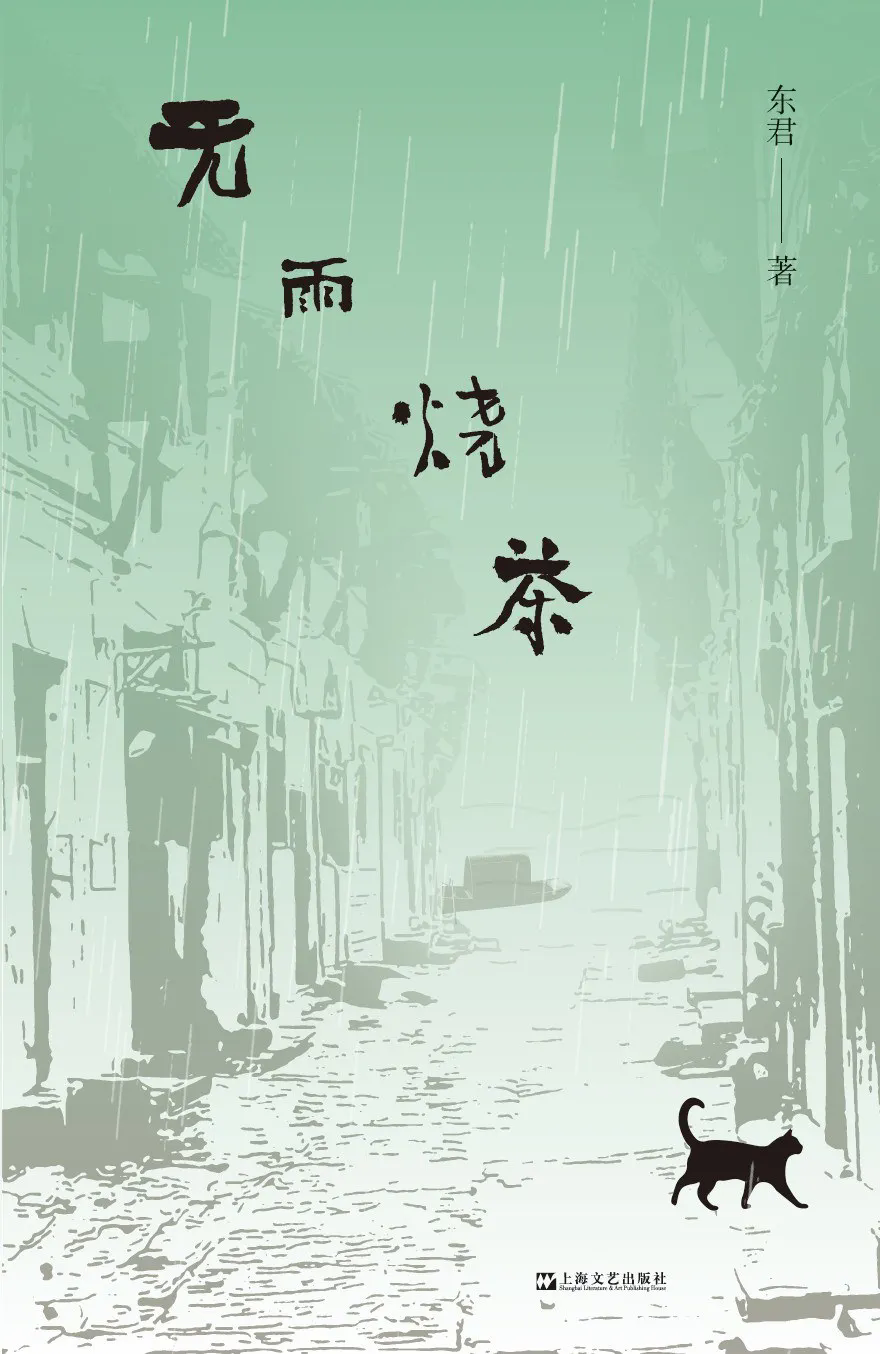
东君/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01
“努力让文字接近一种日常性,
就是为了表达生命的无常感”
记者:首先分享一点我的阅读感受,这本书确实如封面上画着的细雨中透着朦胧绿意的江南小镇,典雅而悠远。而书名也没有像一般小说集那样取其中一篇来处理,“无雨烧茶”出自第一篇小说《美人姓董,先生姓杨》,不仅代表一种场景,也暗含了对待生活的态度,可以请您先聊一聊其中的用意吗?
东君:我们知道,一座城、一座老房子都或多或少地承载着一些人的记忆,小而言之,一个字也承载着记忆。比如无雨烧茶的“雨”字,一经写出,就是给人一种淅淅沥沥的感觉,这里面有视觉的记忆,也有听觉的记忆。“茶”字拆开来,是“艹、人、木”,我们可以想象,人在草木丛中,清气浮动。一个“茶”字跟另一些文字组合在一起,足以唤起每个人不同的记忆。
是的,“无雨烧茶”,有人问我是什么意思,我既可以把它当作“黄昏红霞,无雨烧茶”这样一句朴素的农谚来解释,也可以把它当作一句无须解释的诗句。喜欢一个句子,有时候是不需要理由的。前阵子,我在上海图书馆与批评家张定浩、李伟长一起分享我的新书之后,收到了张定浩在回去的路上发来的一张上海浦东晚霞图,那时候他正要奔赴一场朋友的聚会,这幅晚霞图配上他之前随口道出的一句话:“无雨烧茶,有酒看花”就很有意思了——虽然是一句近乎玩笑的话,但我想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吧。
记者:您的小说题目有一些很有反差感,比如《去佛罗伦萨晒太阳》《我们在守灵室喝下午茶》,这是您的小巧思吗?
东君:《去佛罗伦萨晒太阳》这篇小说写的是阳光,也写阳光下的阴影部分。当一个出卖灵魂的人面对另一个出卖身体的人,他会有什么感受?他在深夜卧室里抛下钓钩,又想钓到什么?最后,解除蹲守任务之后,他为什么又要去那个小区晒一会儿太阳?我在小说中留下了一些无须解释的疑团。我总是相信,读者会比我更聪明,他们会读到背后更多的东西。但我也希望读者不要过度阐释,我写的是人性里面幽暗的那一部分,并没有试图揭露什么或鞭笞什么,小说没必要承担这种功能。
我小说里很多人物都经历了无常的命运,但他们最终还是回到了日常中去。这也是一种反差。我在小说中努力让文字接近一种日常性,就是为了表达生命的无常感。你看陶渊明的诗,写日常,也写无常。如果说,南山是日常,菊花的开落就是无常。《我们在守灵室喝下午茶》这篇小说中,茶碗是日常,高空坠物就是无常。这就好比我们刚才说的“无雨烧茶”,喝茶是日常,雨停雨落是无常。
记者:我想起了最早学习到的关于小说的定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区别于西方小说,我觉得您的作品更契合这句话。而它一定程度上又是写意的,让我想到中国古代文人画,这与您所写的地方历史、你提到的“日常与无常”等有关系,是这些传统推动您形成了您的小说气息或者说腔调?有点好奇的是,对于地方传统民俗、戏曲等搜集、记录,是什么开始有意识地做这件事的?
东君:事实上,现在的记者倒有点像古代的稗官,他们报道的东西有一部分可以归类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我写小说,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20多年前从事记者这个行当所积累的一些素材。此外,2004至2006年间走访乡间、考察风土人情、接触地方文史,也对我日后的小说创作很有帮助,那时候我编写过一本图文志。这种编写工作不同于小说创作,从纸上得来的,如果存疑,常常得去实地求证。
有一回,我听说象阳镇上有个老人,早年唱过田歌,手头还有一部手抄本田歌,就与村上一个较熟的人一同去拜访。但老人已久卧病床,他的儿子坐在门槛上,愣是不让进门,说他爹别无长物,只有这么一部古旧的田歌本子作为传家宝了。既然他看作珍宝,我们也没法子去要,只好空手回了。隔了几天,镇上有位不知名的老人竟给我送来了田歌复印本。那本子上只有寥寥几十首田歌,但毕竟是老本子。
再比如姓氏考证,就更显琐细了。我带着《姓氏探源》的初稿去双庙村拜见高益登老先生时,他说自己年事已高患有眼疾,已是“目不识丁”了。我正想起身告别,老先生喊住了我。他让我坐下来,把书稿念给他听。整整一个下午,老先生一边慢条斯理地喝茶,一边帮我订正书稿中的纰漏。2006年,编写完那本书,我忽然发现,自己这些年来其实一直倾向于民间底层的东西。我喜欢民间的俗人、俗事、俗物、俗语。生活中求的是一派俗态。我以为,把雅的东西玩熟了,有可能变俗;把俗的东西玩熟了,有可能变雅。
02
“一个城市需要一些跑得快的人,
但也需要一些‘落伍’的人”
记者:您怎么看小说与现实的关系?
东君:小说需要创造另外一种现实,重要的不是现实,而是对我们处身的现实有所发现。我们书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书写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越复杂微妙,也就意味着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越复杂微妙。好的小说能把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新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一旦写出来,就是作者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新的发现。
小说虚实相间处正是让读者引发想象的地方。小说跟现实之间必须留出一道缝隙,这道缝隙已经不是眼见为实的那个现实,而是内心呈现的那个现实。
记者:您觉得小说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
东君:小说不应该只是讲故事。故事讲完了,还留下什么?我觉得小说要达到一种理想状态,至少要琢磨这样一些问题:如何构思精妙的情节或细节使小说变得有意思;如何驱使语言,使小说变得有意味;如何布设氛围使小说有意境;如何从形而下的描述中寻求一种形而上的意义。
记者:现代社会一切都讲究快节奏,我们总觉得被某种东西裹挟着向前,但您仍执着写一些慢的人和事,做快时代里的慢者,也许可以为年轻读者分享一下心境?
东君:在现代社会,我有时觉得“守旧”未必是件坏事,我就喜欢那样一种择一城终一生的恒定生活,喜欢传统的日常起居方式,不想改变太多。现在有太多的高科技产品进入生活,我们的脑子经常要更新,于是就可以看到身边很多人都被一股潮流巻裹着往前跑,很少有人会有意识地后退或原地不动。我倒是觉得,一个城市需要一些跑得快的人,但也需要一些“落伍”的人。
记者:有很多作家是离开家乡才能书写故乡,但您是身处其间,您怎么看作家与故乡的距离?
东君:我举两个例子。有一回,加拿大籍华裔作家张翎跟我聊天时说,她在美国援华海军情报部门退役军人的回忆录中发现玉壶这样一个山村,这地方先归属温州瑞安,后归属温州文成,抗战时期,谁也没有想到,在那里,美国文化与中国乡村文化发生了碰撞,她为此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劳燕》。
同在加拿大的陈河谈到小说《甲骨时光》的创作缘起时说,他在一本有关甲骨文研究的书中了解一位最早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的外国人,他就是加拿大人明义士。他读了明义士的自序,激发探究此人的兴趣。他在加拿大继续寻找明义士,以及与明义士有关的加拿大人的资料,而且还颇费周折弄到了一本董作宾《历谱》的光盘。甲骨文的书我读过一本,那就是温州大儒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我当年半懂不懂地读了这些学术著作,无法把它转换成小说题材,可陈河就有本事把明义士、董作宾这些人放到一起,借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他跟这些人也应该有前世今生的联系。
阿河、张翎因为离开故乡而找到故乡,并且发现故乡。这个故乡已经内化为文学意义上的故乡,有其自身的地理方位和风土人情。
写作者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在故乡的异乡者,一类是在异乡的怀乡者。有时我想,一个好作家与故乡之间,也应该保持着这样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老家,有些事因为空间距离太近,反倒不好写,因此我就在小说叙述中有意拉远了时间的距离。有了距离,就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03
“我从来不会相信灵感降临这种鬼话,
更不会坐等”
记者:我看到一篇采访里您说:“我真正自由的写作时间就是2010年到现在,以前都是在动荡不安的生活里写作。”2010年前与后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对您的写作有造成不同影响吗?
东君:我小时候就以文学为志业,但那时候的确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离开文学太远,就变得一事无成。所以,我又决定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写点东西。
2010年我辞职后,首先是感觉自己可以不把失眠当一回事了,其次就是感觉自己可以主动支配时间是一件无比自由的事。有一回,我对小说家钟求是说,以前我总是一点一滴地挤出时间用来写作,现在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就像口袋里揣了大把大把的钱,花掉也就花掉了。钟求是当时经常为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听了我这话,心里不知有多羡慕,后来就把我的原话转告给那些决定辞职但又下不了狠心的作家。
我当专业“坐家”十几年,原本以为自己以后可以写出更多的作品,但事实上,我回头检点,发现自己每年的创作量从来没有超过10万字。10万字好像成了我的创作上限。有位老朋友,喝了酒之后就会拍拍我的肩膀,让我赶紧写一个长篇。三年前,我的长篇写了三分之一,三年后,它仍然安安静静地搁在抽屉里。当然,在这些年,我也没闲着,除了小说,也写了一些杂七杂八的文字。
记者:您提到了被搁置的长篇创作,目前您发表的大多的创作是短篇小说,我也看到您说尝试过后反而认清自己更适合在短篇领域深耕。那我们知道有很多如鲁迅、汪曾祺、卡佛等文学大家,一生都只创作短篇小说,在您看来,决定一个作家写作类型的有哪些因素?
东君:从写什么到怎么写,很多小说理论家都谈到了,但作家可以谈谈他“不写什么”。有些小说家,像汪曾祺,就写短篇小说,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写些别的,他说别的小说自己不会写别的。不写什么也很重要。有些东西,超出他精力范围的,他不打算触及。还有博尓赫斯一辈子就写短篇小说,他认为长篇小说就是纯粹的堆积,这就意味着“不写什么”。
小说有它的常道与变道。不管是短篇、长篇、中篇,体量各有不同,但有些东西还是趋同的:比如意思、意味、意境、意义这四方面,前面我也提到了,现在可以展开讲。
先说意思,情节的推进,有些小说家玩得特别好,故事讲得很生动,也有细节捕捉能力,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意思。那么意味是什么?在意思之外有意味,它只是一种语言营造出来的氛围,意味附着于语言,又不可言传。意境更不好谈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好像只有中国古典诗词讲究意境的,在我看来,如有必要,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也可以讲究意境。最后谈谈小说的意义,小说不一定要归纳出什么意义,但小说如果有什么意义话应该是这样的:它不仅仅要表达生活中一些表层的东西,还要挖掘生命里一些更为深层的意义,甚至还可以探讨自我意义、存在意义。所以,你可以把小说的类型明确的划分为短篇、中篇、长篇,但上面这些基本质素是不变的。
记者:回到您第一次真正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是什么时候?由于自媒体等兴起,成为职业作家在现代社会看似更简单了,但不可忽视的依然是这条路其实很艰难。
东君:10多岁的时候,当我写出了一些老气横秋的句子,我就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了。可我那时候对“作家”这个词的理解还是显得过于幼稚、肤浅了。事实上,我是系统的“局外人”,也没把自己当作一个作家,我感觉自己跟身边那些手艺人没什么区别,充其量只是一个坐在家里的文字匠。
是的,这条道路变得越来越艰难了,但我也有一种“吾道不孤”的感觉。我能写到今天,没有放弃,除了一点运气之外,还跟自身那种倔强的性格、执着的信念有关。
记者:灵感也许是一个作家可遇不可求的,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个您印象深刻的,灵感降临的故事吗?
东君:“灵感”这东西有时就像男女谈相亲时说的“缘分”,你真的会相信?写作需要的是一种持续、稳定的状态。我从来不会相信灵感降临这种鬼话,更不会坐等。
记者:最后更新一下您近期的写作状态?
东君:只要体力、视力、精力尚可,我仍可以保持匀质、定量的输出。我注定不会写得太快。近期在写一些篇幅更长的作品,进展依然很慢。写作的乐趣就在于,你在写的过程中不知道这个小说会走向哪里,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写完《无雨烧茶》这本书,我打算寻找另一个主题、另一种写法,我现在在尝试一种反惯性写作,这么干,就是跟自己较劲,或者说,是让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较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