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2024年第7期|刘汀: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节选)
一
预 感
里尔克
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
我感到阵阵来风,我必须承受;
下面的一切还没有动静:
门轻关,烟囱无声;
窗不动,尘土还很重。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来又卷缩回去,
我挣脱自身,独自
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
这是北岛翻译的里尔克的一首名作,其中的一句“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更是名句。这句诗,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安置了人、海和风暴的关系;当然,在本质上风暴和海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也相当于倒转了人和海的关系。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认知中,从来都是人因走近海而激动,把大海当作审美对象进行观看、认识和描述,现在,通过把人和大海同构的方式,里尔克让大海具有了主体性,甚至是比人更高一层的主体性。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这句话是在宣告,我(人)的激动,是对大海的激动的模仿,激动的动因却又在风暴。所以,对于人来说,大海是先在的,是它首先认出了风暴,也是它告诉人风暴的力量何在。
这是做一个读者的读解,它无疑是极其个人化的。我更想说的是,我们和大海的关系,常常是借用语言尤其是诗歌来表达。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没有诗,也就没有海。
我出生在内蒙古的北部地区,那里多是山岳、原野,再往北一点儿,是无边无际阔大的草原,和海毫无关系。而我最初认识的海这个字,却是和草相关的——草场像绿色的海洋,某篇文章里的句子,展现于少年的我的眼前。所以,在最初的想象中,海不过是蓝色版本的液体的草原。我能想象出来的最大的浪涛,也只是劲风吹拂、青草垂首的姿态。好在,只要风足够恰当,草足够高,草原的确能模仿海上波涛的模样。绿色席卷而来,某些芦花随之跳跃摇动,仿佛是银白的浪花。在这个意义上,海确实比草原更具终极意味,草原有一岁一枯荣,而大海从不止息。
我无法记清自己是否站在草原上想象海的样子,但是我站在海边时,的确回溯了少年时望见的风吹草低的场景。真奇怪,从没有人反过来说海是蓝色的草场。或者,是因为在人类的认知中,海常常被当作是终极象征物——无边无际,神秘莫测,不可捉摸,柔软与坚硬、平静与狂暴并存,百川东到海,海枯石烂,天涯海角。万事万物,哪怕是高耸的山岳,一到了大海的面前,都自动变得渺小和短暂,仿佛只有大海才称得上永恒。因此,海是那个生发一切的本体,余者不过是千变万化的喻体。
几年后,我们在中学的课堂里大声背诵高尔基的《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在铿锵的语调里,狂暴的大海不管升腾起多么凶猛的浪花,都不过是衬托海燕的背景,甚至它愈是强大,就愈显得海燕的无畏。我们的音高和高亢情绪表明,在所有孩子心里,小小的海燕战胜了大海,人人声调激昂、词语铿锵,仿佛即便那时真的置身海上,也会像海燕那样充满对暴风雨的蔑视。风暴、海、人,都在,但那样的时刻和语境下,它们全部笼罩在一只燕子的羽翼之下。这一点,庄子早就说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我们看见了风暴,但是并没有认出它,或者说,并没有认出它也是一种意识、一个主体,而只把它作为要战胜的某种力量对待。因此,也无人像大海那样激动,我们的激动只是想象的激动。
再后来,我和无数同龄人飞离草原,在城市的人海中沉浮之时,读到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终于,人与海的故事无需再借助一只燕子来讲述,他们短兵相接了。一个老人与一片大海,二者开始了漫长的搏斗。老人一番努力之后一无所剩,大鱼只有森森白骨,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绝不服输的倔强,也让大海无法获得真正的胜利。在这时,我蓦然发现,自己并不是海燕,并不能真的超越和战胜大海的风暴,但我们保留着仅有的尊严——至少和它势均力敌,至少和它两败俱伤。
其实,从海燕到老人,也几乎就是我们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的衍变。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段,我们所秉持的理念就是人定胜天,人类不但能战胜自然而且可以利用自然。我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把大地掘开,将里面黑色的煤、白色的银、黄色的金以及其他种种颜色的矿物挖出来,变成火,变成钢铁,变成高楼大厦;轮渡开向大洋深处,打捞出成千上万种鱼虾,让它们的蛋白质和脂肪,化作我们的肌肉和纤维;砍伐原始森林,让那些悬铃木、红杉、松树,经过刀砍斧凿之后化身精美的家具……然后呢,人类突然有一天惊讶地发现,这一切并不是取之不竭的,大自然可能会还以暴雨、海啸、地震。于是,人类不得不向后退了一步,妥协了——我不战胜你,我们势均力敌、握手言和吧。
是的,我们终于开始认出它,因为我们终于开始重新审视最古老的那句箴言:人啊,认识你自己。
二
生命短暂,大海永恒。
曾经的大航海时代,把整个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那些随着洋流在地球上无限涌动的水所走过的路程,终于有了人的足迹。海航者踏浪而行,随之而来的当然是改变——他们和我们,这已有无数部史书去描述。在文学中,在诗歌中,从古代的史诗到现代派作品,大海始终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几乎没有哪个作家或者诗人,终其一生都没有写到海。海是所有创作者命定的主题之一。
阿贝尔·加缪说:“我最喜欢的十个词:世界,痛苦,土地,母亲,人,荒原,荣誉,贫穷,夏天,大海。”大海不是第一个,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常常比第一个更具选择的艰难性,在这一刻,你必须排除世界上的万千词语,而只留下一个。所以,大海就用它庞大的体量和无尽的想象,堵住了这扇门,从此,再没有什么词语能挤进这跋涉的队伍。这是一种拒绝,也是一种孤独,在西西弗斯的苦役中,根据太阳理论(solar theory),他的重复,代表的是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或者是潮起潮落,甚至就是危险大海的人格化——海水永恒地拍打着堤岸,浪花永恒地卷起又落下。但是加缪告诫过人类:你要去想象西西弗斯的快乐。世人总以为他的苦役只是苦,却不晓得他正因如此而感到充实,在现代生活中,充实已是最高的意义和奖赏。因为,我们命定的事物已经不是潮汐涌动的海,而是被掏空的海——空虚。
伟大的提示。我由此更加热爱每天重复的生活,或者说,有规律的生活。我喜欢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像另一种机械化,但我并不反对变化。就像希腊神话和加缪从来没有说过,那块巨石必然按照同一个路线滚落,应该是,每一次它被推上山去或者从山上滚落,都必然有着微小的差异。那么,我热爱的就是这种重复中的微妙差异,浪花都是浪花,但是没有任何两朵浪花是相同的。大海因浪花的不同而千变万化。
日本诗人寺山修司有一首《最短的抒情诗》:
眼泪
是人类自己做出来的
最小的
海
看,当人们终于明白,自己终究战胜不了大海之时,他就会动用属灵的物种独有的武器——审美。马克思说,美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那么,审美也就是把外在的事物用审美的方式,变成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努力要把大海纳入到脑海中来(看,脑海这个词,也是其中的例子)。你如此庞大,如此浩瀚,如此变动不居,那我就真诚地甚至是孩童的恶作剧般地,用最小的液体来代替你——眼泪。怎么样?悬千钧于一发,用一个支点撬动地球,审美确实具有这般威力,又何况,眼泪和大海之间还有另一个真正的相同之处呢?它们都是咸的。咸不是一种味觉,是所有味觉,在人类的历史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盐都曾经是最重要的物料。没有盐,所有的其他味觉都将失去基础。没有盐,大海就成了普普通通的水。
三
再读一首诗吧,韩东的《你见过大海》。这也是一首名作,它和《大雁塔》一起消解了我们曾认为是无比崇高的两样东西——自然和历史。我们只说前者。
你见过大海
你想象过大海
你想象过
大海
然后见到它
就是这样
你见过了大海
并想象过它
可你不是
一个水手
就是这样
你想象过大海
你见过大海
也许你还喜欢大海
顶多是这样
你见过大海
你也想象过大海
你不情愿
让海水给淹死
就是这样
人人都这样
这首诗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那时候,在整个中国尤其是思想界、文学界,正是伤痕、寻根、先锋等思潮一波接一波海浪般侵袭之时。经历过特殊年代的心灵和头脑,不断从所有的事物里寻找价值和意义,我们似乎找到了——传统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形而下的,形而上的。
但与此同时,敏感的诗人们却感受到了反方向的牵引,那些古老而恒定的意义真的存在吗?那些所谓进化论的价值果然如此吗?那些被无数人认证的事物就是它们本身吗?
比如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操的眼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日月星辰,都像是从海中而生。在“海上生明月”的时代,因为“共此时”,天涯就是此地,天涯和此地因为一个“婵娟”而消弭了千里之遥。甚至到了海子生活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海仍然是那个阔大、包容、神秘的抒情客体,是我们“本质力量”最好的审美对象,七月的大海,你面朝它,就会春暖花开。在所有类似的诗句中,大海都置身于崇高的抒情位置,或者被当作是另一些崇高事物的象征物。它代表着时间和空间的结合点,代表着情感的四海皆同,代表着内心的律例,代表着感情的纯粹和浓烈。我们已经在这种表达中生活了几千年。
再亮的光明之下,都会有影子。即便是手术室的无影灯,那些影子也只是被遮蔽,而不是不存在。大海也一定有自己的背面,并且,如果它是有灵的,在负担了几千年的抒情、隐喻、象征,在承载了过多的政治和文化期待之后,它会不会感到疲惫?它会不会早已不堪重负,渴望解脱?
韩东的诗仿佛在唱反调,那些我们所天然认为的崇高之物,一旦你真的去亲近了、认知了,就会发现它们“不过如是”。或者说,所有的价值和意义都是在想象过程中建构出来的。答案就在最后几句里:你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也就是说,当人直面生活的底片之时,你看到的只有黑白二色,再崇高的抒情,也要在不被淹死面前败下阵来。诗中所指,当然是我们人类自身,但也不妨看作是给大海松绑,就让那些水回到水本身吧,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多地回到我们的本身。
那么,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人,普普通通的人,在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中挣扎的人。“我见过大海”这句话的核心词语,不是大海,不是见过,是“我”。我重新成为主体,而且是一个光溜溜的、没有任何文化和意义贴片的主体,匮乏、庸常甚至虚无,但这一切都是自生且自有于我的。人类从海里走上岸,大海也获得了解放。那这一刻,大海还会激动吗?
其实,问题不应该这么问,应该问的:大海还在乎吗?
它自生且自有它的风暴。
只是在诗歌中,大海亦经历着起伏如此大的变奏。不同的时代,大海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是有效的,最终形成有关海洋的合奏。
四
我见过大海。我想象过大海,然后我见到了大海。
就是这样。
第一次是在2002年。我大二,于一个深秋告别同学,孤身一人坐火车到了山海关。傍晚,我乘坐拉客的三轮摩托,抵达老龙头。此处是万里长城的入海口。
我站在老龙头边上的海水里,极目远眺,试图把从书本上读到的大海的信息全都看出来。许多诗句涌现,但是都如海风一般,即吹即过。
我放弃从记忆中寻找对应的努力,把精力集中于真实的景物和切身的感受。
我看见了无尽的海水,它并不是蓝色的;我看见了货轮在水面行驶,没有汽笛响起;我看见海风凉凉地从远处吹过来,没错,是看见海风,因为我的眼睛能感觉到那种凉意;我看见夕光在隐匿,失去了光,大海正一点一点吞掉自己的身体。是的,我没有看到黑色闪电般的海燕,没有明月从远处升起,也没有任何当年背诵课文时的激情澎湃。那一刻的感受,似乎更贴合韩东的诗句:你见过大海,就是这样,人人都这样。
2018年,我带着家人去大连,其中一日流连于老虎滩的海边。女儿挖沙子,父母和妻子光着脚走在海水中,我在旁边看着他们,给他们拍照。那处海滩并不适合游玩,没有细腻的沙粒,遍地鸡蛋大小的鹅卵石,走上去很是硌脚。因此,人们都玩得小心翼翼,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快乐——也许,这快乐的很大一部分来自表演,一个人到了海边,总得拿出点儿情绪来,孤独的人就演忧伤,幸福的人就表现快乐。而我的感触,只能建立在父母妻儿的感受之上,这是他们第一次看海,第一次被海水清洗脚踝。他们和女儿一样,都是没有被有关大海的文学浸染过的人,因此,对他们而言,海从来就只是水,陌生的水。因为陌生,格外亲近。
后来,我带着家人还去过鼓浪屿,去过北戴河,去过青岛,都是有海的地方。海各不相同,一家人出游的情绪却是相似的。这些时候,大海和一条江、一支小溪,似乎也没有多少差别。所以,与其说是我带着家人去看海,不如说,我要把家人介绍给大海:嗨,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妻子,这是我女儿。
我隐藏的话语是:这是我。我是今天的我,皆得于亲人的塑造。
还回溯到2017年。秋天,我出了一次公差,去俄罗斯。其中的一站是游访彼得堡的夏宫。我记得夏宫院子的某一处红砖墙,正临着波罗的海。我们去的时候是深秋,风已经吹出了相当的劲头,那天又是整日阴沉沉的,偶尔飘起细雨。站在夏宫的院墙里,波罗的海的海水就在脚下翻腾,远望过去,能看见海面上一波又一波的潮涌,那些浪花打在岸边的礁石上,碎成千万白银的泡沫。这些虚无的泡沫退回海中,重新聚集为水,再次袭来。
有海燕吗?我记不清了。但是我的确想起了《海燕》,波罗的海的波涛很大,每一波都摆出席卷一切的态势。这些波涛积蓄到一定程度,又刚好遇到一股劲风,就会形成风暴。
我认出了风暴。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就是在这一刻,我彻底认领了这句诗。
……
—— 全文见《草原》2024年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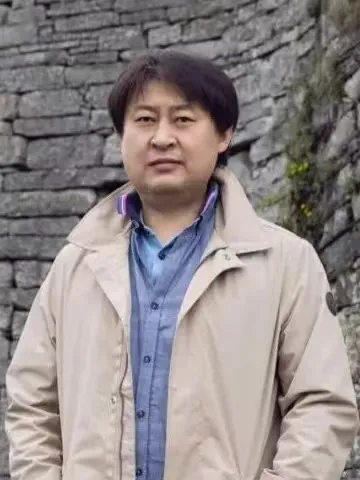
刘汀,1981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文学博士。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散文集《浮生》《老家》《暖暖》,小说集《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中国奇谭》《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诗集《我为这人间操碎了心》等。曾获丁玲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陈子昂诗歌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