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井小民到帝王将相,他笔下不变的是人性的光辉

活动现场
刘恒在中国编剧界是非常“独特”的存在。他横跨作家、编剧、导演三个不同领域,无论创作小说还是写剧本,都手到擒来,横扫多部奖项。“文学于我而言是匕首,老了以后文学是拐杖”。在已古稀之年的刘恒眼里,文学是人类追求高尚品格和人性至善的工具,让人在世俗的泥潭里依然保持超拔的姿态。
5月26日晚,由中国作协社联部和北京电影学院共同主办的《北影大讲堂:文学与电影》顶峰对谈系列第7期《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世俗》在京举行。著名编剧、作家刘恒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德濒就“影视与文学创作”等话题分享经验。夏衍电影学会会长、原电影局副局长、中影集团原总经理江平,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智勤,中国作家协会社联部主任李晓东,北京影协秘书长陈杨萍,北京电影学院党支部书记支宏伟,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李伟等参加活动。据悉,“顶峰对谈系列”获得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注,已连续三期排名抖音同城直播榜前20名,总六期全网各平台有效观看近5100万人。
江平表示,刘恒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一直走得稳、准、踏实,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捕捉闪光点写进小说、搬上银幕。他的文字扎实,能够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生活,同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人类的共性。他希望每一位电影人都应当如刘恒一般,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
李晓东谈到,文学是文化领域最基础、活跃的力量,形态丰富的文学作品为中国影视转化提供重要支撑。“顶峰系列对谈”活动为作家、编剧、导演和学者们牵线搭桥,让不同的行业领域专家产生思想的碰撞和交流,这不仅为文学影视的发展贡献力量,也进一步推动中国影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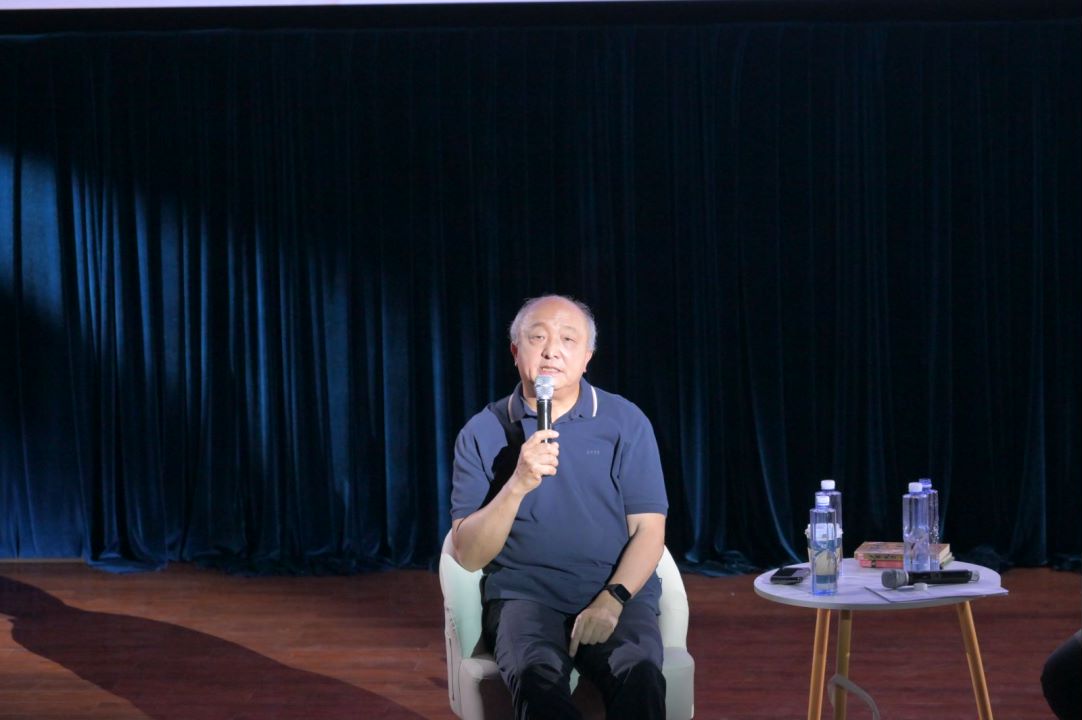
刘恒
激情燃烧的岁月
刘恒本名刘冠军,15岁当兵后阴差阳错之下开始喜欢文学,为了鼓励自己要持之以恒追求文学事业而起笔名“刘恒”。《黑的雪》是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彼时成名作《狗日的粮食》的发表给他很大的鼓舞,他迫切地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创作力极其旺盛,《黑的雪》仅用一个多月便写完了。他在热爱文学的最初阶段也喜欢电影,从电影到小说,再从小说到电影,兜兜转转,不曾放弃,二者仿佛有着“宿命关系”。
自初踏文坛以来,刘恒每构思一部作品,都会躲进某个封闭式农家小院,一边吃泡面,一边忘我地“沉浸式创作”。小说《黑的雪》所体现的孤独感,恰好展现刘恒在青春期末尾之时,经历生活的摸爬滚打、遍体鳞伤之后对人生的新认识。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大众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财富机会层出不穷,所有人都卷入竞争。人与人之间激烈的碰撞、青春期的迷茫、为追逐欲望而“头破血流”……这些都被刘恒写进了小说中,其中所展现的精神“虽然很肤浅,但最突出的感觉是挣扎感,一种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夺取位置要付出的坚韧努力。”
创作小说《本命年》时恰逢1989年年初,王朔、海岩、刘震云、刘恒等人组建了海马影视创作室日后大众耳熟能详的《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均出于此。那是一段激情勃发的创作时期,几位年轻人为了共同的文学梦想、影视梦想走在一起,他们笔下的人物多为社会的边缘人,展现社会高速发展之下个体意识的觉醒。
刘恒认为,和那时相比,当下创作环境更加浮躁,从业者的创作心态急功近利,包括利用技术性手段对观众喜好过度揣摩等。个体很难改变环境,创作者要依靠坚韧的努力适应这一变化,不要过度沉溺于抱怨、埋怨、躺平。
从市井小民到帝王将相
刘德濒观察到,从早期编剧作品《秋菊打官司》、《菊豆》到《集结号》、《少年天子》,刘恒的创作经历了展现市井小民、平民英雄、帝王将相三个阶段的转变。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生动展现一群生活在胡同里的老北京人的生活,其中“张大民”的形象更是无数老百姓的缩影。刘恒谈到,电视剧中大量生活细节都和自己的大杂院生活有直接关系。曾经为了刘恒结婚,家里将葡萄藤砍断,勉强腾出狭小的空间建婚房,但葡萄藤继续生长,办婚礼时葡萄藤竟然把水泥地拱开了。虽然年轻时生活窘迫,但刘恒并没有太为钱所困扰,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除了乐观强大的内心作为支撑,能与亲人一起同甘共苦是幸福的重要源泉。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刘恒将创作视野延伸至更宏大的历史背景,集中创作了《张思德》《铁人》《集结号》等多部电影剧本。一直以来,张思德都是刘恒心中当仁不让的英雄,他希望自己也能怀揣理想,为共同事业贡献力量。投入创作后,他每天早上一睁眼脑海里都是张思德的形象。他将自己当兵的经历、父亲虽笨嘴拙舌但内心善良的警察形象都融入对张思德这一人物的塑造中。回忆起那段创作经历,刘恒认为当时条件虽然艰苦,拼命创作虽然令人感到痛苦,但灵感的迸发却是对写作者最大的奖赏,在作品完成后,他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快乐。
刘恒自称自己创作所关注的主题始终未改变,那就是死亡。他在当兵时曾突然被告知姥爷已于半年前去世。因自幼和姥爷感情深厚,姥爷的去世让他第一次对死亡有了感知,也促使其对死亡产生深切的思考,在创作中密切关注死亡这一文学永恒的主题。
刘恒早期的文学作品《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力气》展现了乡村的三种死亡:为粮食而死、为性而死、力气耗尽而死。在他做编剧的《少年天子》中,死亡主题也始终贯穿全剧。拍摄过程中刘恒父亲病故,在拍摄现场写到死亡段落时,他因思念父亲泣不成声,又怕哭声影响演员,只能拼命憋着,这也让他透彻地理解人物状态,剧中人物仿佛在替他完成某种任务一样,为他排解痛苦、抚慰灵魂,促使他找到了某种意义和光亮。《少年天子》的40集剧本没有梗概,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在他看来,畏惧死亡是人类永恒的困境,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隐喻:最终目的无法实现,因为欲望永无止境,永远得不到充分满足,死亡便是最直接的证明——人类无法永生。即便是帝王将相,也必须经受生活的洗礼或折磨,无法随心所欲而活。
“写作者是幸运的,虽然肉体被死亡终结,但仍然可以在精神世界里留下痕迹。如果创作达到了优秀甚至不朽的程度,所塑造的人物依然存于后世,这就意味着创作者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得以延续和永生。”刘恒说到。
电影剧本是电影的“墓志铭”
刘恒曾与多位著名导演合作并结下深厚的友谊。此次活动发布的视频中,谢飞、张艺谋、冯小刚、尹力、沈好放等导演分享了对刘恒及其作品的印象和感受。大家认为,刘恒的作品能够精准地把握人物的性格,充满对世间的关爱,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谈及写小说与写剧本的区别,刘恒形容小说的文字像“砖瓦”,当作家完成作品时,由文字构成的“建筑”是完整的,属于作家个人。每一位读到作品的人都可以通过文字想象一个与之有关但又各不相同的、属于自己的“建筑”。剧本所呈现的是“建筑”的图纸,描绘线条、尺寸、结构、细节,真正的成品是电影。当电影这一“建筑”完成后,影像便固定下来,这与小说给读者的感觉全然不同。他将电影比作剧本的“墓志铭”,电影一旦上映,电影剧本也就被埋葬了。
当下影视界普遍存在编剧不受重视、地位不高的现象。刘恒表示已见怪不怪,应当“双向”看问题。电影界与编剧的矛盾关系令优秀的创作者敬而远之,电影界对编剧的歧视也是“回旋镖”,这导致优秀编剧外流,整体水平下降;同时编剧达不到电影这一艺术形式表达的要求,也就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对编剧来说,更主要的是靠自身的创作实力立足。
刘恒非常推崇张艺谋对自身职业特性的清醒认识。在他看来,张艺谋创作始终保持初心,努力按自己的理想目标前进,“跌倒爬起来接着向前走”,不被舆论、评价所左右,在不断地行动中纠正艺术追求中出现的偏差。“行动对创作者来说至关重要,作品本身的优劣高低可以评论,但是这种创作姿态和努力值得大家学习。”
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世俗
几年前刘恒的母亲去世,他看着母亲的遗体顺着传送带被火化,内心感受到的不再是悲伤,而是一种顿悟。将逾70岁,刘恒强烈地意识到余生已所剩无几,开始思考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抓住什么、放弃什么。他的内心变得更加温暖和包容,“要善待自己的合作伙伴,不要过于计较,常怀感恩之心。让身边人感到温暖,哪怕点滴幸福也值得珍视,这也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刘恒认为,人道主义是一种理想和浪漫主义,世俗则是实用和功利主义,人类永远在矛盾中生存。人道主义精神对文学和作家至关重要。让人类能够怀揣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生活,追求人性的高尚与纯粹,这也是他秉持的写作态度。他希望创作者要对外部现实保持敏锐观察,对内保持自省和自律,将远大的目标落实到行动中,即便跌倒、被践踏,也要意志坚强地站起来继续行进,即使失败,也虽败犹荣,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