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一蓑烟雨》受业内点赞 梁平:在写作中建设自我人格并重新体认家国与个体精神的宽广存在
在世界读书日到来前浓浓的书香氛围中,深度读一本诗集,是一个好选择。4月22日,“风雨有晴,诗意走马江山——梁平诗集《一蓑烟雨》新书分享会”在阿来书房举办。作家阿来、诗人娜夜、诗人向以鲜、川大教授周维东、西华大学教授王学东以及来自四川文艺出版社的《一蓑烟雨》责编周轶,与诗人梁平一起,在诗人熊焱的主持下,围绕《一蓑烟雨》的写作展开深入的交流和分享。大家谈到写作的中年变法、持续写作,人文地理与诗歌的关系、语言的当代性,以及如何拓宽写作的视野和格局等话题。

梁平(左3)在分享
2024年3月,梁平的最新诗集《一蓑烟雨》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书中收录了梁平近年来的百余首现代诗歌,其中包括《水经新注:嘉陵江》和《蜀道辞》两首小长诗。整本诗集显示出非常清晰的诗学路径自我确认,从2017年的《家谱》、2020年《时间笔记》再到2024年的《一蓑烟雨》,梁平的诗歌地理学在这三本诗集中,既有变化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地理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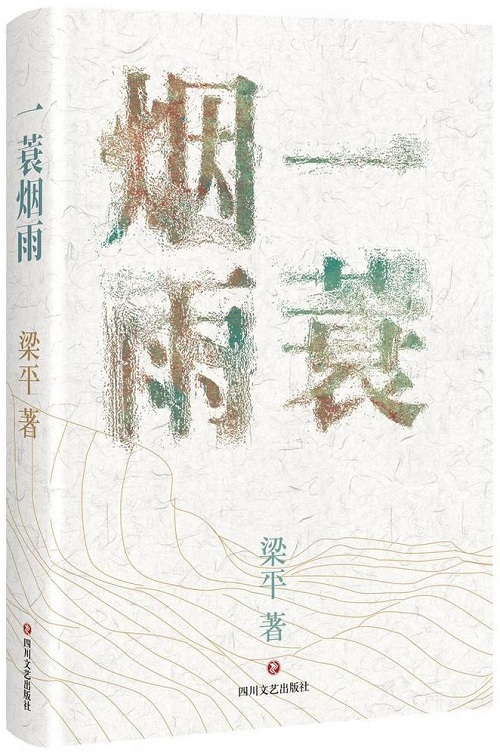
梁平诗集《一蓑烟雨》(四川文艺出版社提供图片)
阿来:梁平诗歌中的人文地理的写作方向,非常值得继续探索
作为早期写诗后来成功转型写小说的阿来,他首先回顾和梳理了他在过去几十年跟梁平打交道所了解到的其诗歌写作的脉络变化,并且延伸谈到诗圣杜甫的作品对成都人文地理美学塑造的贡献。对于《一蓑烟雨》里的写作,阿来说,“写《水经新注·嘉陵江》《蜀道辞》,这些地理人文系列的作品,我都觉得非常好。尤其是在题材确立精神向度的拓展上,是非常值得继续探索的好路径。”作为梁平的多年好友,阿来也给梁平的诗歌写作提了自己的“一点意见”,“虽然在年龄上算是一个老年人,但其实写诗可以‘老夫聊发少年狂’。有些诗,我觉得可以再多几句,写得更松弛一些。这一点,可以向聂鲁达、惠特曼学习。我也非常期待梁平的下一部作品。”
作为一名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诗人,梁平的写作依然保持旺盛的状态。这种写作状态,在向以鲜看来是一种“持续性写作”,“跟青春期写作不同,‘持续性写作’不是靠着天生激情和青春期的能量写作,而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成熟状态。这是更难达到的境界。”周维东和王学东则分别从专业理论的角度,对梁平的诗歌创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周轶是梁平《家谱》《一蓑烟雨》两部诗集的责编,对于梁平的诗歌风格有很深的感受,“宽阔沉稳、深入浅出。他写出了深刻的东西,但是语言不艰涩。可读性很强。梁老师不仅是诗人,而且也是优秀的文学编辑。在跟他一起合作做他的诗集过程中,非常理解和配合我们的工作。”
娜夜: 构建出一个诗人的“精神地理”长诗成功写出“代入感”
梁平的诗歌看得见地理、人文、历史,这在新诗集《一蓑烟雨》里体现得尤为明显。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娜夜,在发言中首先点赞《一蓑烟雨》“很漂亮,封面设计风格很清新,内容跟形式很一致。”她接着提到,读一首诗,一部诗,“我们最想知道的是:作者在关注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关注?梁平先生这部诗集可谓是一个诗人的‘精神地理’,是与地域有关并超越地域的文学精神,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诗意升华。自然与人文互为镜像,互为语境。这本诗集是历史的、遗迹的,同时也是现代的、当下的。这里面的诗歌大部分与地域有关,但又超越地域,对地理有诗意的升华。梁平先生写梁湾村、嘉陵江、成都杜甫草堂,都是他朝朝暮暮的生命情怀之作,如他所说是‘根上结出的果’,而非采风和过客的即兴成诗。”
娜夜提到,这本诗集中有许多场域是已经被许多诗人多次抒写过的,要出新并不容易,“但梁平先生显然做了充分准备。他找到独特的角度、视野,并且语言上深入浅出,这是诗歌创作的良好品质与境界。我认为,梁平先生这部作品中,很好地践行了他一贯坚持的诗学主张。”
娜夜已经读了两遍《一蓑烟雨》,“有很多感悟。有些好句子是诗人本身的情致促生的。比如他写子期和于伯牙,结尾这样写:子期,我拿一整条江敬你。全书中像这样的水到渠成、突然拔地而起的句子还有很多,满足了我作为阅读者的期待。“
作为一个诗人,娜夜也注意到,梁平在这部诗集中,“细节的处理和选择,非常讲究、可感,有心领神会的弦外之音。这是一个好诗人的功底所在。”
娜夜还特别分析了诗集中收入的、引发很多人解读和共鸣的长诗《蜀道辞》,“这首诗读起来,代入感很强。要写好一首长诗,能否写出‘代入感’,起到决定性作用。这首诗的技术支持恰如其分,使整首诗想象力飞扬又张弛有度,又不乏意趣,激情又十分克制,真的是一路‘大步流星’而非‘磕磕绊绊’。他写得想象力飞扬,张弛有度,全书气脉灵动,似乎都在他手里攥着,中途没有磕磕绊绊 ,这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境界。”好诗对读者也提出不小的要求。“这首诗需要读者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更深解读出所拓展的精神时空,和辽阔诗意。”娜夜说。
一个诗人的写作来路跟成长经验高度相关
梁平回顾生命的青春岁月
作为分享会的主角,梁平在本次活动最后环节发言中,首先表达了感谢,“感谢出版社,也感谢我们在座的嘉宾,尤其要感谢我身边的阿来先生。我看了一下他近段时间的日程,发现他一直在各地奔波当中,每一天都是安排得满满的。今天下午他本来要去外省一个地方,为了本场分享会,他把机票时间往后挪了。向教授还主动为我这本书写了一篇文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梁平同时做文学刊物编辑:《红岩》3年,《星星》15年,在《青年作家》《草堂》至今已8年。“半个世纪过往的脸谱和结缘的文字不计其数,虽有心得,却不敢自以为是。这么多年身不由己,做事挤压作文的时间太多。年龄越大越是感觉到该写的欠账还是该一笔笔清算,《一蓑烟雨》是我最近两三年新写诗歌的一个结集,是近年来我的创作最为真实和整体的一个呈现。也是我非常看重的一本诗集。”梁平说,“其中有关于写作的根,关于诗歌中的我,关于叙事与抒情,关于历史与现实。”
一个人的写作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密切关系。在分享会上,梁平谈到自己的生命经验,“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跟在座的20多岁、30多岁、40多岁的青年人,文化营养有很大不同。我写诗的时间很长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写诗到现在,已经近半个世纪了。我曾经在江津琅山公社五里八队当知青,我住的地方是生产队农具保管室,土墙茅草屋,在保管室一个角落空余的地方,生产队找人砍两根树子剔了枝桠,树干洞穿土墙,钉上木条,一张篾席堆上一大堆稻草,再铺上一张草席,那就是我的床我的家了。我们的农活基本上都是开山放炮修梯田,一天下来躺在床上就不想动了,以至于我现在躺在松软的席梦思床上还时常想起那松软的稻草床。那个时候农村还没有电,一盏煤油灯还舍不得把灯芯调亮,煤油也很金贵。读书更是奢侈的事。我带到农村去的书只有几本,有三本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一本是《新华字典》,一本是郭沫若编选的《红旗歌谣》,一本是俄国作家、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严冬:通红的鼻子》,还有一册油印的江津名人吴芳吉的《婉容词》。《严冬:通红的鼻子》是一个长诗单行本,涅克拉索夫看见红颜色的高加索山,居然是严冬通红的鼻子,感觉如此美妙。再有吴芳吉半文半白的《婉容词》,直到现在还记得‘美洲在哪边,留一生颠涟,不如那守门的玉兔儿犬’,婉容活生生一尊望夫石。”
说到此处,梁平很动情,“之所以回顾这些,我是想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一样的样子。那段经历对于我影响很大。在我一开始的写作中,那个时代各种诗歌流派很多,但我没有去参与或者融入某个流派。我偏居一隅自己写自己的,写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的感悟。说起来这一点,我很感谢当时《四川日报》副刊部两位诗人王朝清和王尔碑老师,曾经从成都专程来江津看我,他们到了县委宣传部说明了来意,宣传部通知了公社,公社基本建设工地的高音喇叭通知我,我得到了很大的鼓励。两个老师跟我说,你就写你自己的,好好写。所以我一直保持自己这样的写作姿态。”
如何拓宽写作的视野和格局?
多读书,保持创新力
随着经验和阅历的增长,梁平对自己的诗歌写作路径已经有非常清晰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确认,对诗歌领域内的一些争论、课题,也有自己深入、冷静的思考,并形成较为系统的诗学观念。梁平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与生俱来有一种隔阂甚至是敌意。这个有根的写作,让我有了明确的写作路径,那就是努力消减这样的隔阂和敌意,与人、与自然、与社会的不平衡达成最大尺度的和解。”书名“一蓑烟雨”来自苏东坡《定风波》里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把这个概念当成新诗集的书名,梁平是这么理解的,“苏东坡一生是被流放、颠沛流离。他遇见风也遇见雨,但是他的那种豁达,他的乐观,他的平常心是怎么得来的?我觉得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有一个自我调适的心理过程。”
自2001年从重庆来到成都工作、生活,至今已23年。这两座城市也渗透进他的诗歌写作中。《一蓑烟雨》的编选,以嘉陵江和蜀道为发端和收尾,就有着关于重庆和成都二重奏的深刻意味。当有人问,对于这两个城市,哪一个是自己的精神原乡,梁平的回答很明确,“在我的精神围墙中间,这两个城市其实是一体的。其实它本来就是一家人。把这两个城市作为我的精神原乡都是可以成立的。”
有诗歌写作者现场向梁平请教,在拓宽写作的视野和格局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梁平回答说:“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有两件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一个是多阅读,尽可能地让自己有更多的知识、文化储备。另一个就是,在写作的每一个时刻,保持创造力。如果没有创造力,去跟风人家写什么,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是无效的写作。就我个人来说,新时期以后,整个理念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了自己的写作路径,该写什么,怎么写。我试图在写作中建设、健全自己的人格和重新体认家国与个体精神的宽广存在。”
(除署名外,其他图片由阿来书房刘建伟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