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学》2024年第1期 | 甫跃成:守护者(组诗)
《午饭后经过一处工地》
工地里出来的几个中年人
戴着黄色安全帽,穿着绿色反光背心,
蹲在马路边晒太阳。
有的抽烟,有的看手机,
有的闭着眼睛靠在树下,什么也没看。
他们不说话。
除了我,没有人经过。
枝头的残叶微微晃动。万籁俱寂。
这是一个冬日的正午。
我心怀感激却不知为何。他们的心情
是否也有相似之处?
我从他们身旁经过。烟草的味道。
隐隐的呼噜声。打在他们身上的阳光
与打在我身上的,应是同一种。
《滴水声》
天明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滴水声,
而那些滴水声,几乎让我失眠了一夜。
它们那么密集、响亮,近在咫尺,
仿佛水珠滴进了我的脑仁,
把我粗糙的记忆,也敲平了一块。
黑暗之中我找不着那些水,
但是白天,我多想跟它们碰上一面。
奇怪的是,我再也没有听到滴水声,
它们居然不辞而别,没留下任何
蛛丝马迹。早上起床,拉开窗帘,
我没找着落水的屋檐、接水的篷布;
雨后的世界浑身湿透,也帮助它们
抹去最后一点来过的证据。那些滴水声
是怎么来的?怎样的源泉、路径、落差
在那个特定的夜晚,造就了那些声响?
我收拾行李,离开宾馆,没入人群。
后来我去过无数城市,住过无数房间,
听到过无数的流淌、渗漏,总能见到
滴水的痕迹。但是那家宾馆
很多年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对屠宰铺的六只羊的正面观察》
前肢吊住。后肢吊住。
剥了皮,开了膛,
掏空下水,内脏,腹腔打理得
干干净净,露出两排
整齐的肋骨。
从这个特殊的角度,我不偏不倚,
与那只羊,正面相对,总觉得是
与一面镜子正面相对。仿佛我在
展示隐私,我在推销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自己。
它两眼圆睁,神情呆滞,
当然并不快乐,但也看不出
如何痛苦。大约我也是这副面容。
但它毕竟只是畜生,何况还是
死掉的畜生。它哪里会像
人类这样,在头颅正面
层层叠叠地,生长着无数盾牌。
舒一口气,我向右挪了一步。
那只羊的左肩上,便层层叠叠地
现出六张脸来。
《老科学家》
老科学家死了四十多年,他的妻子还活着。
我们去拜访老科学家,没有遇到。
我们问他的妻子,得知他正在四十五年前的
某间实验室里,做电缆补偿实验。
这会儿正在做,还没有结束。
也不知他做完实验后,会不会
走上四十五年的路程,回到我们中间来。
他就站在历史中的某个点上,忙他的事;
但因为太远,具体位置,连他妻子
也弄不明白。只留下我们,这帮串门的,
守在历史之外,他们夫妻的客厅里,说着
他的逸事,左等右等,等了足足一个下午。
《灭蚊记》
毫无疑问,这是意义非凡的一握。
他向空中捞了一把,
死死攥住,确保捏死了那只蚊子。
这些天来,那只蚊子
总在他耳边飞来飞去。在黑暗中。
在寂静里。在他解除了所有武装的当口。
它肯定是故意的。它从来不在
他埋头工作的时候来,也不在他
跟朋友喝酒聊天的时候来。
打蛇打七寸,它深知他的薄弱环节,
瞅准了,就痛下狠手,从他刚爬上床
就围住他,一直到他再次逃进人群之中。
这下好了。那只蚊子
终于栽在他的手心。胜负已定,
一切都将到此结束,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出于谨慎,他又反复攥了几把,
仿佛书里说的,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起身,开灯,不无激动地
摊开手掌,他只看见一片空无。
《守护者》
他问我能不能帮他守着三轮车,
好让他把两个包裹,送到台阶上面的那栋楼去。
当然没有问题。只是有些意外。
他只跟我见过几面,知道我住在这个小区,
但不知道具体位置。他对我的了解
仅限于一串号码,以及地址栏里的
一个网名。他凭什么,对我这么信任?
突然有了恶作剧的冲动。
如果我把三轮车开走,他怎么办?
如果我顺手藏起几个小巧的包裹,他死无对证,
又怎么办?他凭什么认为,我不会这么做?
而我真的没这么做。
我甚至心头一暖,渐渐地有了
一种守护正义的使命感。十分钟后,我望见他
出现在台阶顶部,满头是汗,憨笑着
朝我跑来,像老家的一个亲戚。
《生产记》
她说她错过了孩子出生的过程。
从昏迷中醒来,刚一睁眼,借助天花板上
一面硕大的镜子,她就目睹了
那血肉模糊的场面。她细细分辨着
那被切开的:一层,两层,三层。
鲜红的剪刀。鲜红的纱布。鲜红的
来回穿梭的针线。
那个腹腔,跟她先前见过的
并不一样。她对我说,她见过的
从来不像这么凌乱。它们总是
被打理得干干净净,挂在肉铺的铁钩上,
等着一个上好的价钱。
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躺在这里,
也不明白,那开膛的事件
又跟她有什么关联。但这想法只有一瞬。
她对我说,医生的右手
在拿刀的同时,还能麻利地
用手套套住左手。然后两手互换工作。
“横着剖,还是竖着剖?”
没等她回答,十个指头,活动着关节,
已在手套下跃跃欲试。
直到一阵婴儿的啼哭,把她从昏迷中
拽了回来,把她从别的世界
拽了回来,并将一个撕烂的空腔
塞进了她的腹部。这让她觉得
作为母亲,她错过了孩子出生的过程。
作为父亲,我错过的,还要更多一些。
我只看见她被推进手术室,再从手术室里
被推了出来。
《死亡是个渐渐的过程》
父亲告诉我,砖厂李全
有次从窑顶滚下来,钢筋扎破肚皮,
后来手术,肠子被割去两米。
隔壁老六,年前做彩超,
意外发现,腰子无缘无故地
少了一个。还有装了假腿的郑叔,
切了苦胆的二舅,甚至一些
我隐约记得名字的同辈。
父亲是在我
问起他断指的康复情况时
说起这些的。那么多人
都在变得残缺不全,并且越缺越多,
越缺越多。所不同的
只是父亲缺在明处,而他们
缺在暗处。
还算不错。截至目前,
我保留着全部零件。唯有腰椎
偶尔疼痛,大约是盖到父亲胸前的
那些黄土,盖到了这里的缘故。
《女孩和她的姐姐》
她把妈妈叫作姐姐,这是近一年的事。
这是在她想要一个妹妹,没有得到我们的回应
之后发生的。爸爸妈妈是两个人,
而她是一个。她多么需要一个小姐妹
跟她搭积木,过家家,用太空沙
捏各种神奇的形状。
多么简单。她仅仅是要
一个妹妹。实在没有,弟弟也行。
她不明白为什么,添一个妹妹
竟有那么多考量,必须精打细算,评估财力、
人手、假期、房屋面积。
她不明白那么多玩具、绘本,只要她喜欢,
爸爸妈妈都给她买了;而一个妹妹,他们居然
纠结了这么多年。作为对策,从爸爸这里,
她抢走了妈妈,让她充当她的姐姐。
“姐姐。”她从卧室跟到厨房。
“姐姐。”她从厨房跟到客厅。
有时我真想奔过去,
抱住这对孤单的小姐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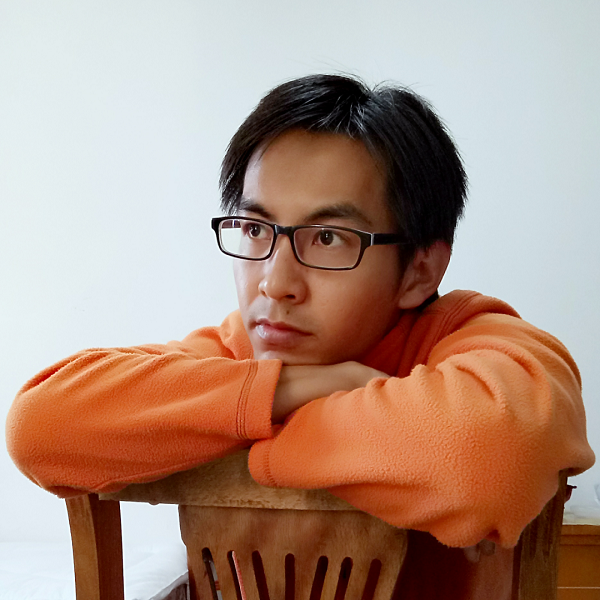
甫跃成:1985年生于云南施甸,现居四川绵阳。曾获诗探索·中国春泥诗歌奖、“四川十大青年诗人”称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