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冰开讲“从六朝古都到文学之都”—— 千年文脉在这里绵延

萧统雕像。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邢虹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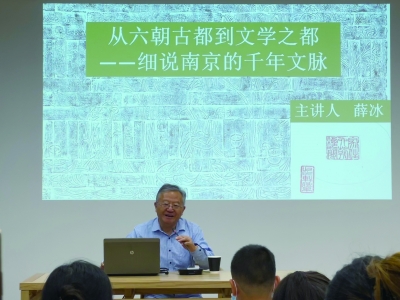
薛冰做客建邺区图书馆。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程锦欣 邢虹 摄
从“天下文枢”到世界“文学之都”,南京文脉绵延千年,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厚重历史和文化积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学馆、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专著《文心雕龙》、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等都是在南京诞生的。近日,作家、学者薛冰做客建邺区图书馆,开讲“从六朝古都到文学之都——细说南京的千年文脉”。“从六朝时期开始,南京就站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高标准上,文人墨客在这里创作出了大量文学作品,南京的文脉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得以成为中国唯一的世界‘文学之都’。”薛冰说。
首开先河
创立中国文学最早的规范
“中国文学最早的规范是什么?为什么说南京是为中国文学创立早期规范的城市?”薛冰说,这一切都要从六朝开始讲起。
这个时期的南京,文学创作繁荣,有陶渊明的田园诗、谢朓的山水诗,还出现了第一部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等。“创作过程中,理论也发展起来了。没有创作的基础,理论是空的。”薛冰说,研究中国的文学理论,一定会追溯到南朝齐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提出了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等。它以先秦以来文学创作为经验,继承和发扬了前人文学理论的丰富遗产,在文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到现在为止,研究《文心雕龙》仍然是一个专门的学问,研究中国的文学理论是一定会追溯到《文心雕龙》的。”
同样完成于南京,钟嵘的《诗品》是现存最早的诗论专著。薛冰表示,《诗品》与《文心雕龙》齐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双璧”。但与《文心雕龙》不同,《诗品》的宗旨在于评论诗人诗艺的优劣高下,因而集中探讨了汉魏以来五言诗歌的源流迁变。《诗品》将汉魏以来的重要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加以精要评论。“哪怕能进入下品也是非常难得的。”薛冰说,“在这么长的一个历史周期里,只有100多个人的作品被选入。《诗品》里不单是评论了诗人,也对他的代表作品、诗歌风格、诗歌流派的传承,包括其家族进行了评价。”钟嵘将评论对象限定为五言诗,“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这不仅如实地反映出当时五言诗体已取代四言诗体的发展现状,更加彰显出作者敏锐独到的眼光和突破成规的勇气。在五言诗的经典化历程中,钟嵘的《诗品》毫无疑问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这一时期的南京还诞生了现存最早的文学作品总集《昭明文选》,由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如果不是《昭明文选》把很多作品保存下来,它们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薛冰说,与此同时,《昭明文选》起到了界定文学范畴的作用。“《昭明文选》经书,不选史书。哪些作品可以归入文学?文学作品如何来界定?这部文选确立了标准。”
有意思的是,《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文心雕龙》里受到肯定的作者,他的作品就很有可能进入《昭明文选》。这个比例有多高?达到80%。”薛冰说,这是因为萧统十分认同刘勰的理论,而且经过政治家、文学家沈约推荐,刘勰入朝为官,被萧统看中,成了他的“秘书”,也参加了《昭明文选》的编选工作。
“四学并建”
文学真正成为独立学科
文学教育方面,六朝时期同样具有开创性。
很多大学里都有文学院,你知道文学院是怎么来的吗?《宋书·雷次宗传》中记载,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在北郊鸡笼山(今之北极阁)开四馆教学。以雷次宗主儒学,何尚之主玄学,何承天主史学,谢元(谢灵运从祖弟)主文学,此为宋之国学。南朝实行“四学并建”,设立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和文学馆等四馆,各就其专业招收学生进行教学和研究,由此形成了高等教育分科教授制度,文学与儒学、史学、哲学分离。以前,文史哲都是不分家的,四馆的设立,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史哲的不同特性。“这是最早的文学教育,担负起了文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使命。如今大学里的文学院是从哪里开始的?答案就在这里。文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就是在六朝时期。”薛冰说。
如今,鸡笼山下原文学馆所在地,南京“世界文学客厅”已经建成开放。历史在这里有了回音,传统在这里有了延续。
现代蓬勃发展的文学社团,也在六朝时期就出现了。“竟陵八友”就是其中大名鼎鼎的一个社团,为文学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朝齐永明年间,有一大群文士集合于竟陵王萧子良左右,其中最出名的是8个人,因此被称为“竟陵八友”。《梁书·武帝本纪》记载:“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焉,号曰‘八友’。”
“今天的北极阁附近,文学馆在这里,竟陵王的府邸也在这里,当时是文化人集中活动的一个场所。”薛冰说,文学社团的出现,说明社会上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的人多了,才会有一部分人聚集起来。梁武帝萧衍当时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如今莫愁湖公园中有一块碑,上面刻着《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这首诗就是萧衍的作品,莫愁湖就是因这首诗而得名的。
“竟陵八友”为声律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写诗要押韵,押韵规范是从哪里来的?就是‘竟陵八友’研究出来的。”薛冰说,唐诗的兴盛可以说在六朝时期就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诗歌体裁从五言到了七言,诗歌的形式、诗歌的押韵和声律,都是在那个时期有了文学基础。发展到了唐朝,加上社会安定繁荣,所以诗歌创作一下就兴盛起来。”
文脉绵延
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寻根”
唐朝重要的诗人几乎都到过南京,成为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现象,“金陵怀古”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母题。诗人们留下了无数写南京的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南京的文脉千年绵延不断,在北方中原遭遇危机时,这里就成为华夏文明的救赎之地。“文人墨客追寻文化的文脉和根源的时候,必然会到南京来。他们来了以后,进行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又让南京的文脉进一步延续发展。”薛冰以李白为例,“他前后五次来到南京,每次来都会召集一帮朋友一起聚会、写诗,一起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留下那么多的作品,形成了唐朝时期南京的文学氛围。”
唐代之后,也是如此。王安石、苏东坡、秦观、周邦彦……他们都在南京生活,在南京留下了重要作品。“王安石虽然是江西人,但是他非常喜欢南京,所以最后在南京定居,再未离开。”提及王安石的南京情结时,薛冰联想到了另一位大家——苏东坡。王安石当宰相的时候,苏东坡与他政见不合,但到了晚年,两个人都离开政坛了,苏东坡被流放回归时经过南京,前来拜访王安石,他们不再纠缠昔日的恩怨,在文学上的交流也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苏东坡对王安石说,如果早十年能跟你交往的话,我的文学成就一定会更高。王安石便建议苏东坡也在南京定居,一起做邻居。”苏东坡听后,写下了著名的《次荆公韵四绝》:“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清代名士李渔迁居南京,所著《闲情偶寄》可以说是当时文化人的“生活百科全书”。老门东芥子园的复建,多亏有他。“他在书里大量记载园中的亭台楼阁,所以今天我们才能照着样子把它修复出来,再与大家见面。”薛冰说。作为中国绘画的入门读物,《芥子园画谱》就诞生在芥子园,此书最初是由李渔之婿沈心友邀请王概、王蓍、王臬兄弟三人共同编集,到今天仍然在中国画的入门和深造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代文人袁枚来到南京后,写下了诗歌理论作品《随园诗话》,书里有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特点——女诗人的诗特别多,占了近一半的篇幅。“在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女诗人的作品,但是袁枚鼓励女子作诗,积极推荐她们的作品,这是非常难得的。”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朱自清为南京留下两个重要的文化地标,《背影》“带火”了浦口火车站,引得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他将自己的感情与思绪,融合在风景描写技巧中。鲁迅因在南京读书起步,得到了公派日本留学的机会,从而走向世界……
“南京文脉的发展,从来不是关起门来的,不是封闭的,而是打开的。开放包容,把全国最优秀的文学人才吸引到南京来,在这里留下重要的文学成果,从六朝开始一直到当代,都是如此。”薛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