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于旸:命运本身也包含对命运的反抗
编者按:“文学苏军新力量”是江苏省作家协会优化文学梯队建设、培养推介文学新人的重要项目。2023年,江苏省作家协会联合中国作家网,隆重推出“文学苏军新力量”第一批10名青年作家,通过文学访谈、视频推介、专家点评等形式,让广大读者了解他们的创作历程,倾听他们的文学心声,共同瞩目当下青年写作的来路与远景。

作家简介:周于旸,1996年生,江苏苏州人,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小说界》《青年文学》《长江文艺》等刊,有作品被《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已出版小说集《马孔多在下雨》《招摇过海》。《马孔多在下雨》曾入围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
不停,不停。周于旸的小说里有关于节奏的艺术,事物在动,有根基牢固却努力挣脱的自我,也有离散了的漂浮体,仿佛断线的风筝,向遥远的某处逃匿。《鹦鹉螺纹》中那个荒诞的、近乎伪科学的永动机不停,里面装载着一对父子难以名状的情感关联,十数年如一日;《暗楼连夜阁》中祖父的手表不停,一旦停下就意味着时间退散、命运来临,所有的过往将以沉默告终;《宇宙中心原住民》中何仁觉的检测工作不停,面对永远闪烁的电子波浪纹,稍一停歇,警报声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响起……不停的自然也是周于旸的创作,从青春文学起步,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他的文字里充满怀疑也充满创造。记忆不停,想象不停,现实不停。于是,每时每刻,都是在告别陈旧,开始一段新的故事。
突破自我的前提是先为难自己
陈泽宇:于旸兄好,很抱歉这份采访提纲比预想中来得要晚些。总有层出不穷的事情,按下葫芦起了瓢。我一度认为这种忙碌的、快节奏的生活和文学是对立的,慢慢发现也不完全如此。那就从这里开始聊吧,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周于旸:谢谢泽宇兄。两年前我辞了职,回家全职写作,生活较为懒散,每日睡到中午,下午去书店写小说,晚上和朋友玩游戏,临睡前读一点书,这就是日常的生活,大概花了一年左右才适应。我感觉人天生带着劳动的基因,没了工作以后就要与这种基因对抗,脱离了社会范式,经常会感到虚无,写作勤奋的时候还好一些,大多数时候比较懒惰。
陈泽宇:谢谢分享。阅读和准备采访提纲时,我特意暂未检索关于你生活的相关信息,怕形成某种刻板印象。根据我的阅读体验,比较你近年来和稍早时期的小说,这些作品写作风格保持着相对一致,但最近的写作在技艺上愈发成熟。这是一个青年新人成为成熟作家的标志,也意味着写作者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上升期。你觉得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写作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初步找到某种阶段性的方向感?
周于旸:前一篇小说的遗憾,在这一篇小说里解决了,如此持续性的一阶段可能就是上升期。这种体验在早几年比较明显,翻出那时候写的文章,可以很清楚地排个优劣次序出来。但最近一段时间写的小说,它们应该拥有了等同的质量。写作于我而言还是痛苦居多,因为想写好,所以尤其痛苦。如果写作中感到顺畅,反而会怀疑文章缺乏雕琢。写小说需要给自己设置难题,再想办法解决难题,突破自我的前提是要先为难自己,这样能够减少一些自我重复的东西。

《马孔多在下雨》,周于旸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
陈泽宇:《马孔多在下雨》,你去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着实很“火”,还冲进了年度“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决选名单。从书名不难发现,马尔克斯是一位对你意义重大的作家。于是问题来了,这恐怕也是你已经被问烦了的问题,《百年孤独》的哪些片段让你印象深刻?当然,如果你愿意分享,我们也很乐于倾听你第一次阅读这部大书时的细节感受。
周于旸:毋庸置疑是开头和结尾,中间当然也有许多精彩的片段,但开头和结尾让它成为了一部难以超越的经典之作。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叙述策略,第一次阅读时,因为叙述过于紧凑,读着读着就混乱了,它一度程度上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不再拘泥于理清故事脉络,更着重于享受作者的语言结构和叙述技巧。
陈泽宇:还想多问一句,你觉得,与曾经也深受马尔克斯影响的那一代作家相比(比如莫言等人),你对马尔克斯的接受有什么不同?我发现,随着文学时尚的偏移,代际写作的阅读接受也存在一定变化。
周于旸:《百年孤独》有很多科幻的元素,我想这是为很多人所忽视的。第一代族长实际上是个科学家,在那个闭塞的村庄里,外来的吉普赛人带来任何一件外头的东西,都会被当成了不起的发明。何塞·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用放大镜把自己点着了,就想着能用它作为武器发动阳光战,还做了详细的手册寄给当局。这很像科幻小说的构思,放大镜在这里充当着和机器人、外星人一样的道具作用。
想象力不是固有天赋,有其路径可寻
陈泽宇:《马孔多在下雨》里收录的同名作品中,还清晰可见你连结的其他文学血脉,主人公马登这个名字,就是从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里来的。以及小说中关于“迷宫”的装置性挪用,也体现了强烈的博尔赫斯气质。诗性和哲思的缠绕,借由人物个性或情绪表达出来,其中最明显的是孤独感。“孤独感本身就是一种归属感”,看到马登说出这句时,我感到为之一振。但还是想听你细谈一二,孤独感已经贯穿在你若干篇作品里,为什么你对这种情绪情有独钟?你是在什么层面上理解“孤独”的?
周于旸:写作本身就意味着孤独,大部分工作都有通力合作的部分,但艺术创作基本属于个人。最早有这种体会就是在写作的时候。我认为孤独是一种途径,它可以通向独立、自由或专注,人在向内探索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与之相遇,它不单单是一种负面的情绪,也可能是一种正向的状态,我认为好的小说或多或少都带有孤独的气质。

《招摇过海》,周于旸 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陈泽宇:你的小说中,除了孤独感、童年记忆、故乡情愫几种鲜明的特征外,科幻外壳也很常见。如果说《退化论》还是相对保守的启蒙主义框架内的类科幻文学,那《子宫移民》《宇宙中心原住民》《鹦鹉螺纹》等几篇都是借用科幻的外壳来探索更深层次的人性和无意识问题了。你喜欢读科幻小说吗?或者说,你是否认为这种类型化的文体特征为叙事动力提供了更有效的建构方式?
周于旸:严肃文学更在意把事物写深刻,而科幻小说追求把事物写开阔。两者的出发地不同,严肃文学像一棵树,从土地出发,一直伸到天空。科幻小说像一架飞船,它飞得很高,看到的风景更广阔,但和大地的联系就没有那么多。严肃文学关注个体的命运,从中折射出社会和时代的印记,而科幻小说通常会牵扯到整个人类的命运。科幻小说给我的启发是它的框架和思维模式,例如像阿瑟·克拉克的《神的九十亿个名字》这样的小说,本质上表达的是科技进步加速了人类的灭亡,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命题,它用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讲清楚了,它进入文本的方式和严肃文学不同。我觉得想象力并不是一个固有的天赋,是有路径可寻的,这是科幻文学的思维模式,我认为它同样匹配严肃文学,好的小说需要想象力,哪怕只是一个修辞、一个意象。
陈泽宇:还想从《招摇过海》出发与你谈谈“命运”。在漫长的汉语传统中,“海”往往是作为他者的存在,所以也容易安置诸种镜像关系。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人的理想状况,早在孔子时期就有了“乘桴浮于海”的表述。你在小说中塑造的舅舅曾传裕有着“招摇”的一面,也有着按捺不住的理想心结,但最终又归于一种荒诞式的宿命。你似乎对写“命运”怀有复杂的情绪,它在舅舅的漂流瓶里,也在《暗夜连声阁》祖父手表的秒针上,既能看到你对“命运”的抵御,也能看到一种潜在的自信。想听你聊聊对“命运”的看法,绕开文本的创作谈,从生活实感讲一讲这个话题。
周于旸:命运这个概念很像人类创造的一种虚构,往小了说,人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改变命运,往大了说,命运本身也可以包含对命运的反抗。这是个吊诡的概念,取决于用当局者的视角还是上帝视角来看待。我只能通过小说来理解这个概念,在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是作者的布局,一个人的一生就在纸上,因此宿命感比较明显。

近年来,青年作家周于旸的小说刊发于各类文学期刊。
“在我的写作中,叙述节奏是重要的”
陈泽宇:谈一点个人意见,不知道你是否认同。似乎你在结构短篇时有一种惯性,利用一些功能性的人物来推动文本情节的发展,比如《雪泥鸿爪》中江锋后来的妻子杨韵,再如《暗楼连夜阁》里祖父曾经的女学生,还有《招摇过海》里的外公。这些人物基本上都在按照作者的叙事要求推动文本,他们“辅助性”强,主体性偏弱,导致这类人物与主角之间的势能有些不均衡。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小说中一些对“谜”的“释疑”游离于人物之口,回到了叙述人的讲述里,比如《宇宙中心原住民》后段。这种叙述层次的混淆让小说的腔调在“圆融”的一端上显得没有那么尽美了。当然,这种觉察也可能仅存在于我的幻觉里。
周于旸:短篇小说里很难把每件事都做好,写好一个人物,讲好一个故事,渲染一种风格,把控节奏和腔调,有时只能做好其中的一到两件。在我的写作中,叙述节奏是重要的,我很难为故事或人物去牺牲这一点,通常会选择一种折中的方式来平衡这些问题。
陈泽宇:访谈进行到这里,我一般都会问一个我的保留问题,也请你来作同题问答:据说有“上午型”、“下午型”、“夜晚型”的写作者,随着时刻的切换,写作的风格也有些不同。你有类似的体会吗?你一般在什么时间,选择什么样的环境写作?
周于旸:我对写作时间倒是没有太严苛的要求,但是比较挑地点,我喜欢在视野比较开阔的地方写作,书店和咖啡馆之类。不过因为经常要赶稿子,也没得挑地方,书房和卧室也是主要的创作地点。

2022年,周于旸凭《马孔多在下雨》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2022决名单。
陈泽宇:如果几个月前谈论下面这个问题,还会更有时效性一点,当然现在问也不晚。你怎么看待ChatGPT等人工智能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它能构成一种对现有文学场的挑战吗?相同的问题在几个月前我也和其他青年作家聊过,现在感觉ChatGPT有些落潮了。但我又犹疑这只是话题层面的落潮,毕竟,真正的历史都发生在不经意之间。
周于旸:ChatGPT刚出来的时候,我特地去了解了一下它的能力,它能够写出一些高分作文,但总体来说停留在工具写作的层面,还够不到艺术创作的层次。它对一些行业有冲击,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暂时比较小,让人担忧的是它升级进步的速度。
陈泽宇:最后,请向读者朋友推荐几本书吧,不必是最新出版物,就推荐你最近读到的、值得推荐的好书。
周于旸:最近对历史社科类的书比较感兴趣,在读理想国译丛的《娜塔莎之舞》,很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读完,它的叙述特别流畅,很有小说的感觉。前段时间在读《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也是一本厚书,讲一个人的海上冒险史,是一本十分好读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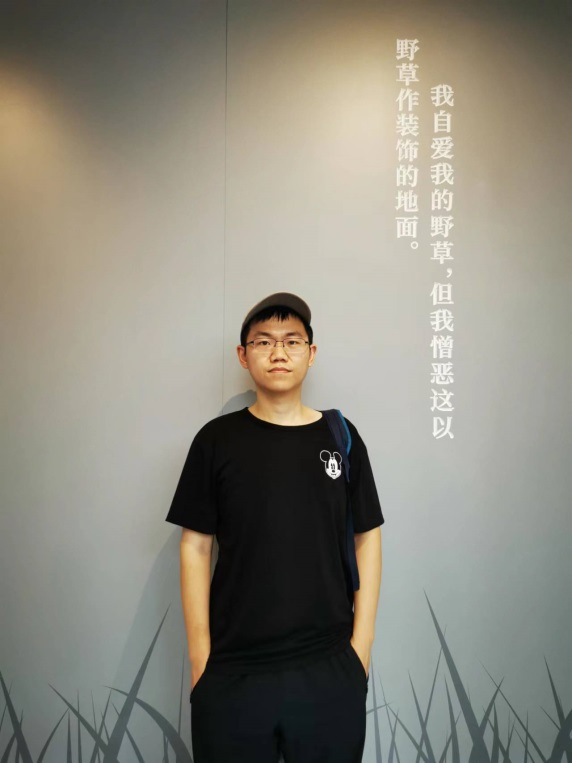
陈泽宇,中国作家网文史频道编辑。1995年生于济南。主持“茅奖作家研究”“文学批评经眼录”“理论评论新著列锦”“十号会议室”“行进的风景”等栏目。有作品散见于《文艺争鸣》《青年文学》《特区文学》《诗歌月刊》《文艺报》《芳草》《诗潮》等。
附:周于旸创作简表(2015-2023)
发表情况
2015年
《曾经春秋不见夏》发表于2015年《萌芽》第6期。
2017年
《我亦未曾饶过岁月》发表于2017年《萌芽》第5期。
2019年
《无欲之城》发表于2019年《萌芽》第2期。
《马孔多在下雨》发表于2019年《特区文学》第1期。
《裙底辉煌》发表于2019年《香港文学》第10期。
2020年
《鹦鹉螺纹》发表于2020年《长江文艺》第5期。
《北冥有鱼》发表于2020年《特区文学》第4期。
2021年
《云顶司机》发表于2021年《朔方》第2期,并被《长江文艺·好小说》第4期与《小说月报》第4期转载。
《比天之愿》发表于2021年《雨花》第8期。
2022年
《不可含怒到日落》发表于2022《青年文学》第1期。
《大象无形》发表于2022年《雨花》第3期。
《无声年代》发表于2022年《湖南文学》第5期。
《暗楼连夜阁》发表于2022年《长江文艺》第11期。
2023年
《雪泥鸿爪》发表于2023年《十月》第1期。
《退化论》发表于2023年《小说界》第2期。
《招摇过海》发表于2023年《人民文学》第6期。
《穿过一片玉米地》《岛的周围全是水》发表于2023年《西湖》第6期。
《宇宙中心原住民》发表于《安徽文学》2023年第7期。
出版情况
1、《马孔多在下雨》,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2月
2、《招摇过海》,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