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文学》2023年第8期|周闻道:一条上岸的鱼
不得不引起我的注意,这张不显眼的照片。
开始还没有注意到它的特别,只当是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909基地创业史厅的普通一角。一种常见的“革命传统教育”式的老旧厂房,里面可能还陈列了一些古董式的老旧设备。照片很普通,有点儿泛黄,在该院的各类重要介绍中都可以看见:一排长长的厂房,不伟岸也不耸立,只有两层楼,静静地伫立在两片浅山间。想来原是粉白色的外墙,只是时间久了,墙面已经浸染了岁月的痕迹,呈现出浅浅的灰暗色。这倒好,一下拉近了与两侧青山的距离。
就在这拉近的一瞬,我有了新发现:这哪里是一排厂房,分明是一条鱼,畅游在一片广袤起伏的绿海之间,略显朦胧的色调,与其说淡化了海与鱼的界线,不如说更融会了它们的和谐,渲染了它们的纯朴真实。当然,真正让我确认自己发现的,还是在我了解了照片上这排房子的真实身份之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196模式堆)。从目的指向上,就会联想到船,一条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船,或者说,把它理解为一条鱼,一条上岸的鱼。
话似乎有点儿玄,其实一点儿也不玄。哪个人不知道,现代科技的许多成果,其创造机理都源于仿生学,比如仿照鸟就有了飞机,仿照蛇就有了火车,仿照鱼就有了船。要说把在江面海面行驶的船比喻为鱼还有点儿牵强,那么把潜艇形容为鱼,就不得不说实至名归了。
问题也就来了——我们小时候就天天唱“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这里就仿佛是欧洲的天鹅一下出现在澳洲,明明是水生动物的鱼,为什么游到了岸上,或者说它游上岸来做什么呢?我心里非常明白,眼前这个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也开宗明义是“陆上模式堆”,就在离我老家,或现在我工作生活的城市不远的峨眉山麓的一片浅丘里。绿色的海和鱼,都是我的文学想象。
眼前这一张照片,画面灰暗模糊,很像我们在909基地看到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照片的光线和成色。画面上一名中国海军战士,神态坚毅,手握炮舵,正在装填炮弹。可是,炮弹还没装上,没有发射,更没有消灭敌人,战舰却中弹沉没了,这位勇敢的海军战士也随舰沉入海底。我不知道这位英勇的海军战士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所在的战舰是大清北洋水师的哪艘战舰,但可以确定的是,再勇敢的水师,也挽救不了一个软弱无能的王朝沉没的命运。
未来世界的博弈,会在海上。
既然未来的博弈在于海,就得征服海,就得有驭海的蛟龙。
当世界的逻辑演绎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一个黄钟大吕般的声音: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是毛泽东说的。他在求助苏联帮助造核潜艇碰壁后,发出了这样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当时,还与中国处于“蜜月期”的苏联说:“核潜艇非常复杂,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成。你们就不要搞了,我们来保护你们。”
无语。惊讶。苏联的话外之音!
将自己国家的安全保障维系于他人?毛泽东明白了,也更加笃定。当豪情与诗性结合,就有了“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才是他老人家需要的国家境界。对此,当代核动力人自有独特的理解。他们认为,鹰击长空,指的是我们的歼-15、歼-20、歼-31上天;鱼翔浅底,指的是我们的核潜艇入海;万类霜天竞自由,则指的是我们饱经磨难的国家和民族,在世界邪恶势力的重重围攻、打压下傲然崛起、雄立于世,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的幸福安康。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这首写于1963年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已然满满贯穿着反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捍卫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意志。大梦谁先觉,自有明白人。彭士禄当然理解毛泽东。
就这样,一个伟大的梦想赋予了鱼——为仿生的鱼赋魂,护其成龙,捍卫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主权和民族尊严。
在909基地向海楼茶吧和在建的红色教育基地桥头,我都曾认真观察核潜艇的模型。当思维脱离僵硬的金属,我脑海里总是会幻化出一条鲜活的鱼。那鱼在大江大河或大海里遨游,那么自信,那么自由,那么笃定。此时我就会想,这究竟是啥鱼呢,如此自在而从容?我调动所有的记忆搜索,从家乡岷江滩头冲浪而上的“串杆子”,到附近黑龙滩水库里的花鲢、白鲢,从儿时用竹竿在门前思蒙河里钓起来的“乌棒”,到澳洲黄金海岸搁浅的巨鲸,似乎都像,又都不像。像是它的形,尖尖的头,长长的身,灵巧的翅与尾,畅游的姿势;不同的是魂。
对,鱼与核潜艇的差别在于魂。我发现,导致它们差别的原因,是它们是否经历过劫难,是否上过岸。上岸是对鱼的一种赋魂仪式。只有赋魂得道,才能跃门为龙。只有有自护能力,才能有效保护自己;只有有效保护自己,才能有效消灭敌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国家要求核潜艇项目立即上马。
要让大江大海里的鱼上岸赋魂,非一蹴而就,首先得保证赋魂期的安全。既然最近、最直接、最主要的威胁来自北面,那么,就以北面边境为起点,在国家的版图上划出一线、二线、三线。核潜艇研发的选址,或上岸的鱼赋魂的圣地,显然在三线地区。经过专家们重重调研发现,川黔地区真是三线中的三线,核潜艇研发重地舍此何求?“山不
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双福界牌三线9区,落户代号09的196模式堆,是天地人合。
此处峨眉山、青衣江、瓦屋山造就了“两山对视,一水中流”的格局。两山对视,为远游的鱼上岸修炼赋魂,创造一方物华天宝之地;一水中流,核心是流水。水是鱼的家和魂,上岸修炼的鱼,经过赋魂、跃门成龙后,又可以顺着来路,重返大江大海。于是,国家与“两弹”一起规划的核潜艇工程,在一线的“两弹”试验成功后,立即被推到“一线”。八千多人的建设大军,从北京和全国各地赶来,开启中国核动力工业的破冰之旅,或者说,为一条梦中的鱼上岸修炼赋魂而开天辟地。
初到时的艰辛都不说了,20世纪80年代,喝过滤的泥浆水、住“干打垒”、穿劳动布,几乎是当时“三线”建设企业普遍的状况,没有哪个好到哪里去。从高干到国家级专家,都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也没有听说有人被这样的艰苦吓退吓倒。虽然这也是“三线”精神的重要组成,但并不是给上岸的鱼赋魂的主要内容。
让“鱼”修炼成核潜艇的关键是“堆”——核反应堆芯。
又回到鱼,刚才909基地那张不起眼的照片的主体,那个至今已作为文物保存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
随着我国与苏联关系的破裂,相关专家撤离,中国的核潜艇核动力研究,几乎就是一张白纸。何况核潜艇不比原子弹,靠核裂变可以一爆了之,让巨大的能量瞬间释放,形成强大的摧毁之力。核潜艇需要通过一个反应堆,在狭小的空间内,把这种核裂变控制起来,让它变之随人,慢慢释放,造福人民。这就像把猛虎驯化成柔猫,把海啸归顺为溪流,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个世界前沿性科技难题,许多研究了几十年的专家,都面临不少未知。
但怎奈,“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彭士禄还是被“赶鸭子上架”了。
彭士禄虽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并不是学核物理的,后来为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决然改行,去搞“八字没有一撇”的核潜艇,只到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进修了两年。这就像要求一个二年级学生,去承担世界级尖端科技难题。他1958年底刚从苏联留学回国,就被安排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从事国家刚启动的核潜艇核动力装置预研。从此,他就与中国核动力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也曾多次说:“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核潜艇,二是核电站。”而这两件事的核心、关键或灵魂,都是核动力。
此时,又恰逢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先搞“两弹”,核潜艇项目暂时下马,只保留了一个五十多人的核动力研究室,彭士禄作为该室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凭借着强烈的国家、民族使命感,彭士禄与他的队员们,在最艰难的时期坚持下来,鲤鱼逆水,蓄势以待。这正验证了一句名言:机遇属于有准备的人。
终于,随着“两弹”的成功,中央决定将搁置的核潜艇项目重启。彭士禄团队怎能不闻鸡起舞,激动万分。
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
这是彭士禄回忆起当时心情时说的话,看似随性而语,其实,那背后不知隐藏着多少期待与付出。比如告别北京的妻子儿女,只身入川,面对原始自然的“巴山蜀水凄凉地”。于是,按照“先治坡,后治窝”的原则,用青石、黄泥、稻草、米汤等混合砌成的“干打垒”,构成了909基地的建筑风格,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不仅院党委工作部、组织部、宣传部、技术部等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就连院领导和院士们,也挤在这种“干打垒”房子里。宝贵的钢筋、水泥、木材,要用在核潜艇陆上反应堆等关键设施的建造上。可就在这么一层低矮的“干打垒”里,却建立了15个国家实验室,创造了中国的一批批镇国之“鱼”。它们从大海的深处上岸,来到双福界牌这片小小的山头,修炼成正果,然后又下海、上岸,奔赴自己的使命。
要说克服生活上的艰难还简单,攻克那些数不清的技术难题就不简单了。基地指挥部设在一个小山包上,山包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也没有问,也许本来就没有名字。在基地,这样的山包很多,就像过去乡村的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能被称作张王氏、孙钱氏之类。这个山包嫁与了基地,嫁与了中国的核潜艇核动力事业,设为指挥部,就叫指挥部了。在基地,一说起指挥部,没有人不知道在哪里。而今,虽然基地院总部迁到了成都,这里仍是根和魂。
我关心的是,在基地众多的山包之中,当时为什么就选中这个山包,作为基地的最高指挥中心。基地人员的一种解释是,彭士禄在忙碌之后喜欢散步、休闲、健身、放松,还要思考没完没了的核堆问题。而这里有一棵香樟树,须两人合围,据说已有400余年历史。树干高大挺拔,伟岸雄傲,树冠绿荫如盖,枝叶婆娑,树下正适合进行这一切。相较而言,我更赞同另一种说法:这里相对较高,且面朝南方,前面十多公里就是峨眉山。在晴好之日,站在山头往前一望,就可以清晰望见峨眉山和金顶那里的日出和云海。
再往前,视线就被峨眉山挡住了,一切只能靠想象去完成。
比如此刻,我站在山头上,站在指挥部或彭士禄故居前,抬头向南眺望。近处,我看见郁郁葱葱的基地,像一片海,海风吹过,碧波荡漾,霞光泛绿;一座座的小山包,沉浮于绿海间,似一艘艘整装待发的战舰,舰头直指南方;或者可以理解为一群游上岸的鱼,正准备产卵,孕育新一代的生命。远处,我不仅看见了隐约可见的峨眉山金顶,还想到越过峨眉山金顶,再往前就是中国的南海。
一位哲学家说过,热爱是最大动力,笃定会创造奇迹。
在彭士禄团队的努力下,从1967年开始建造中国第一台1∶1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到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建成投运,不是一万年,也不是一百年,仅仅三年多。
1985年,彭士禄也因此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当鲜红的获奖证书呈现在面前时,彭士禄的眼眶闪着泪光。这是胜利的眼泪!透过彭士禄眼里的泪光,回望如烟来路,我们还怎能尘封得住自己的泪?
中国核潜艇工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三十多年啊,彭士禄都是直接参与者、探索者、设计者、指挥者。怎能忘记,在潜艇核动力装置研究初期,为了建立反应堆物理计算公式,彭士禄用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夜以继日计算出十几万个数据,并创建出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怎能忘记,彭士禄在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期间,带领团队攻克解决的那些核潜艇研制、生产、试航中的重大技术难题。大家很欣赏他处事果敢的性格,他也因此得了一个“彭胆大”的俗号。科学不是靠大胆,但这个称谓却不是贬义,是科学、果敢、担当的代名词。大家还记得,在遇到一些风险较大的技术难题时,彭士禄经过科学论证,一旦拿定主意,就会果敢地说:“好,就这样干,出了问题我负责,就是要枪毙也枪毙我。”
怎能忘记,怎能忘记……
是的,这鲜红的获奖证书,凝聚了太多的“怎能忘记”。这些,都是为了给这条上岸的鱼赋魂,让鱼升华为龙,重返江海。1970年,中国第一台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第一次启动试验,主机就达到满功率指标,紧接着,是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
终于修成了正果——上岸的鱼。
当赋魂的鱼升华为龙,重返江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无声之威。我不知道这条重返江海的鱼,是要先去黄海探望那些沉没的北洋战舰,为那位没有填完炮弹的勇士敬一个礼,还是去南海逛逛?可以确定的是,重返大海的鱼,你的龙威,让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有了底气。
有了底气,更该清醒。威武的恐龙都曾灭绝,何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自从世界进入核时代以来,核武器就成了一种镇国大器。由于核武器的威慑太大,没有哪个国家承受得起,二战时期不可一世的日本天皇,也不得不在美国的“胖子”和“小男孩”面前乖乖举起双手。由此,世界上产生了“核武威胁有限论”,不是指核武器的威力小,恰恰相反,是说其大,大到没有国家能够承受一颗。也就是说,你拥有一万颗原子弹,与我拥有十颗的意义是相同的——因为我的十颗已足够你承受。世界因此在高危中平衡。可是,又衍生出第二个问题,打破了这种平衡:既然一颗原子弹足以置一国于死地,要是遇到流氓、无赖之类,先发起攻击怎么办?
由此产生第三个问题:即便拥核,也必须保有二次打击能力。
感谢你,重返大海的鱼——中华之龙。
你不仅无声自威,更让从来不曾想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我们,拥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威慑。从此,我们再也不怕流氓、疯子与无赖的肆意,可以安心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
也许是受彭士禄的影响,重返大海的鱼很善解人意。在获得“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境界,为国家夯实镇山之石后,它想到了第二次上岸。这次上岸的目的已与前次迥然不同,不是为了修炼和赋魂,而是反哺——用自己第一次上岸获得的
赋魂赋能,造福人类。当然,也在造福人类中不断完善自己,提升自己。
在909基地,人们被反复提醒一定要记住一个时间:1970年7月28日。这一天,上海市委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发展核电的重要批示,文件内容看似是针对华东地区缺煤缺电而言的,实际上对整个中国核电事业都是指引。从此,核能的魅力,像一盏阿拉丁神灯,让鱼获得更加强大的能力,迎接主人的召唤。
先只是简单的原理移植,即将水下核潜艇上的堆芯,移植到岸上来,将推动核潜艇的动力,用来推动汽轮发电机,为人类提供强大的清洁能源。由于先有了核潜艇的196模式堆,我们顺利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然后想到嫁接,有
了引进法国技术嫁接的大亚湾核电站。从此,我们站在了世界核电工业的前沿,让核电发展加速、提质、增效。无论哪种形式,彭士禄都是奠基者、引领者、指挥者、参与者;同时,他还不断引入同盟军,由几十到几百几千人,是“江山代有才人出”,更是共领风骚永向前。
就这样,从上岸、修炼、赋魂,到返海、再上岸,鱼已不再是原来的鱼,而成龙——中华之龙。不知是命名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就有这种天意,当黄河中希望跳过龙门修炼成龙的鲤鱼,与从大海里上岸希望修炼成龙的鱼照面,这个龙的民族,才真正把龙写成。
事实是如此具体:一个大写的龙,让这个多难的民族拥有了过去从未有过的自信,敢于喊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豪言壮语。
专家的判断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能源是工业生产和许多工业产品运行的粮食,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命脉;而陆地上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标志的化石能源,据估计,按目前的开采使用状况,最多还可支撑二百年;水能、风能和以钚、铀等为原料的裂变核能等,不仅储量有限,碳排放也较高,特别是裂变核能,还有潜在的环境风险。因此,根据现有科技的认知限度,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海洋,认为海水里数十万亿吨计的氘、氚储量,及以此为原料产生的聚变核能,才是人类的终极能源和“太阳”。
这也许还需要几十年。
但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无疑,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还离不开裂变核能;而我们再次上岸的鱼,已游到了世界前列,虽然仍是前路漫漫,但是回望已一览众山小。
每一次突破都是高峰,每一个拗口的概念都是奇迹。当难题攻克、奇迹诞生之后,便是我们再次下海或上岸的鱼,不,是我们的中华之龙,“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时候。
我相信,从生命和哲学的意义上讲,眼前这个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就是一条上岸的鱼。上岸是一种宿命,为了修炼赋魂,得道于大地,就像跃过龙门的黄河鲤鱼,一旦得道,它就会蜕变为龙,然后义无反顾,重返大江大海,践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参观完彭士禄、赵仁恺故居,我站在909基地指挥部山头,沿着香樟树绕了一圈,静静感受,然后抬头远眺,看着眼前的一片绿海,我感觉,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条鱼,从上岸再入大海的鱼,到远洋深处去寻找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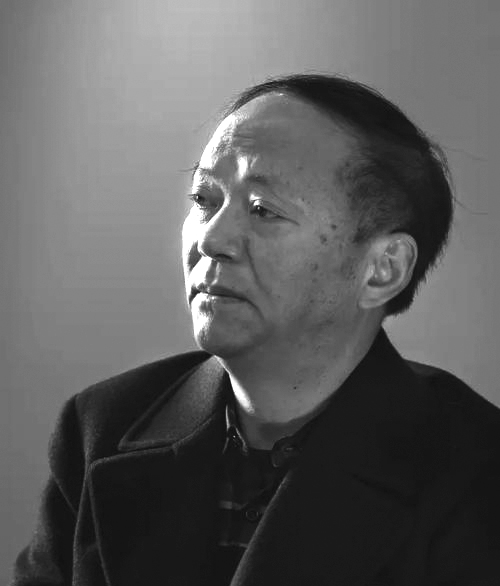
作者简介:周闻道,本名周仲明。散文流派“在场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