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2023年第4期|叶梓:碧螺春月令
圆圆,多朴素的一个名字。
她是2009年从杨湾嫁到双湾的。杨湾和双湾,是东山镇的行政村,下面还有自然村。圆圆现在住在双湾的涧桥村,涧桥一词很是清新,让人能想起古老的新涧亭和白居易“烟萝初合涧新开,闲上西亭日几回”的好句子。
我跟圆圆的认识有些偶然,有一次受朋友所托,给她帮了点小忙,事成后圆圆非要约着吃饭,我婉辞不得,就在石湖边的一家饭店见面了,算是正式认识。此后,每年碧螺春上市,圆圆都会托朋友送来点自产的碧螺春。那次饭席上我们也互加了微信,朋友圈里的她,这段时间忙得也是一塌糊涂。
每次收到茶叶,我对朋友说:一点小事,都几年了,难为情啊。
朋友回话:东山人么,就这样。
东山人的形象,立马在我心里更加高大。
东山是太湖边的一个古镇。2022年的春天,苏州的疫情此起彼伏,人心慌张。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给圆圆微信留言说,要不要我来帮你卖卖茶?她回我,好啊。其实,也就是一句玩笑话。数日已过,疫情控制住了,想出门透透气,就去她家的茶园浪荡了大半天。后来,我突发奇想,决定以她家的茶园为根据地,观察碧螺春一年里的长势。现在,学着汪老头子《葡萄月令》的笔法,写写碧螺春的一年四季——也算是《碧螺春月令》。
一月,江南偶尔会落雪。去年就落了雪。落了雪的茶园更加寂静,更加美。别人踏雪寻梅,茶农的孩子雪天里到茶园里走走,也挺好。落了薄雪的太湖,茫茫无垠,真正的水天一色。茶树喜阴,这湿漉漉的空气最合适。偎着万顷碧色的太湖,碧螺春茶树的心里,高兴着呢。往小里说,是太湖水滋养了它;往大里说,太湖就是它一骑绝尘的绝对靠山。
二月,我总会抽空去茶园看看茶树的长势。
圆圆家的茶园有两大块,一块在山坞上,一块得从双湾码头坐自制的铁皮小船才能到达,算是滨湖低地。太湖的湖湾处,有不少这样的低地,是水稻和水产养殖区。她家的茶园,是她公公和婆婆在侍弄——公公1963年生人,有点南人北相,跟我很投缘,婆婆要稍小一两岁。这些年,山坞里的茶园我去得多了,所以就想去看看湖滨低地的茶园。在双湾码头,他站在船头,手一摇,“突突突”几声响,船就发动了。去茶园的水路,也就十来分钟,但其美景和意趣却如入桃花源。我越来越喜欢这块茶园,渐渐熟了,去的次数也多了,与他们相处得像老朋友似的。圆圆的老公开了一家外贸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平日爱喝些酒,偶尔,我们还能一起喝两杯。
这个月,两位老人满怀希望,等茶树发芽,心里有期盼,也有忐忑。月底了,还要施一次肥,山浪人家叫“催芽肥”。山浪人家,是太湖边东山、西山人对自己的称谓,类似乡下人的意思,有那么一丁点儿的自卑。施肥得从茶行的上坡开沟,施的基本都是尿素,偶尔会有硫酸铵。
三月,采茶季到了,一个字,忙。
采茶季,圆圆总忙着发朋友圈,下单,打包,对接快递业务。圆圆说,这一个月的节奏,像是在打仗。好在这些年卖茶卖出了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都会提前预订,茶炒好后直接邮寄,反而比以前简单了。有些客户家住在城里,她偶尔会开车上门送货。
月初,茶树上的芽,小而嫩,极可爱。这个时候,只要有一场雨,茶芽就疯长开了。开始采茶,就要没日没夜地忙。早出晚归,是茶农最真实的写照,常常是凌晨一两点从家里出发,午饭在茶园吃,下午两三点才回来。每年茶叶开采的具体时间也不一样,有时早,有时会晚几天,纯粹是看天吃饭。而且,不同的品种采摘的时间也不同:苏州本地产的碧螺春茶树品种,是群体小叶种,有线丝种、酱瓣头种、柳叶条种、楮叶种、鸠坑种、祁门种等等,一般在清明节前三四天开采,但从外地引进的乌牛种还要更早一些。就算是同一个品种,因为光照、位置不同,采摘时间也不同。圆圆家的茶,湖滨低地的熟得早,采完了,山坞里的刚刚好。采茶也真是一门大学问。
回了家,也闲不下来,要炒茶。拣茶的人,大多是雇来的,工资日结;而炒茶是门手艺活,只有自己炒才放心。但愿意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前些年,我还没有移居苏州,经一位朋友牵线,拜访了施跃文先生,地点就在他的东山茶业合作社。他是苏州有名的炒茶高手。我跟他交流了整整一个下午,也长了不少见识。听他讲述、看他示范,才懂得碧螺春的制法必须要做到“手不离茶、茶不离锅、揉中带炒、炒中有揉、炒揉结合”——这个包括了杀青、揉捻、搓团显毫、烘干四道工序的过程,是碧螺春茶从叶到茶完美蝶变的关键。
圆圆的公公曾告诉我,当地茶农有句顺口溜:
铜丝条,
螺旋形,
浑身毛,
一嫩三鲜自古少。
说的就是检验碧螺春的标准。
如今我来苏州六七年了,竟然再没有见过施跃文先生——他现在已是碧螺春制作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两天,从万里之外的摩洛哥传来喜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的第43个人类非遗项目,也是苏州的第7个。其实,这是一个庞杂的系统项目,包含了15个省份的44个小项目,仅江苏就有苏州洞庭碧螺春制作技艺、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和扬州富春茶点制作技艺入选。
其实在我看来,那些籍籍无名的炒茶人更是功不可没。这次入选非遗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贯穿了采茶、制茶、饮茶等各环节的传统制作工艺,以及过程中衍生的相关习俗。在这之中,传承人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普通茶农的作用也不可小觑。普通百姓与茶联系的日常生活,代代传承、生生不息至今,才组成了意蕴深长的中国茶文化。
当我在电话里告诉圆圆公公这个消息时,他说:
山浪人家,不懂哉——
他把那个“哉”字,拖得很长。
四月,继续采茶。
这个月采的茶,做炒青最好。碧螺春是卖给别人的,炒青是口粮茶,留着自己喝。在苏州,老茶客往往更加偏爱炒青。碧螺春太嫩,两三开就没味了,炒青呢,一杯能喝一上午。但圆圆家很少做炒青,因为忙不过来——除非熟人和回头客有预订,才会照单制作。
忙活了一年,炒成的茶不足一百斤,给一个家庭贡献的收入也还不到十万元。茶,只是她家收入的一小部分。我问圆圆,以后公婆老了,茶园怎么办?她一脸茫然,说,没想好,也不知道自己愿不愿意干。过了好一会儿,她又说,边走边看吧,说不定过些年又喜欢上茶园呢。
五月,天渐渐热了。
茶农们还是要天天去茶园,修剪茶树。这是个技术活。圆圆的公公和婆婆都是行家里手,干了一辈子,早就了然于心了。这段时间最重要的一项活,是焖树,也就是把剪下的枝条就地铺在茶园里。如果你仔细观察一棵碧螺春茶树,就会发现,茶树的根部比起其他树要粗壮,而枝条又很细,这就是一年又一年焖树的结果:根部一直在长,而枝条总是新的。只有新的树条才会生长出鲜嫩的茶芽。二十多年前,茶农们会留着枝条,采夏茶,也采秋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没人这样弄了,就让它烂在茶树跟前当肥料。这倒让我想起范成大《劳畲耕》里三峡深处“颇具穴居智,占雨先燎原”的做法。
六月,枇杷熟了。
去采枇杷,总能和茶树相遇,但就像村子里遇到熟人一样,顾不上多看一眼。碧螺春茶园是典型的茶果间作区。这个“果”字,可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圆圆家的茶园里,是清一色的枇杷。因为双湾这一带最宜种枇杷。去双湾的路上,就能见到一巨幅广告牌子,上书14个大字:世界枇杷看中国,中国枇杷问东山。14个大红字的下方有3个小字:双湾村。苏州本地人都知道,双湾的枇杷品质最好,所以价格也要高一些。碧螺春茶园里,枇杷最多,其他还有银杏、青梅、杨梅、石榴、柑橘、板栗、桃子,我能记起名字的差不多这些。后来听朋友说,还有一种叫胜胜子的树,但我一直没见过,也许碰到过,但也认不出。
这种茶果间作种植还有一个更学术的名字: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这种茶果复合式的立体种植,恰好形成了梯壁牢固、梯度布局、水土保持良好的生长模式。碧螺春茶树喜阴,怕阳光直晒,也怕霜雪寒冻,而果树恰好喜光,又抗风耐寒,刚好为茶树提供了遮蔽骄阳、蔽覆霜雪的良好生长环境。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因其既有悠久农耕文化历史,又具备经济与生态价值的高度统一,于2020年1月列入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算是第五批。自此以后,我每泡一杯碧螺春,就像是阅读一次这方山水的家园观念和历史记忆。
古人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说,谈的是交友之道,对碧螺春茶园来说,何尝不是这样呢?碧螺春的佳妙之处,就是滋味里藏着隐隐约约的果香。茶树和果树根脉相通,枝丫相连,果树的花粉、花瓣、果子、落叶等落入土壤,碧螺春茶可以从土壤养分中吸收到果香和花味。这些茶树天天跟让人垂涎欲滴的果子长在一起,怎能不香呢?苏州的老茶客,嘴刁得很,有的能尝出茶园里枇杷树多还是橘树多。只是这些年橘树越来越少了,因为橘子卖不上好价钱。有人说,整个东山,再也找不到张艺谋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时那么盛大的橘园了。
我不知真假。
七月,杨梅熟了。茶树的花芽儿渐渐成形。偶尔,我会去茶园,同他们一起锄锄草。
八月,溪水流过老茶树。水声潺潺,不知流往何处。圆圆带我去看山,我问她溪水从哪里来,她说不知道;流向哪里,她还说不知道。山坞里的夏风吹着,比城里清凉得多,人心也是舒畅的。环顾四周,纷红骇绿,满目斑斓,不禁想起范成大当年过永州愚溪,“我欲扁舟穷石涧”的冲动。此际的我,最奢侈的梦想是踏遍东山西山的每一座山坞,跟每一株茶树说一句:你好!
而这个月的茶树,有时候会遇到高温天气。
2022年的夏天,苏州迎来了连日高温,气温最高时达40℃左右,池塘干涸了,河道也干涸了,茶树和果树危在旦夕。旱情严峻,只能主动出击,原本的农闲季泡汤了。高扬程喷灌泵用上了,汽油机泵用上了,高扬程电泵也用上了,就连镇上调拨的绿化养护车和消防车也用上了。茶农们每天起早贪黑,顶着烈阳干,就是为了救活一棵又一棵茶树和果树——往大里说,是坚决打赢农业抗旱“攻坚战”,往小里说,也是救活自己的命根子啊。
九月,施肥。最好的肥是人工肥。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没有了,就施复合肥。圆圆回忆说,她小时候,老父亲给茶园施的是菜籽饼,一种特制的人工肥,效果极佳。
十月,主要工作是防虫。
茶园里的虫,主要有茶尺蠖、茶叶瘿螨。尽量不用农药是果农的执念,所以用得最多的办法是物理除虫:设置一个诱灯,虫子趋光而动,迎光而来,然后用高压电网进行触杀。
十一月,橘子红了。
碧螺春的花也越开越盛。茶树的花初开极小,白色;第二天略微泛黄;第三天,黄色更重些。茶花花期长,到开败差不多要一个月。但碧螺春的花是要采掉的,得把茶树的力气留下来,等着第二年长芽呢。茶树在开花,边上的枇杷树也鼓着花苞,跃跃欲试的样子。无需走近就能听到旁边蜜蜂“嗡嗡嗡”地在飞。再过些时间,就开始大批量熬制枇杷蜜。
2022年11月8日,我为了拍摄碧螺春的花,去了圆圆家的茶园。她的公公和婆婆带我在茶园转了一大圈。他们一边跟我说话,一边忙着采花,手似乎从来没有停下,采掉的茶花就顺手扔到茶树下。中午返回,我跟她公公喝茶,婆婆下厨烧饭。不一会儿,一桌菜就好了。红烧塘里鱼、银鱼炒鸡蛋、太湖虾、蒸白鱼,汤是排骨冬瓜汤,凉菜是东山白切羊肉,说是早晨从东山镇上有名的矮马桶羊肉店买回来的。
喝不喝酒?
不喝。
那就多吃菜吧。她又特意加了一盘油焖茭白,使劲劝我:现在正是吃茭白的时节。
十二月。茶树的花也采完了,剩下光溜溜的枝条。这时间差不多也要施肥了。这次施的肥,是给明年的催芽肥打基础,山浪人家叫基肥。冬天天冷,但基肥也不敢少,少了,茶树翻过年就缺底气。这跟人的身体一样,底气不足,干啥也干不好。施完肥,才算真正闲下来了。
圆圆总是自嘲,自己是半真半假的茶二代。其实她虽然不怎么去茶园,但骨子里是爱茶的。春天新茶上市,就卖茶,但一年中更多的时间她经营着一家茶餐厅,就在滨湖大道上,也算是开在了家门口。餐厅名字很独特,叫柒茶。柒,取的是苏州方言里“吃”的发音。茶餐厅很雅致,是她自己设计的,辟有两间独立的茶室,还有两个包厢对外营业,但不是客人来了就能吃到,需要预订。圆圆说,这样做是为了留出足够的时间,把最有特色、最时令的东山美食提供给客人。她是一个地道的“吃货”,对吃很感兴趣,现在还在挤时间上烹饪研修班,学习中式面点的做法——原本忙碌的生活里把自己安排得如此满满当当,内心是多么热爱生活啊。偶尔闲下来,圆圆也会读点跟茶有关的书,《茶经》她也翻过,似懂非懂地读,关于碧螺春的文化书籍她也读过不少,也许是一知半解,但读了总比不读好。
人生在世,虚浮不定,所以也叫浮世。一年四季里的碧螺春,也是在虚虚浮浮中度过一日又一日。人呢,喝着喝着,一年也就过去了。
又一年,过去了。
如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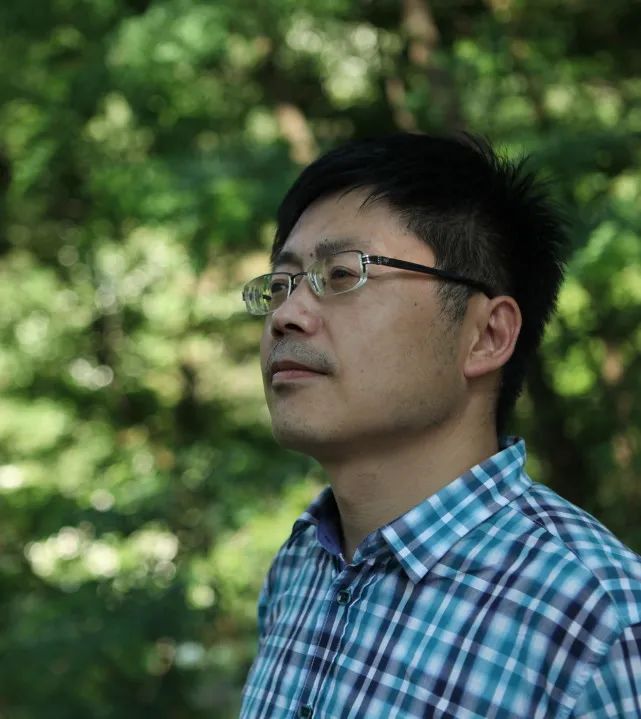
原名王玉国,甘肃天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出版有散文集《陇味儿》《天水八拍》《石湖记》10余部。近年来致力于南宋诗人范成大的研究。现居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