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告别的一切》:无法告别的困境与追寻
晏杰雄、黄赞琴、肖雨桐、薛云、陈亚蓉等5人正在讨论中
晏杰雄:中南大学原创文学读书会本期围绕路内最新长篇小说《关于告别的一切》进行细读。作者曾言:“这本书试图讨论一切的‘非一切之物’,彻彻底底的不彻底,永恒的半途而废或是认真的半真不假。”初遇与重逢之后是告别与不告而别,别离、隐退之后则是记忆的复现与变构,这部典型的“路内式”小说借此布下指涉个体精神困局与时代更变的深层隐喻,也留下众多可供探讨的切入点。主体叙事与所附着的嵌套叙事在情节错位的比照之下,指向自由无碍地重构命运、重建秩序的意图。在日常生活书写之中,作者、叙述者与人物交混发声,又在隐含哲思的话语迷宫内叠加出多声部的叙事效果,颇具艺术表现力。下面几位同学分别从小说的主人公情感经历、自我与他我之思、叙事艺术、女性群像等角度展开深度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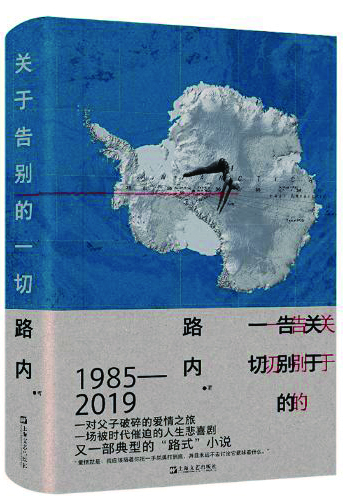
黄赞琴:在告别中寻找心灵的寄托
《关于告别的一切》主要围绕李氏父子的爱情之旅展开,其中,主人公李白的情感经历颇令人感慨。从心动、守护到背叛,从告别到重逢,他在繁复的感情之网中不断追逐寻觅,所寻的绝不仅是爱情,更是身心可依之所、精神寄托之地。
小说中,李白母亲在他年幼时不告而别,徒留他与父亲生活。这一失去女主人而男主人又窝囊平庸的家庭,无法给予孩子良好的成长环境,周遭的社会环境又打压着这个残破的家庭。李白自童年时代便缺失母爱,成长历程中内心多受压抑,以致在此后的感情故事中,他对母爱与母性角色的潜在渴求便外化于对待多组情感关系的态度上。例如,其父李忠诚想要追求俞莞之,李白并未产生反感,反而十分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俞莞之等人的出现及善意之举,为年少的他带去了温暖和安全感。又如,曾小然之于李白,是永远不能忘却的初恋。较李白年长的她更似姐姐,李白对她不单喜欢,还有依赖,他的灵魂在与她相伴的时光里寻到了寄居之处。这是李白心灵第一次得到安慰,经过时间的沉淀,这段难得温馨的时光成了他一生的梦乡。但与初恋告别后,他再度失却寄托,心灵在反复的告别与寻找之间来回漂泊,始终难寻停靠点。
经历着不断的告别,李白的心灵处于“无所依”的状态,互相交织的渴望、彷徨与逃避长久地伴随着他。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他对周边物事产生了更多的理解,心理状态更为矛盾,所追寻之物也更为复杂。李白不断告别又开始新的感情,如此重复,他看似自由、洒脱,实则是心灵无所寄托。他明明能够找到栖身之地,但仍选择继续孤身追寻,是因为他在一次次告别中,早已处于一种淡然的状态,又或许是幼时父母感情悲剧带给他心理创伤,不愿去相信婚姻。好在李白仍是有思想力的,不同于李忠诚浑浑噩噩地过完一生,他有自己独特的处世原则。在爱情之外,他也在认真生活,或许他在情感中寻找不到的东西,可以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找到。行进至小说结尾,李白仍未收获一段彻底圆满的爱情。也许,在不久后他会投入新的感情,又承载更多的告别,直至寻到心灵最终的寄托之所。
肖雨桐:在束缚中弥合的自我与他者
路内在书中作了一个精心设定,将主人公命名为李白,与唐代大诗人李白同名同姓。身为作家的主人公看似是话语与真理的主宰者,但实际上更像是边缘人物——不仅与历史脱节还蔑视宏大历史,又将生活处得一团乱麻。相比大诗人李白,书中的李白倒是落魄潦倒的,只剩冗长乏味的“艳史”可供翻阅。小说中的“规训”无处不在,作为权力的微观具象驯服着书中每一个人,使其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界限。因此李白永远处于一种断裂状态,被动地消化他者、吸收他者,但小说的存在又分明是李白的传声筒,以荒诞的反差与鲜明的话外音回荡着声声抗争。
路内曾言:“我们是否敢于和这个最细分的‘他者’决裂?我看不一定。”在小说的两次动物园事件中,作者便连接起一条探讨自我与他者的纽带。第一次时,狮子在李白面前杀死了饲养员,人类所“依赖他者钦佩与承认的自尊”成为破裂的残骸。然而,当再一次回到动物园时,李白选择主动跳进熊山。这一跃看似是为了解救小猫,但实际上传达出自我的超越意识。前后事件在对比之间映照出自我与他者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他者在某种意义上就似子宫,无论自我走多远,都走不出水乳交融的汲养与唇亡齿寒的羁绊。
但即便如此,书中又以双重束缚的关系指向对“自我”的回归之路。自李白的母亲离开起,李白与青梅竹马的曾小然便以彼此替身的身份,杂糅地叙述着“自我”与“他者”的依存与对峙。“尿不尽”成为两人的幼年心理创伤,伴随着他们以不彻底的姿态游离于性和爱之间,与一段段蓝色易逝的爱情邂逅又告别,终日漂泊流浪。同时,两人又在镜像的凝视中形成对峙。重逢后的曾小然坦言自己“远不像看上去这么整齐”,在祭拜父亲之后方得大梦初醒,留白式地透露出追求自我的倾向。而李白最终也说出了“我像是掉进了熊山,面对一头正在醒来的,熊”。前半生霎眼即逝,两人就此迎来转折,自我与他我交织划分出镜像外的偏差。于是,“我”在自我中生成,也在他我中修正。
薛云:虚构时代的观望者
幽默的语言是路内创作的引子。将李白在唱台上不带妆不开口之状比作来到大型枪决现场,将李白向期刊投稿之举比作V-2导弹射向伦敦,这种幽默是作者自成一体的语言风格,是对小说主人公内心真实情感的掩藏与修饰。对主人公李白而言,嬉闹和调侃似乎有一种可以抵御时代洪流侵袭的错觉。他就在这般“苦中作乐”里长大,岁月并未把他改造成大腹便便、横肉满脸的疲惫中年人。与曾小然重逢时的他,仿佛还是中学时代那个小镇吴里长大的少年。所以诙谐的语言带来的绝不仅是片刻的欢笑,还有笑声过后才真正显现出的感伤余味。作者状似无意显露的幽默,也舒缓了小说中岁月流逝、时代更迭带来的压抑和苦痛。
《关于告别的一切》展现了作者对现代小说技巧的娴熟运用。在语言风格之外,小说采用了与《慈悲》等作品相同的双线时间结构。一条自李白的童年记忆回溯,另一条则从他与曾小然重逢起步,两条线索在交叉之间向前推进,终结于李白在动物园与方薇的通话。“此刻”与“过去”二元叙述时空不断穿插上演,独特的叙述视角与相异的时空交织成完整的故事。交叉并行的双线叙事使得小说像一首为主人公的人生谱就的乐曲。在双线的交汇点,“此刻”与“过去”由一个词、一句话、或一个故事衔接起来。二元叙述时空之间的即时回应负有难以描摹的宿命感,使得小说不仅像一首乐曲,也像钢琴交错嵌合的黑白键,紧密相依,而又沾染上时空转换所附带的不同色彩。
小说虽然大部分为第三人称叙述,但更像是李白以第三人称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大段第三人称叙述后,作者偶尔会没有预兆地转换为第一人称,全知和受限视角就在人称转换中交替,正意味着叙述者选择以个人化的视角来抒写自己的内心世界。间或偶尔插入的第一人称叙述,其实可以看作李白这个真正的叙述者,忘记了掩藏自己的踪迹。路内在《天使坠落在哪里》中这样写道:“我肯定不是局外人。我不是站在外面,不是站在街边,我像是一个不小心闯了红灯、站在路中央观望着这个时代的人,有时候觉得看到的东西很可笑,有时候觉得自己站在那儿也很可笑。”路内通过小说创作让读者看到自己眼中的时代,李白则通过视角切换将身为旁观者的读者拉入故事当中。这是路内文字的魅力,也是小说创作的魅力。
陈亚蓉:鲜活的生命过客
路内在《关于告别的一切》里运笔形塑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赋予了她们鲜活生命和独特品格。小说里,“鲜活”如“白月光”的曾小然,她有着如普通邻家姐姐般的懂事和沉稳,但更惹人注目的,是她如刺猬般执拗的独特锋芒——父母合葬的决定不允改变,青涩爱情带来的直白羞辱于她而言只需“付之一笑”;周安娜,交往52位男性是她对世俗规矩的反叛,她如长有反骨的独行侠,放荡不羁且个性张扬。正如书中所说“她像一个赌徒随意抛弃了手中的扑克牌,造成一种漫天飞舞的视效”,她永远骄傲且自由;还有钟岚,普通的钟岚不起眼吗?不,她好似一个矛盾体,倔强外表下包裹着天真而柔软的、渴望被爱的心,烟火气息里潜藏着对文艺的内在追求……作者笔下的众多女性似是百花园中坚韧且鲜活的花朵,盛放或凋零时永远保持着独一无二的生存姿态。作者借助诸多女性形象传达自身的态度观念,即女性本应各具独特气质,或天真,或倔强,或勇敢,或洒脱,或骄傲,而不应为世俗的眼光、身份的约束、糟糕的情感经历、鸡毛蒜皮的琐事所定义。每位女性皆是鲜活灵动的生命个体,不论扮演何种社会角色,都是独立而独特的。
将这些女性人物视为独立个体时,她们与主人公李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便得到了解释。不论各人以何种感情和身份产生交集,爱情、友情、亲情或是一夜情,青梅竹马、朋友、偶遇者或是爱人,这些女性人物最终只是李白父子生命中的过客。情感关系的结局是否完美因此也显得无足轻重,反而会得到读者的宽容和理解。在容纳了过去与现在、相恋与背叛、相伴与分别、生存与死亡的种种时空里,面对诸多过客关系的李白,自始至终坚持着他的情感立场,即“爱情就是:我应该陪着你把一手烂牌打到底,并且永远不去讨论它意味着什么”。
然而,即使女性角色往往以过客身份掠过,她们依然在整部小说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再粗壮的树干,失去绿叶的装点总显得单调乏味,作为架构小说主体的一部分,这些鲜活的独立个体的存在意义便寄于其间。对于李白父子而言,不论联结彼此的是何种情感关系,不论最终上演的是悲剧还是喜剧,这些各具风采的女性角色都是他们记忆里色彩明丽的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