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种》2022年第11期|李晋瑞:红四毛和白刺毛进城去染发(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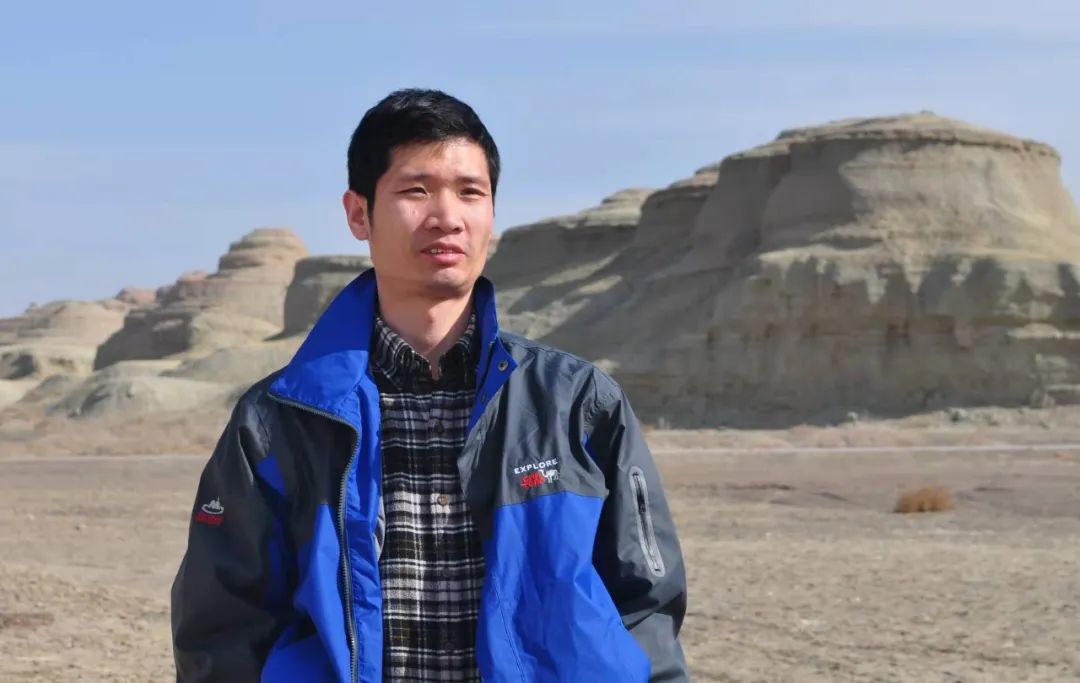
李晋瑞,70后,山西平定人,以小说创作为主,偶涉散文随笔。主要作品有《原地》《爱上薇拉》《中国丈夫》《别离》《陌生的玩笑》等,其中《中国丈夫》曾获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别离》入选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红四毛和白刺毛进城去染发
文/李晋瑞
人们之所以都叫他“红四毛”,是因为他有一头红发,是家中第四个男孩,还因为他大笑时会呈现出一张血红大嘴,还有,他总喜欢说“我要吃掉整个世界”。不过根据我的回忆,他的头发并不算红,顶多是偏黄。在我们那一带,或者说在那条川里,人们的头发普遍又黑又密又硬,尤其是男人,理发时,推子从后向前,从下向上,逆茬而行,碎头发就像铡草刀疯狂铡出的草节儿一样四处乱飞。红四毛的却不是。他的头发细细软软,柔柔顺顺,黄里带着微红(只有在阳光下细看才能看到),总是那么服服帖帖溻在脑瓜上,再加上他经常和别人说,他命贱,贵不过四毛,综上所述,人们似乎就非得叫他红四毛不可了。
红四毛因为这个名字自卑过一段时间,走路时总盯着自己脚尖儿看,似乎只有一双脚是他最好的朋友。当然后来,他很快发现,其实自己的脚也不可靠,他真正的朋友是一个因为满头的少白头而被别人叫作“白刺毛”的人。不过在家中,红四毛的兄弟姐妹,包括父母对他都很好,无论做什么都让着他。可正是因为这个让,让红四毛百般难受。有一次因为他走路总是低着头,母亲担心他会驼背,狠狠地掴了他一个耳光,他就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对着一面镜子怔了一个下午,晚饭时,好心的姐姐去叫他吃饭,敲半天门却无人应声,姐姐只好捅开窗户纸往里看,她想看看红四毛在里面到底搞什么名堂,结果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姐姐把情况告诉母亲,母亲把手里的勺子往锅里猛地一杵,厉声下令——谁都不准找他,他要是有本事就永远别回来。
几年后,红四毛和我坐在县城里偏僻一角的饭店吃一碗刀削面时,他跟我说,他母亲说出那种绝情的话,完全在他预料之中。因为母亲受够了他的敏感,受够了过那种小心翼翼的生活,她本来是一个喜欢喂驴养马,放到战争年代可以挎上盒子枪上战场的女人,所有家务里那些需要轻拿轻放或提心吊胆的事她都不喜欢,也做不来,即便地里的谷苗需要间时,她宁愿给牲口去割草也不去插手,家里的孩子一个个轮流长大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姑娘,自从她可以把头发捋到后面扎上头绳她就再没有碰过她,十一岁那年这个姐姐因为饿,自己踩上板凳把切好的红薯、南瓜,掰好的豆角,放进锅里,自那以后红四毛的母亲就再也没有操心过做饭的事。母亲生了那么多孩子,可是她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生那么多,每生一个她就把那个孩子称为“讨债鬼”,可是怀里的讨债鬼还在吃奶,她就发现自己的肚子又大了。以她的性格,她可以学村里女人秘密传授的经验,坐到尿锅上进行生产,那种口大底儿小形似小瓮的器物,可以容下一个婴儿,而尿锅口的大小,只要女人踏踏实实坐上去,就可以将它封个严严实实。村里有婴儿是死在这个尿锅里的,当然对外宣称的是婴儿一掉下来,就没有了心跳。红四毛跟我说,他搞不清母亲为什么不以那样的方式早早要了他的命,因为母亲说过,他确实是被生在尿锅里的,然后——红四毛做了想象,多可怕啊,如果自己像哺乳动物那样,一离开母体就能睁开眼睛,那么他看到的将不是母亲的脸,而是母亲的屁股。红四毛是这样说的,不过接下来要说的才是重点,他说,他应该是母亲不想要的那个孩子,因为只有那些不想要的孩子才会被母亲生在尿锅里,可是自己为什么没有死呢?应该是,壮实的母亲并没有因为生产而耗尽力气,兴许当时她的双手还扒在炕沿上,她很可能是想检查自己有没有把尿锅坐严实时,突然发现尿锅里居然是一个几乎看不到一根胎毛的婴儿,可她的孩子从来不是这个样子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一头乌发,怎么轮到这个——难道这是老天的一次特意安排?为了重新看清婴儿,也因为心里充满了困惑,结果身体失去平衡倒到一边,尿锅被她撞翻了,红四毛于是从中扑了出来,在没有看到世界时就有了“二次出宫”的经历。母亲把这一切视作天意,红四毛这才活了下来。在那个把自己反锁在屋里面对一面镜子发怔的下午,红四毛一次又一次在脑海里重演着自己出生时的情景,镜子里那个人,皮肤那么白,头发那么红,简单就像个外国人,他甚至怀疑自己的出生纯粹是母亲杜撰的故事,以他的长相,自己极有可能是捡来的,因此家里人才对自己那般忍让。
那天下午,他一直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笑,可镜子里的家伙也对他发笑,笑得没意思了,一怒之下,他就把镜子砸了。然后从后窗跳了出去,就穿着一身只有从流浪汉身上才能扒下来的衣服,衣兜儿有两个是漏的,裤兜也是,衣领补过三次,袖口底边脱了丝,本是深蓝色,却早已变成了灰白色。他快速走过暮霭沉沉的街巷,出村时,头上的月亮已经皎白。他知道绝不会有人找他的,那个家的孩子太多了,一共八个孩子,多他不多,少他不少,再仔细想想,兴许母亲的真实想法是,多走上几个孩子才好呢,每天闹哄哄的,少一个,就能多一份清静。等他再大一点儿时,他的想法就变了,觉得那可能是母亲的一种忧伤,她厌恶了这个穷呵呵的家庭,或是她受够了这个家庭的穷了,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一个个懒洋洋的,头不梳,脸不洗,一到晚上把臭鞋扔到门外,臭脚还留在屋里,她可能就觉得——这么一大堆的孩子,哪怕是谁,只要他离开,哪怕他出去和猪和狗和一只鸽子待在一起也比留在这个家里强。可是直到他死,我知道,他都没有向母亲问起过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看来,问也白问,母亲是不会给他什么答案的。
红四毛说,那天晚上他走在月光下的山路上,双脚其实是不着地的,起初他并不确定自己要去哪里,他的身体在前移,耳朵却一直向后背,他希望自己的家人,不管是谁能够跑出大门,冲着那座黑黢黢的大山喊上一声“回来”,他迅即就会返回去。可是没有,他越走越远了,家里连只狗都没追出来。他已经走出村庄,却不知道脚该迈向何方,但是无论去哪里,都不能回去,一旦回去自己就输了。红四毛摇着头,其实后来他怎么想都不知道自己一旦回去输掉的到底是什么,但一个“输”字,逼着他坚决往前走,这时他突然想到另一个因为外貌和自己有着相同感觉的同病相怜之人,他的初中同学,当然也是我的同班同学——白刺毛,初中毕业后,因为成绩不好,他俩都回家务农了,他决定先去白刺毛家待上一晚。
白刺毛家我知道的,就在我们村再往前一点儿的山洼里,不过需要爬一道坡,那个山洼里只有他们一家,实际上就一处山庄窝铺。白刺毛家人丁不兴旺,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白刺毛居中,上面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因此白刺毛很羡慕红四毛,有一年夏天白剌毛在红四毛家住过一晚,一盘炕上赤条条躺一群孩子,那画面总让白刺毛想到军营里的战士,他跟红四毛说,想想都带劲儿。白刺毛总说自己没劲儿,他母亲不爱说话,他哥哥闷葫芦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妹妹杨红艳倒是口齿伶俐,却早早去县城打工了。
红四毛说,他推开白刺毛家的院门,最先看见的是白刺毛的哥哥,可是白刺毛的哥哥连哼都没对他哼上一声。红四毛进屋,白刺毛正在吃饭,一回头看见是他吓得差点儿把碗摔了。白刺毛对红四毛说:“你这是——刮得哪个方向的风?”
“我来看看你,听说你小子拿到驾照了。”红四毛心里很沮丧,但不能表露出沮丧。
“看我?”白刺毛说,“不能吧——我明白了,你是听说红艳回来了吧,红艳是下午刚回来的,她现在县城学理发,她说等她学成了,咱俩的头就交给她理。”
“去去去。”
白刺毛还笑,说:“不过红艳回来后又去我姑家了,今晚不回来了。其实,你那点小心思还能瞒过我?!”
“既然瞒不过,那咱们就合计合计。”
“不过,这事要成,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白刺毛依然在笑。
这时白刺毛母亲进屋了,问红四毛吃饭没有。红四毛说吃了,他是吃过饭才动身的。
红四毛回忆说,那天晚上是他经常夜宿白刺毛家的开始。为了便于说话,他和白刺毛单独住了一间屋子。身材颀长、肤色白皙的红四毛,躺在身材敦实、皮肤偏黑、满是少白头的白刺毛身边,就像躺在一棵大树旁,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包括他自己独一无二的红毛,以及白刺毛硬茬茬刺猬刺一样的白发,真像是天意的安排。
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就是红四毛和白刺毛出事的那天,红四毛专门到县一中来看我。我们坐在一个偏僻的饭店里,就是街角突然多了一个棚子,旁边支一个汽油桶做的火炉,最高级的菜是蒜薹炒肉,大多食客只要一碗面,而不知道哪天又突然就消失了的那种临时饭店。红四毛说我怎么也该请他一顿了,因为在他认识的人中我是最富有的那个,理由嘛,有三条:一、我父亲在外面当工人,还是正式工;二、我是我们家的独子,哪怕我家房屋只有一间地亩只有一垄,到底也全是我的;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初中三年,我们同宿舍了三年,我是唯一可以带干粮而且经常是白面馒头去学校的人。他说,同学三年,我没吃过你一口馒头吧。我说,没有。所以你得请我,好好请一顿,起码得有肉、有酒。我问他,白刺毛呢。因为我知道他们俩好得像穿一条裤子的人。他说,在红艳那里,他知道你不喜欢他。其实我确实不喜欢他,无论红四毛,还是白刺毛,我都不喜欢,天然的不喜欢,觉得他们臭烘烘的,身上有虱子,还穷狠穷狠的一股痞子劲儿。但他来了,专门来看我(他是这么说的),我不可能不见他。不过,我跟他说,你小子都在社会上混了,应该你请才对。他说,那是下顿,这顿必须你请,算是补请,你想想以前多少人请我,你从来没有请过我吧。于是我想到初中时,红四毛和白刺毛在巷子里逼住某个同学暴揍,然后晚上他们舔着油滋滋的嘴回来的样子。我说,那行,你点吧,你可劲儿点。我们坐下,他却只点了一碗刀削面。我说再来点吧,起码花生米、黄瓜、豆芽拼上一盘。他没有拼。只是让老板加了两个茶叶蛋。他说不行,我这个人重感情,把白刺毛扔在红艳那里,我在这里吃过油肉吃不下,我还是留着肚子吧,等见了白刺毛再吃,我答应他要请他吃过油肉的。
我和红四毛一人一碗刀削面就那么吃着。他就告诉我,他和白刺毛躺在白刺毛家炕上的那天晚上其实讨论了好几件大事。那时他大哥已经在外地修水库开山时被火药炸死了,他二哥嚷嚷着要娶一个寡妇,问题是那个寡妇要带三个男孩来,他三哥一百个反对,威胁说如果二哥真娶那样一个寡妇,他就去下煤窑,还要死在里面,要是死不了,他就砸断顶柱来个自我塌方。比他小的三个兄弟一听可兴奋了,一起打闹着跑出去,有的笑,有的哭,说他们要去告诉村里人说他们的三哥要自己砸死自己了。红四毛夹在中间,对这些事似懂非懂。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但作为一家之长,就算做做样子也得有个态度,孩子们一个个都会长大,男婚女嫁是绕不过去的人生大事,他能怎么办,算算家里只有三间房子,老二成家要是占上一间,剩下的家里人还怎么住,他试探着和老二商量,看老二能不能去寡妇那边住,老二一句话就顶回来了——爹,你说的这话像不像一个当爹说的话嘛!红四毛的父亲就只剩下坐在炕沿上默默地抽烟了,他斜睨着身后,一盘土炕上,一领铺不满的破席,一到冬天孩子们取暖全靠柴火烧的热炕而不是身上的被子,就这么一个光景,自己羞愧归羞愧,可毫无办法啊。谁知这时父亲竟然问起红四毛来,毕竟除了老三,红四毛就算最大的男孩了,可父亲哪里知道,这个红毛孩子早已经忍无可忍了,他气不下二哥的没出息,更气不过三哥的自私,但站在他们的角度,他又无法指责他们,于是他对父亲说,这又不关我的事,问我干吗,哪个神经病才会管你们家的事。听听——你们家的事,那到底谁家的事?可红四毛当时就是这么说的,他哗地起身,快速从父亲面前经过,并夺门而出,在他重重将门摔上的一瞬,他发现父亲低下了头,又听到母亲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从老的到小的,一家子废物。
那天晚上,红四毛想到了这些,尤其想到母亲的那句“一家子废物”,他用脚蹬了一下白刺毛,说,白刺毛,你说咱俩是不是好兄弟;是,当然是,反正我看你比看我哥要亲;我也这么觉得,那咱们商量点事吧;怎么,要我现在起来和你对着月亮星星拜把子吗;没那个必要,咱不走那个形式,有心比什么都强。我是说,咱俩的关系还可以更亲一些;怎么个亲法;让你妹嫁到我们家;可以啊,不过得有个条件;什么条件;那你姐得嫁到我们家来;嫁你吗,我姐比你大很多;嫁我哥;那也大三四岁了吧,还有我姐——那屁股,磨盘一样,你哥会喜欢吗;喜欢,大屁股女人能生,我家就缺孩子,让她嫁过来赶紧生,那样我妈就顾不上瞅我了;那这不是换亲吗;你管它是什么,至少这样可以省彩礼啊,你家要有钱,你二哥还用娶个寡妇啊;是啊,可怕的寡妇,一进门就是四口,如果再生,我的天啊。你看红艳多好,人水灵灵的,还有那双眼睛,眨起来就和打闪一样,特精神,我就喜欢这样的女人;那你姐呢,她愿意嫁过来吗;她——早想嫁人了,她早就说,只要是个男人就嫁,她一天都不想待在我们家伺候一群饿狼了。你知道吗,她说她不怕吃苦受累,最怕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样子,一个个来者不拒狼吞虎咽的样子,每次她都用厌恶的眼神看着大家,即便这样,我妈还要让她学绱鞋纳底,负责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她坚决反对,我妈把针扎进她大腿里她都犟着不从,她可能知道自己一旦上手会意味着什么,因此她早想嫁了,觉得自己只要嫁出去,就是跳出了火坑。可是我妈有言在先——不行,除非她可以给家里换一个媳妇回来。眼见最着急的就是我二哥了。白刺毛哗的一下掀开红四毛的被子,冲红四毛说,你把话说清楚点儿,你让红艳进你们家,是嫁你,还是嫁你二哥。红四毛就结巴了,他说,嫁谁咱再商量,总之眼前我二哥的事着急,咱们得先把这茬儿事处理好,往后就顺溜了。因此,他们最后商量的方案是,必须先把红四毛二哥娶寡妇的事给搅黄了,哪怕让红艳给当个幌子,等容出时间来再说。
我问红四毛干吗要和我说这些。他说,你别问,听就是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时他的头发还是原来的样子,红黄红黄的,软软地贴在脑袋上,有几次因为长都掉进碗里了,他不得不像女孩子那样伸手捋一下或向后猛地一甩。我还和他说,头发该理理了啊。他说,是该了。接着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和白刺毛还聊了关于人生、命运、前途的大事,他没想到白刺毛竟然和他的观念完全一致,他们做出决定,从那天起他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他们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们一起回顾了以往的人生,展望了未来的前程,彼此发现可以在一个道上走的人只有对方。你们具体谈论了什么事?我问他。他说,谈了很多,什么都谈,但又好像什么都没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包括娶妻生子之类的事,各自的家庭是指望不上了,想到这里,最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叹——你说咱俩来这个世界干什么呀!但感叹之后,他们又同时想,必须行动了,得想办法挣钱,因为没钱,谈什么都没用。看来你是有想法了。我说。他抬头看我一眼,笑了笑,啥也没说。
我俩吃完面,红四毛把嘴一抹去结账。我说,不是说好我请的嘛。他说,本该是你请,可我突然想,你家条件好有钱,不是你的错,现在你还在上学,我好歹已经在社会上混了,不能让你请。我就有点儿纳闷,问他,那你来找我干什么。他说,我还真不知道,你这人咋这么有意思,这人活一世啥都知道了,也就没意思了吧。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不行吗。说着,他揪起衣领让我闻,你闻闻,闻闻,也是一股好闻的味道吧,以前我往你跟前一走,你就躲,你说嫌我说话刌,快算了哇,我还不知道?你是嫌我臭。说完,他就走了。我突然发现他那天从头到脚穿了一身让人窒息的新衣服,白底咖色细条纹格衬衣,一条浅蓝色喇叭牛仔裤,脚上是尖头漆皮黑皮鞋。我说,鸟枪换炮啊。什么鸟枪换炮,是脱胎换骨。在饭店门口炙热的阳光下,红四毛油皮地回答我。我还对他说,看来你是挣钱了。已经走出几步的他,回过头来,迎着刺目的阳光对我说,还没有,不过已经是在挣钱的路上了。
我们就此分手。一个星期后,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红四毛和白刺毛杀人了,被害者竟然是县公安局局长的儿子。
律师认为这起凶杀案属于故意杀人。因为作为共同犯罪主体的红四毛和白刺毛的作案动机成立,他们需要钱,他们为了掩饰体貌特征一起去染了发,出事时他们口袋里装有工矿里做电缆头为区别相位而用的塑料带,证据确凿,而且他们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可是审判结束,红四毛却扬言,那是一次意外。奇怪的是,他又不提出上诉。这起杀人案在我看来就有了许多扑朔迷离之处。
人们都说,出事那天,红四毛和白刺毛确实是商量好的,他们要去县城染发。染发前他们没有想过杀人,谁不知道一旦杀人会是什么结果,所以在他们的脑海中连杀鸡的念头都没有产生过。他们去县城染发,无非两个原因,杨红艳在理发店,多少能便宜点儿;再者,在那个普通人很少染发的地方,尤其他们是两个有特色的人,染发不是件小事,毕竟在这方面杨红艳专业,他们想听听她的意见。如果再往深里说,那就是红四毛想让杨红艳那双柔软的手摸他的头,他决定不用等红艳学会理发就将自己的脑袋交给她了。
当然,那也是他们一夜深刻讨论的重大成果。出发前,人们看到他俩一起走进村北头的寺庙,一座早已破败人们却念念于心的关帝庙,庙里关老爷神像的头早已不知去向,威武的身体也住进了两窝麻雀,神像前的石头祭台倒还在,不过厚厚一层尘土已经成了鼠雀描绘生活的画板。人们相信他们一定虔诚地双双下跪。人们猜不出他们祈求关老爷保佑他们什么,但知道他们和自己一样相信无形的神灵无处不在,否则这两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也不会大拜到如此五体投地,以至于他们并肩走出庙门时,裤子、衣服前胸、脸、鼻尖、额头、头发上到处是灰。人们看到了他们洒脱、昂扬、毅然决然的气度,就像怀揣使命的武士走向战场,用他们的话说,这是“毛毛”兄弟本就有的风度。他们从人们面前经过,有长嘴的人还问他们:“喂,二位,你们这是——”
“去县城。”
“有营生了?”
“去染个发。”
“去染个发,还这么——”
他们猜不出对方想说的是“神气活现”还是“兴师动众”,总之不听了,不想听了,有这个家伙到处嚷嚷,人们很快就会知道他们去县城染发了。然后等到第二天天亮,人们将会看到两个和大家一模一样却又是全新的年轻人,红四毛和白刺毛的头发变得乌黑了。不过,他们所到之处,红四毛说,咱们得给他们立个规矩,谁要再敢叫咱们“毛毛兄弟”,就先扁然后撕烂他的嘴。
他们出村,步行十里到镇上才能坐上公共汽车。这在当时的农村非常正常,但对红四毛和白刺毛来说却非常异常,毕竟那时他们早已经声名远播了。只不过人们对他们的这种声名怀有一种复杂甚至是矛盾的看法,因为无法对他们给出一个统一的评价。这么说吧,不论熟悉,还是陌生,红四毛和白刺毛在那条川里,总是尊老爱友,和穷苦人说话和和气气,甚至会掏腰包施善,可是对同龄人,他们就态度大变,尤其遇上那些动不动就显摆自己还想耍横的人,他们就绝不会手下留情。最出名的一次是,他们在公路上拦住一辆货车,司机摇下车窗看他们,话还没说人就先笑了,问他们为啥要染这么个颜色的头发。他们说,少废话,你要去哪,如果顺路就捎我们一程。那个货车司机问了他们去哪,眼睛却往天上一瞟,说,路是顺路,可是不能捎,因为他们身上太臭了,怕熏坏了他车上的蘑菇。红四毛就笑,他和白刺毛确实臭,大夏天的,又刚挑了一上午的茅粪,他们很客气地上前,突然跳上车,说是要借车上的观后镜照照自己,结果在他们脚踩踏板的同时,就把车门拉开了,他们一前一后钻进了驾驶室。据说,红四毛用自己脚上的板儿鞋一路扇着司机的脸扇到了县城。后来很多次白刺毛争辩说真正用板儿鞋扇司机脸的人是他,红四毛一路上负责讲道理,他们有约在先,红四毛文,白刺毛武,可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对兄弟——“毛毛兄弟”,在那一带,“毛毛”本来是指路边的毛毛野草,也就是狗尾巴草的意思,最贱的东西,但因为他们——人们说,到了县城后,红四毛和白刺毛并没有下车,他们嘻嘻着和货车司机说,你拉这一车的蘑菇真是有钱人啊,可我们兄弟俩长这么大还不知道蘑菇是什么味道呢。货车司机二话没说,就送了他们一大袋。不过他们一下车,就把那袋蘑菇送给路边摆摊的大娘了,还有人说,他们不仅拎了人家一袋蘑菇,下车时还掰断了货车司机的一根手指,为的是让货车司机长点记性,别以为自己有辆货车,就狗眼看人低。但红四毛和白刺毛坚持强调说,这都是旁人杜撰的,他俩再赖,也不能赖到那种程度吧。不过在那条川里,“毛毛兄弟”却是大名鼎鼎的,最直接的证据是,他俩去县城从来不花钱,只要他们往公路边一站,过往的车辆,尤其是经常在这条路上跑的车就会停下,甚至到后来曾经教过他们的老师也打起了他们的旗号,站在公路边向货车摆手,告诉货车司机他曾经在小学或初中时给红四毛和白刺毛代过课。可当这位老师回到学校后,他一旦站上讲台,就又教育在座的学生不要以红四毛和白刺毛为榜样,因为他们是痞子,是无赖。
但是,这天不比往常,染发是件异常隆重的事,他们要求自己亲自走到镇上花钱买票坐公共汽车去县城。也正是红四毛和白刺毛坐着公共汽车去往县城,两人严肃地,纠结着,一再,反复地窃窃私语,问对方也是问自己,真要把头发染了吗的时候,在县城理发店的杨红艳早有预感一样,店门一开,抹净了柜台,整理了器具,拿起了一把电动推子,她将它举到眼前,打开电门,嗡嗡如蜂的声音让她在心潮澎湃中看到未来。在她的想象里,她将来的理发店就开在自己家,院门外竖起高高的幡旗,上面就印鲜红的四个字——红艳理发。她相信从幡旗立起的当天起,整条川的男人就会陆续来理发,近的步行,远的骑自行车和摩托车,所有的顾客青一色是男人,女人就是挤在摩托车后面跟来她也不接待,男人的钱好挣,她会给男人找来理发的理由,价格要比县城里理发贵一点点儿,可是要比县城的理发价加上公共汽车票价再便宜一块,他们会来的,到时再买一台录音机,播放邓丽君的歌。无论那些男人的女人在旁边怎么要求给自己男人的头发理短点儿,她都会故意给他们留长点儿,她懂他们的心事,他们想多来她这里几次,因为红四毛说过,整条川里,不要说男人,就是女人,只要她的一双柔软的手往脑袋上一放,他们的魂就飞了。那样她抽屉里的钱就呼呼增多,她会用那些钱帮大哥娶亲的,一旦大哥娶亲自己就可以解放了,母亲说过的,家里就她这么一个姑娘,在大哥娶到女人之前,她的婚事是不准提的。母亲没有明着说换亲,但意思不是明摆着的嘛,可是这能怪母亲吗,能怪大哥吗,换换角色,自己也得那么干,谁让自己的父亲死得早,家里又那么穷呢!
没一会儿,红四毛和白刺毛就从杨红艳面前的镜子里走进理发店了。两人并排坐在一条长凳上,红四毛还是习惯性地向后甩头发,和杨红艳还没说几句话,老板娘就来了。老板娘问红四毛和白刺毛:“理发?”
“我们等等红艳再说。”红四毛说。
“她又不负责理发。”老板娘说。
“是我哥,他们从老家刚来。”
“两个都是?”老板娘满脸狐疑。
“都是。”红艳说。
哦——老板娘拉上帘子去换衣服了。
红四毛看看白刺毛。白刺毛看一眼红艳,兄妹俩一起出了理发店,再回来时,红艳一脸笑容,满眼欣喜地看红四毛,说:“不能吧!真的?好事啊!这可是——看来以前我真看错你了,你这人还有救啊。你让我想想,今天这是什么日子啊?”
“他的生日。”白刺毛不喜欢红艳一惊一乍故作夸张的表情。
“不能吧!真是?”红艳比刚才更夸张了,她学以前红四毛的样子,头往后仰,大张开嘴,只不过没有发出爽朗的笑声,而是把脸凑到红四毛跟前,压低声音,“那我们庆祝一下,你俩先去转悠转悠,简单吃点儿,晌午时就赶快回来,然后我请假,下午我请你们看电影,好好庆祝一下。”
在大街上贴出布告,已经要枪决的前十几天,我和红四毛的父亲、他二哥以及红艳去看红四毛(我至今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看一个将死的杀人犯)。红艳告诉我,红四毛和白刺毛从她工作的理发店出来后不知道该去哪里,他们蹲在十字路口的转盘处看了一会儿熙熙攘攘的车流,又到街口看了一会儿老头们下象棋,然后靠着电线杆猜了好一阵眼前经过的女人裙子里内衣的颜色,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他们竟然是一对闲来无事的无业游民,所有人都在忙,可是他们马上就二十了,忽然间发现自己的人生一片空白。这时,一个剃着光头、胳膊上有刺青的男人从他们面前经过,最抢眼的是那家伙脖子上竟然戴着一条比筷子还要粗的金链子,红四毛看着人家,目不转睛地看,白刺毛当然注意到了,他推一把红四毛,怎样——要不,咱们——啊,我从后面猛砸他的头,你过去拽上他那条链子就跑,他来不及反应的,就等他反应过来你往人群里一跑,他也认不出了。红四毛说,这个人我好像见过——对,我想起来了,他以前是个养路工,听说借钱买了辆大车跑运输,发了。白刺毛用肩膀靠一下红四毛,你想什么呢?你,还有我,咱去哪借钱?红四毛就说,咱们这不是最重要的一天嘛,今天咱们把头发染了,就算上正道了,就按你说的,咱俩去下窑,以现在咱俩的情况,最适合下窑。白刺毛说,下窑是比干其他的挣钱多,可是下窑也危险啊,不是瓦斯爆炸、透水,就是塌方。红四毛当然知道这些,他说,要怕死,那人就别活了,要说死人,怎么也会死,一口凉水咽不对也死人,这事咱们说好的,你不能反悔,到时候咱们分一个班,万一我死了你得负责拖我。白刺毛说,你听你放的什么屁,咱们一个班,要死,我也死了,咱俩谁拖谁!红艳长叹一声,唉,你说这俩圪节货,好端端的去染什么发。我说,红四毛中午去看我了,正好是星期天,我没课,我们一起吃了饭。红艳说,我知道,我知道,红四毛都跟我说了,其实我知道他羡慕你,那天他穿的衣服是他长那么大穿过的最好的衣服,然后就烧躁地去看你了。
人们是这么描述那天后来的事情的。
红四毛和白刺毛在街上转得实在没意思了,便决定进商场。他们进商场不看衣服,只看女人,以他们的认知,认为好看的女人除了在电影里,就是在商场里。他们确实看到不少,细皮嫩肉的,身段窈窕的,眼睛漂亮的,嘴唇殷红的,头发大波浪的,身挎细带小皮包的,脚穿高跟凉鞋的,他们倚在柜台上看,尾随在人家身后看,被看的女人因此警觉,不是把他们当流氓,就是把他们当小偷。但他们看到的却是,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冲他们翻白眼,红四毛和白刺毛两人有着共同的感受——狗眼看人低,尽管他们没有说出来,但已经在心里冲整个世界大喊了。后来,红四毛站到商场门口,大大地张开嘴,每过去一个女人他就甩上一下头,然后说:“我吃了你。”和个神经病一样,白刺毛笑,从后面用膝盖顶红四毛,说,也别怪人家,人是衣服,马是鞍,咱们身上要穿一水新的衣服,你看她们哪个还会那样看咱。那时红四毛脑袋一甩一甩的心里数着数,已经吃掉五十三个女人了。他马上抿住嘴,示意白刺毛凑上来。他问白刺毛身上有多少钱。白刺毛说是有一些,出门时他妈让他带给红艳的,红艳在理发店学徒,虽然不用交学费,但没有工资,房租和早晚的饭费也得自己解决。红四毛说,把钱给我。白刺毛问,你几个意思啊。红四毛说,下个星期咱们不是就去参加招工了嘛,我总得有身像样的行头。白刺毛不乐意地说,我还没有像样儿的呢。红四毛就说,把钱掏出来,算我借,等第一个月开了工资就还,再说,你要去招工,你哥,你妈会管,我没有人管,就是死在外头也没人管,还有,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吗,就算——没等红四毛说完,白刺毛就把钱掏出来了,但红四毛等晌午见了红艳得给她一个解释。两个人返回商场,红四毛置了一身行头,立刻鸟枪换炮。红四毛站在镜子前,除了一头的红(黄)发,真都认不出自己了,他嘿嘿笑,就对白刺毛说,你想想,等红艳给咱把头发染了,那我才真认不出自己了呢。来来来,你也换一身吧!白刺毛也想换,可是钱不够了。
两人从商场里出来,时间还早,可他们不想再转悠了,他们商量要不先去吃饭,可是吃了饭也不到晌午,那就到西瓜摊上吃几块西瓜吧,两人又觉得没这个必要,也有点儿破费,因为中午吃饭时无论吃什么,和店主要一碗面汤就解决问题了。总之两人还得在街上乱转,他们从大商场转到集贸市场,从集贸市场又转到电气维修一条街,那条街人少,店铺不多,也冷清,但哪个店铺门前都堆一堆破铜烂铁,阳光烈烈地照着,熏蒸着地上废旧机油的味道,红四毛特别喜欢那种味道,相比于自己有生以来总也摆脱不掉的猪粪羊尿的臊臭,他觉得这种代表着工业的味道很令人向往,他走进其中一家,看着几台把肚肚肠肠掏在外面的电机,还有几根亮到可以照人的传动轴,他就想如果自己要有一辆汽车,说不定也来这个地方修理,然后他看到后面货架上各种各样叫他神往的货品,他突然叫来店主,说自己要三盘塑料带,红、黄、绿各要一盘(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这东西做什么用)。白刺毛跟进来问他,买这东西干吗。红四毛就笑,你这个人啊,难怪你年纪轻轻就老成这样(指白刺毛的白发),活得一点儿创意都没有。他把塑料带装进口袋,跟白刺毛说,你家的衣架是铁丝窝的吧,你家还有两把钢筋焊的椅子,你想想,用这东西缠了,一纹一纹的,颜色鲜艳,还防锈,那得多好看。白刺毛第一次发现红四毛原来还是这么细心的一个人。
时间还是过得那么漫长,似乎能代表时间的一切都像脚上粘了胶一样。白刺毛跟红四毛说,咱还是回理发店吧,中午把红艳叫出来咱们一块吃。红四毛伸手拍了白刺毛脑门儿,说,你长点儿脑子好不好,红艳要能和咱们一起出来她会不出来?她那么安排一定有她的道理,她为什么叫咱们晌午回去,还不是上午她要好好表现下午她好请假?她叫咱们晌午回去,还不是——哦,那时她兴许有空,兴许趁老板娘不在,她就可以偷偷免费给咱们染发。但他们实在逛得不耐烦了,无聊到恨不得去帮旁边的清洁工打扫卫生。这时红四毛想想,跟白刺毛说,这样吧,你回理发店去,那里有电扇,凉快,我去一中看个人。那中午饭呢?白刺毛问。咱们各顾各,吃完后让红艳先给你染,我卡着点,保证在轮到我时准时到场。红四毛说。白刺毛应该没有猜到红四毛去一中是去看我,因为我平时和他们不搭边,再说就算猜到,他也不会去,红四毛一水新的行头,而他还是——他丢不起那个人。
因此,后来很多人问我那天中午红四毛见我到底说了啥。我说什么也没说。他们不信,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回答到后来,连我都问自己,红四毛在那天中午真的什么都没和我说吗?可是他真的什么都没说。这也符合常理,如果他没有想杀人,他怎么能和我说到杀人的事呢,如果按照律师所言,他已经蓄谋好要杀人,难道他会把这天大的秘密告诉我吗?但有一点可能是红四毛的真实意图,那就是他要改变我对他的印象,他想让我知道,他也有光彩照人的时候。
当时我还小,或者说作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旁人,我没有理由去和律师探讨具体的实情细节,但在人们口中普遍流传的说法是,所有犯罪事实红四毛和白刺毛都是签字画押认可的。否则的话,在枪决那天红四毛也不会是那副表情。
……未完
本文载于《芒种》2022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