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的景观》:以青春为燃料烧出“未定型的景观”

望道讨论小组由金理召集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方向研究生、本科生参与讨论,立足前沿现场、关注当下作品、传递年轻声音。自2016年4月起,每次讨论的整理稿均由望道讨论小组的微信公号“批评工坊”推送、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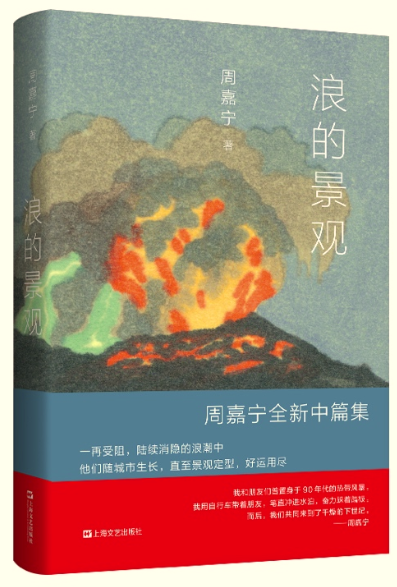
《浪的景观》 作者:周嘉宁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金理、孙辰玥、周乐天、谢诗豪、李琦、曹禹杰、汪芦川、欧阳可欣8人正在讨论中
情绪是这部小说集的核心
金 理:周嘉宁小说集《浪的景观》一共收录三部中篇,按照发表顺序,不妨从《再见日食》谈起。这篇和后面两篇《浪的景观》《明日派对》相比,风格似乎有些差异:前者尖锐充满紧张感,后两者就有舒缓的笔调。周嘉宁当年赴美参加写作营的经历参与到了《再见日食》的创作中。我会联想起王安忆在爱荷华遇到了陈映真,可能对于作家而言,这往往是具有“决定意味的时刻”。
孙辰玥:周嘉宁所理解的爱荷华和虚构的佩奥尼亚间的指涉关系一定是复杂的,当她对这个跨国界的“空间”进行了一番有意味的梳理和创造之后,我觉得文本中的紧张感未必指向崩裂,也有可能是要冲击出一个记忆的“出口”。泉在告别前曾对拓说“想象你就是我,一个更为正常的我”,两人都是通过对方来感知并想象自我,然而“对方”常常是以一种既脆弱裸露而又回避触碰的状态出现的,因而彼此只能感受到自己如何在痛苦中消耗能量,但那些创伤却依然还没得到纾解和愈合。所以,我在读小说结尾的时候就不禁想到,当拓得知了泉此前和此后的故事后,说“无论泉在世界的哪一部分再次出现,都代表着那里可能存在的出口”,是不是意味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拓对于泉,对于这些青年在佩奥尼亚看似开放中的“封闭”,对于他们未完成的相互理解,会做出一些新的尝试。
周乐天:我觉得《再见日食》里拓和泉这两个主要人物过于浮光掠影了。拓简直有些像在指涉川端康成之类的人物了。当然不是说不能写这样级别的作家形象,甚至也可以说作者是在讽刺拓,抑或是讽刺时人对文学作品的判断能力。但不管怎么样,拓在小说中的总体形象还是更像一个感伤的文艺青年而非作家,我看不出他身上本应具备的、与作家身份相符合的思辨能力。如果说对拓的人物塑造过于温吞,那么泉的形象则是过于尖刻且单薄了。作为一个没有真正登场、凭着朋友记忆出现的人物,或许这种单薄还较为说得通一些。
金 理:对《再见日食》的意见分歧,也说明这部作品的难度。天才少女是个太过尖锐的人物,仿佛锥处囊中,锋利的尖刃一定会刺破口袋。同时泉和所关联的历史风暴之间的关系又非常迫近。“作为历史的人质”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人与时代的关系,这两点叠加起来,就不会给作家的闪转腾挪的艺术空间留下多少余地。由此来看,我倒能理解拓的“过于温吞”,需要一个性格不那么鲜明、行为不那么主动、和时代的关系不那么直接的人物作为泉的对镜。拓离开日本时与朋友绝交,在后者看来,当创伤性事件发生过后,青年人不应该撤离历史现场。拓的选择可能会接近作家的态度,人在面对时代时可以松弛一些,不那么直截。但是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大家怎么看待周嘉宁反复提及的申奥成功那个晚上(这不仅是作家自述中青年时代的开始,也是这批作品诞生的原动力之一),国家赢了,青年们无比欢乐,这种同频共振好像又回到个体和时代之间更为直线、单一的关系。
谢诗豪:情绪才是这部小说集的核心。三篇小说中反复出现类似“世界中的世界”的表达。这不是偶然,那些“世界”都指向一种内心感受,比如拓和泉一起停在湖心,感觉自己身处一个世界中最小的世界,“没有其他人可以抵达”。这个“最小的世界”在现实中当然不存在,但它对拓而言却无比真实。再如作为电台主持的张宙,对“我”和王鹿而言活在电波里,却可能比现实中的人更“真实”。这或也突出了小说的真实观,即一种以情感为依托,以可能性为基础,以“信”为要义的真实。
以情绪为中心的写法在《浪的景观》和《明日派对》上是成功的,这两篇小说的人物背景都很轻,读者隐约知道一点“我”和群青的家庭背景,对王鹿、潇潇的过去了解得更少,但这不影响我们理解他们,进而体会小说想要传递的情绪,有时我甚至觉得周嘉宁是有意地不去“描写”,担心过多的细节会“伤害”情绪。但在《再见日食》中遇到了一点困难,就像金理老师所说,历史的风暴太强,人和风暴的关系太紧,像在一段轻盈的乐章中突然出现一个重音,很难让人视而不见。
李 琦:再回应一下个人感受和时代氛围的问题。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对小说人物和亲身经历这一事件的周嘉宁来说,可能是一种很朦胧的氛围,为当时那种集体性的喜悦所震慑。这和她从日食这种自然现象中感觉到的差不多,为之感动的是那一时刻“共振的心灵和情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温柔”。有意味的是,这一事件或者说这个夜晚被周嘉宁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个人意义。她曾谈到,这个夜晚是她人生的开始。之前是懵懵懂懂的少年,对世界也没有什么认识,18岁第一次出门远行,就遭遇了这样一个充满了喜悦和友善的梦一样的世界。这个夜晚最终凝结为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标识,代表着她对世界的最初感知,成为她人生中某种底色性质的存在。而这种天真乐观的底色却似乎随着主体的成长,逐渐成为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周嘉宁曾对这种矛盾有很概括的表达。她说,因为她的人生底色那么乐观明亮,所以她后来经常会怀疑,这种明亮的底色是不是导致她在后来很长的时间内,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存在一种偏差。当时的快乐是幻觉吗?如果当时的快乐是真实的,那么现在的痛苦又从何而来呢?所以我觉得,周嘉宁的这些小说其实是以个人的、细腻的方式呈现了很大的命题:近30年时代的这种曲折走向,给一代人,至少是一代人中的一部分人造成了一种前后矛盾的生命体验。面对这种矛盾和断裂,他们非常困惑,难以将其解释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周嘉宁小说中那些犹疑滞涩欲言又止的部分,正是这种困惑和困难的表现,她和她笔下的主人公都在经历一种“祛魅”的痛苦。
看见更为辽阔的“青春”
曹禹杰:我们似乎确实能够在周嘉宁的小说中指认一个又一个时刻:911、申奥、非典等等。问题在于,周嘉宁真的是要去铭刻这些事件以及它们带来的政经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转折吗?我觉得周嘉宁的态度可能更复杂。《浪的景观》里群青和“我”有一段对话,从中可见群青的态度颇堪玩味,他身上有一种高度的自觉清醒与天然的洒脱不羁,他不曾想过要把眼下的一切凝结为纪念碑,真正让他如痴如醉的,恰恰是在尚未掘通的隧道中冒险的过程。在那一刻,无限的可能性在青年人的面前徐徐铺开,而当种种可能性最终收束为一个固定的出口时,他又能无比洒脱地将这一切弃之身后,继续迈向前方。我觉得这是周嘉宁写作中难能可贵的一点,也是她为当代文学史中的青年谱系做出的贡献。
汪芦川:对于周嘉宁这一批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80后”作家来说,“青春”是无法绕开的主题。《风姿花传》中曾经提到,一个能乐演员如果到了50岁,之前20岁、30岁、40岁的技艺都还“保存在自己的现艺之中”没有消失,如果这时候再表演20岁,那就是一种复合形态的、人生经验累加以后的20岁姿态。周嘉宁曾借用这个例子来谈自己的小说写作,认为这是小说技艺有趣的地方,因为那是复合形态经验的虚构投射,而不是青春本身。但从审美来说,她承认喜欢的人或者世界,确实多少都有些少年心境的投影。对于具有少年感的生命状态,周嘉宁似乎有一种持久的审美倾向。在周嘉宁的作品里,我们能看见青春的实体,而更多的时候,是青春的倒影,一种有历史意味、意涵变得更为辽阔的“青春”。
欧阳可欣:如果回到全书的标题,回到“景观”这个核心意象本身,会发现周嘉宁所有故事的书写都不妨作为一种典型的、具有“现代性”观看方式的产物:超越特定的时空,以明确的“历史的后见之明”进行重构或解构。周嘉宁在小说中不断表现出的在“说破”与“不说破”之间的摇摆,实际可以认为是对于青年时代懵懂拥有的一切不成熟的想象和激情的确认与保留。身处历史之中,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此时此地的情感与行动在20年之后会激起怎样的波澜,但只要所有这些确实地生成于、黏附于个体,成为个体生命中真实存在过的经验,那么它们就不应当被轻易否定。
周嘉宁在小说中通过还原一种“叠合性”的真实,将中年人的质疑、怀旧、因循、暮气和年轻人的浪漫、肆意、反叛融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那些可以被轻松辨认出的属于“80后”作者的反思,还是尚且年轻的一代所表达的否定和怀疑,都可视作对具有真实性的历史事实的尊重、确认、妥善保存。《明日派对》结尾写到三个人在苏州河上违规划船,“我们奋力将小艇划向岸边”,让我一下想到《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于是我们逆水行舟,奋力向前,被不断地向后推,直至回到往昔岁月”。当然菲茨杰拉德是毫不保留地在悼亡一个逝去的好时代,周嘉宁显然不认为过去必然是美好的,她看到这一怀旧浪潮中有意无意的自我美化,但这并不妨碍每个个体重视、重拾旧时光中所发生与没有发生的种种。周嘉宁写到此处时当然未必想到盖茨比,但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他们的的确确在对过去年代,尤其是要以青春为燃料才能烧出的景观的态度上达成了某种共识。
李 琦:很赞同可欣的看法。似乎对周嘉宁来说,如实地呈现这种张力、分裂,比选择一个明晰的正确的立场更加重要。这一点正是她的诚恳和她的写作的独特性所在。《浪的景观》中写到的那个挖到一半的跨江隧道,即一种“未定型的景观”。未定型的意思就是最后的结局还没有呈现出来,还充满了未知的可能性。它虽然最终一定会有一个结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结局就是未定型时期的唯一结局,只不过历史选择了其中一种,后来的人就会理所当然地觉得这一种就是历史的必然,然后站在这个终点一路追溯上去,去解释和批判那个起点。但其实结果和开端之间并不具有一以贯之的唯一的因果线索,而是有着深广的沟壑。对终点的否定并不意味着要连同那个起点也一并否定,在终点处所感受到的痛苦并不能完全解构掉在起点处所感觉到的快乐。在这个意义上,这两篇小说不是单纯的对逝去的黄金时代和青春岁月的怀念,而是在呈现一种被压抑的可能性,一种被压抑的能量。
周嘉宁由此对那个问题——面对今天的痛苦,昨天的快乐是幻觉吗?——做出了一个阶段性的回答,这个回答就是:她虽然在持续地成长和反思,看到世界更多的面向,但她认为年少时所感知到的那种振奋和快乐,那种向上的气流非但不是一种幻觉,还是一份给当下的自己以支撑的珍贵的精神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