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勇:我个人阅读偏好在本次入围作品中得到了盛宴般的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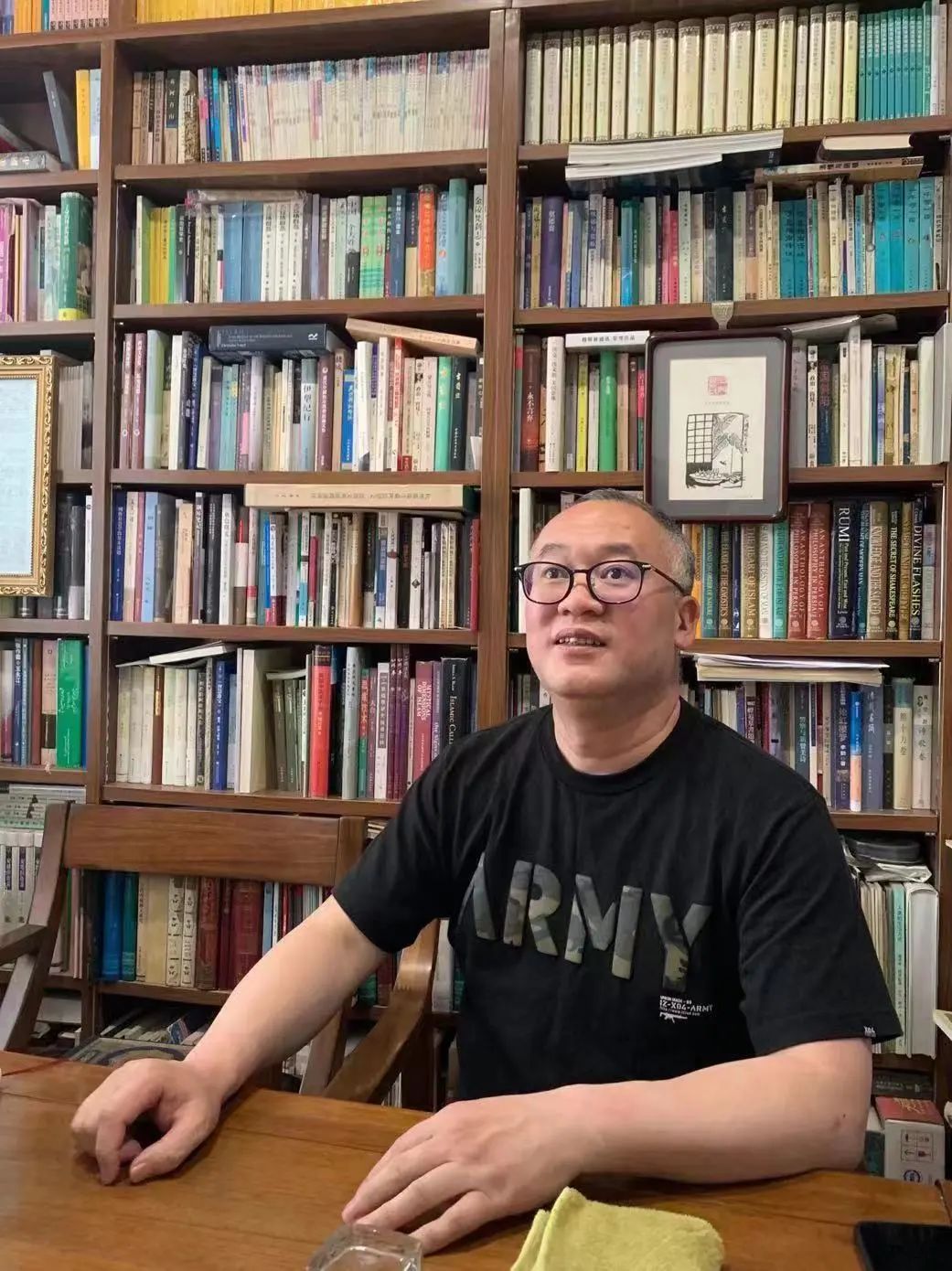
曹元勇
出版人和文学译者。策划并编辑出版过草婴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作品全编,以及实力派作家张承志的文集和阿来、格非、马原、残雪等作家的作品系列。著有评论随笔集《聚焦与印象》《美人鱼的眼神》;译有《海浪》《马尔特手记》《已知的世界》《老无所依》《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等作品。
Q1 大益文学作为一个民间纯文学机构,在2020年已经成功颁出第一届“大益文学双年奖”(线上),您是本届评委之一,如何看待“大益文学双年奖”,它具有什么特殊意义?
大益文学和“大益文学双年奖”有自己始终如一的文学坚守,它对文学的纯粹性和先锋性的追求与执着,特别令人敬重。尤其是在许多人文领域,包括文学、包括哲学,个性和创新日益变得模糊、日益被机械复制所深度裹挟的今天,大益文学及其双年奖对文学理想的坚守,意义非凡、难能可贵,对新时代文学的探索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感召。当然,“大益文学双年奖”包括这一届在内才办了两届,还是众多文学奖项中的一名新兵,希望这个奖能够持之以恒地办下去。
Q2 第二届“大益文学双年奖”共有十部入围作品,您对于本届整体入围作家的水平有什么评价?
总体而言,入围本届双年奖的作家作品,个性和特点都比较突出,体现了文学创作丰富的可能性。入围的每位作者,写作方式和风格均称得上是独树一帜,有的想象力奇崛飞扬,有的写实功夫细腻入微,有的叙述语言自带温度,有的哲思本身既具有超越时代的深度、又具有诗意感性的饱满,等等。
Q3 此次入围的作家们,横跨老、中、青三代作家,国籍有中国、斯洛伐克、智利,您对本届“大益文学双年奖”作家的年龄和国籍分布怎么看?
对于入围作家们的年龄,我在审读过程中倒是没有特别在意,因为幻想的和写实的两种风格在老中青三代作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如果一定要做个比较,那么从作品内容看,年长一些的作家的作品所承载的生活经验要更加厚实、更加丰富、更加饱满,而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则以令人惊奇的想象和幻想见长吧。
至于作家们的国籍,除了多数是中国国籍,这一届入围的有智利的一位,斯洛伐克的一位,还有旅居西班牙、用汉语写作的一位。这说明面向未来的大益文学奖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在世界文学交流既方便又彼此快速影响的二十一世纪,文学本身的视野和眼界自然需要放得越宽越好。不过,这次入围智利和斯洛伐克两位作家的作品,我个人感觉要比其他几位本土作家的作品逊色一些。
Q4 在评选过程中,您认为最重要的评分要素是什么?为什么?
语言的准确性,想象的力度及其与时代和现实的关系,写作方式的挑战性或者说开拓性,还有细节丰富性与合理性,我感觉这些都是决定一部作品是否优秀,以及这部作品优秀到什么程度的要素。如果一部作品的故事和细节虽然想象力非凡,但过于离奇、失真的话,就会损害作品的整体品质,损伤它的力量。如果一部作品的细节显得单薄,或是写作方式比较陈旧的话,也会影响作品的分量及其在艺术上的贡献。
Q5 此次入围的十部作品,哪些作品让您印象深刻?它们最感动您的理由是什么?
这次入围的好多作品都给我留下非常好的阅读感受。比如入围的三部散文,耿占春先生的《爱,人类最小的共同体》无论是文体还是思想容量,在本土当代哲学写作和文学写作中均可谓独树一帜、独一无二;旅居西班牙的女作家赵彦的《我的西班牙人物辞典》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独在他乡的生活质感和心灵的温度;而诗人陈东东的忆旧散文《中南新邨》则透过对童年生活细节的绵密追忆,写出了记忆的确定和不确定。再如入围的几部小说,严前海的《前往苏北的告别》写得人物饱满、情节丰富、叙事技巧娴熟、时代背景复杂,整体上显得比较厚重;杨帆的《欢乐宾馆》则通过卓越的想象深入勘探了主人公的内心奥秘,有些部分的描写还颇具一定的狂欢色彩;而最年轻的作者迂夫子的《赋新词》的想象力则堪称奇崛,等等。
Q6 在评选本届“大益文学双年奖”最终奖项得主的过程中,对您来说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应该还是打分吧。比如三篇散文作品,我都想给最高分,但按照评委会要求,打分的时候又必须打出不同的分数,确实很难取舍啊。
Q7 您平时会对哪些小说话题感兴趣?您会喜欢具有怎样特质的文学作品?它们会影响到您此次的评分吗?
虽然进入新世纪以来,作家们似乎对写什么的重视又超过了对怎么写的重视,但我想真的能够引发我们关注的小说话题、文学话题,还是离不开写作的方式、写作的内容,离不开作品与时代的深层关系,等等。我个人比较喜欢能够超越现实表象、深入到一个时代的精神内部的作品,喜欢那种用想象、幻想将历史、现实和新的结构探索相融合的作品。应该说,这种个人偏好在阅读这次入围作品的过程中还是得到了盛宴般的满足。
Q8 您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一位资深文学出版人,在您看来,新生代的文学创作者们有哪些变化?他们体现出的哪些特征是符合当下变化的环境?
谢谢。文学代有人才出。对新生代的文学创作,我个人了解得非常不充分,所以也难以说出什么准确的看法。在我的粗略印象中,新生代的作者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没有“文革”以及“前文革”记忆或经验,许多重要的近现代历史事件,甚至包括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对他们来说也显得很遥远,但他们生活在全球化的大时代,拥有自己不同于前辈们的生活阅历和经验,他们的作品首先表达的是他们这一代的经验,整体来说可能是像其他一些时尚艺术一样,轻逸有余,厚重不足吧。
Q9 作为一个编辑,您怎么看待这个身份对自己写作的影响?
我想,对于一个真正有创造力、有天赋的写作者来说,职业身份并不是他能否写出好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Q10 “大益文学”坚守先锋精神,您怎么理解“先锋”,您对大益文学院的发展和大益文学书系的出版工作有什么建议和期待?
大益文学对文学先锋精神的坚守,大益文学主编陈鹏先生对文学纯粹性和先锋性的执着追求,我想是很多文学写作者都非常钦佩和敬重。我们生活在一个机械复制无孔不入的时代,而真正的文学最需要的还是要有创新、要有叛逆和批判精神。何为“先锋”?先锋精神应该包括实验、怀疑、批判、求新求变。
至于建议和期待,我想说的是:坚持,永不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