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盏2020》:选本的立场、审美与作家的感受力

明湖读书会于2018年4月23日成立,是一个在暨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专业老师指导下由爱好读书写作的学子组成的读书会,成员含本科生、硕士、博士百余人,成员从2019年起曾参与《作品》杂志的“品藻”专栏及“明湖杯”大学生文学评论比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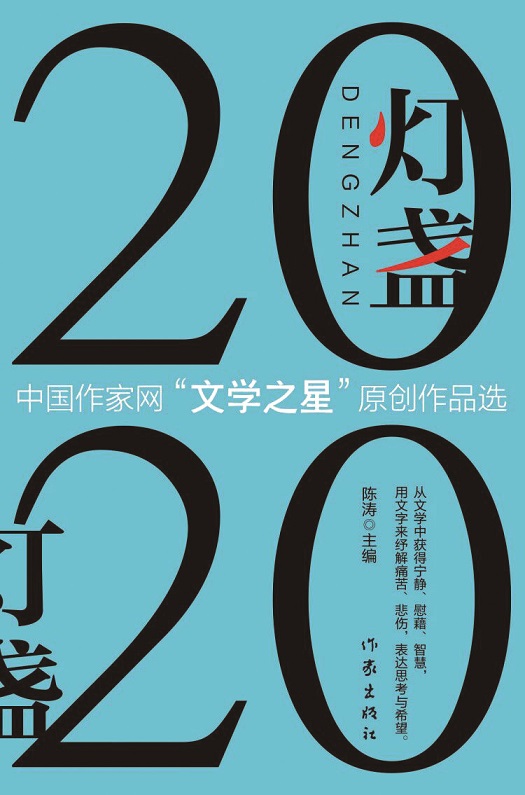
申霞艳:
我们这次共读的是陈涛主编的《灯盏2020:中国作家网“文学之星”原创作品选》,入选此书的是2020年度中国作家网“本周之星”栏目的优秀原创作品,包括散文、诗歌和短篇小说,共计48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历史中有相当漫长的选本传统,选本不仅是作品择优的过程,还会呈现编选者的审美标准。如今文学生产十分繁盛,不仅印刷物数量庞大,网络作品更甚。复制、粘贴、语音输入大大降低了写作难度,这就给阅读挑选带来巨大的困难,所以选刊、年选和排行榜十分盛行。《灯盏》就是对中国作家网原创作品的遴选,从中既可以看到平台和本书主编的立场与审美理想,也能够看到当前活跃在网站的作者们的写作倾向,我非常关心他们提供了哪些新材料、新思想或者新方法、新感受力。随着文化积累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当代人的表达能力普遍增强。虽然不少作品在技法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其中蕴含的新鲜的生活经验和表现力也相当打动人。
提醒大家在阅读时关注媒介对文学的潜移默化,印刷媒介曾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精神生活,移动互联网对当今文学的介入和改变会更大,要关注这种生产、传播方式变更带来的深层影响。中国作家网作为专业的综合性文学网站,我们从他们的遴选中可以看到他们为倡导全民阅读、培育文学新人、维护文学生态的和谐健康等所做的努力。
陈杏彤:
《灯盏》中“故乡”“村庄”“土地”等属于高频字眼,说明作者们对“乡愁”的眷恋,对“青山绿水”的深情。尤其是散文和小说刻画了很多有质感的人物群像:以“哭”为艺术的农村妇女、最后一艘渔船上的老鱼头、无力捕捉兔子的老猎人、老主顾们逐个去世的剃头匠……
《田园杂兴》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有漫长的农业文明传统,诗人范成大将所作的农事诗总集命名为《田园杂兴》,小说借用此名显然是有意为之。主人公开垦出八亩拾边地、侍弄出一片好庄稼,取名为“马丰收”,小说开篇以他的绰号展开,从中可以看到鲁迅、赵树理等写作传统的影响。“丰收”是千百年来农民的希冀,马丰收把土地当作亲人、把耕种当作事业的精神让人十分感慨。随环境迁移而改名换姓的情节设置体现了人物内心的无根感,而最终姓名的确立则暗示了普通民众为了弥补精神空虚所找寻的不同寄托。
“马丰收”这个人物形象特别感人。对于中国亿万农民而言,或许看得见抓得牢的土地更能带来共鸣,这也是基层写作者独特的创作路径。小说结尾,马丰收完成了从“村里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变,但他仍选择每天坐公交回到田间耕作。我不禁思考,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是否可以避免给城乡之间划上清晰的界线,能不能在城市中也留一块“无用”的土地?无论文学命题抑或社会话题,《灯盏2020》透出的光亮虽微小但不孱弱,足以照亮一些幽暗之处。
黄魏越:
《灯盏2020》中的文字是有声的,执笔者用敏锐的听觉捕捉到万物的初生、悸动、流亡。乡野的河流、烛火、虫蝇,世界的万顷寂静,沙漠苍茫落日中的驼铃,《胡笳十八拍》的曲调都被揉进纸间化开。那是一个童真世界,作者以赤子之心正视了其他生命的存在,达到与自然界同频共振的效果。徐春林以文字录下《村庄的声音》,王小勃让万物之灵俯下身去,化作能听见百虫低语的《大地耳》,殷朋超在雪窝深处倾听麦苗和油菜羞答答的心声。童真的语言向我们传递了这些不轻易为人共享的悄悄话,我们亦能有幸闻得草木学舌、悬铃而歌、鸟鸣跌落、长河泣诉。人与自然结为一体,人类小小的身体也变成了辽阔的疆域,熊林清写顽疾的触角在纵横交错的“土地”上探索肉体的世界,一如我们以语言为触角在自然的世界里冒险。与此同时,这种调动了各种感官的语言传递、搭建出的世界又往往是悲凉和辽阔的。村庄活了,裹挟黄沙的风开口了,村庄又死了,驼背上的月亮又沙哑了。时间的流逝没有轻纵任何一个空间,岁月的起承转合令文本世界充满了历史感。也正是在叙述中浓缩的颓败、衰微让纯真和童趣变得更珍贵,让语言富有辩证的哲思。支禄的《河西走廊》里写到了沉浸在月光中的枯骨,菡萏的《岁月长赊》中提及了在春日丧失机能的器官,这些矛盾的意象无不见证生与死的纠缠搏斗,见证生生不息的世界中的死亡。过往的活泼生机、古朴优雅最终被安葬在苍白的纸上,辽阔悲慨的语言是它们的墓志铭,这也许是古老、喑哑的世界最后一次发声。文字中大开大合的起落,纯真与辽阔的交织,让这个空间更泓邃深远。细细读来,不无悲凉感慨。
古格妃:
在现代人的“家园”日渐失落的今天,稳定性、确定性、温暖感变得尤为珍贵,此次阅读对我来说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次次“重返家园”,带来了很丰沛的情感慰藉和思想触动。
“家园”的呈现伴随着对自然、故乡、历史的思考。无论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多以故乡生活、自然风物、历史古迹为主题,这些作品真挚细腻,朴素文字里浸润着对故地、旧景、亲人的深沉感怀,文字中充分发挥着创作者对地域的感受力。埃里克·坎德尔曾说:“经验和记忆成就了我们。”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更为切身的是如何处理“文学与记忆”“自我与记忆”的问题,而故乡的记忆不仅是事件、建筑、地貌,更是个体对具体事物的连绵感应,进而积累成一种深沉持久的感受,将感受诉诸笔端,由此一个地域、村庄、生长其中的万物、生活其间的人有了被看见的可能,正如鲁迅的绍兴、萧红的呼兰河、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灯盏》中的创作者也在书写着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回望故乡是每个人进行自我辨认的需要,也是远行的证明。在《故乡的河流》《村庄的声音》《柴火》《村庄还是村庄》《寂静的深处》《忆乡辞》《那年,我忘了抱它》等作品中,创作者们再次回望故乡的山水草木,在物是人非的泡沫里,打捞不时荡于心间的浓厚乡情。而在《河西走廊》《悠悠水下千年城》《走进燕长城》等作品中,作者们则从贴近的寻常人事中抽离,将眼前景物与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交汇,曾经的历史名地沦落为罕为人知的古老遗迹,在寂寞的岁月中静观文明的盛衰,轻叹历史的深邃苍凉。穿越感性和审美的文学形象去探视故乡、历史、自然这些庞杂而暧昧的存在。在回望的过程中,创作者试图召唤从简朴远古出发的神话,因而给我们带来了别样的审美体验。
曾嵘:
《灯盏2020》辑录的散文风格相当平实流畅和自然生动。《青瓦的村庄》将笔触对准城乡一体化中沦陷的村庄,吹响了对原乡的挽歌;《那年,我忘了抱它》为一棵椿树作传,穿插盖房、搬迁的历史,其中既有对自然事物的体察,也有对时间流逝的感伤;《村庄的树》则写出了桂花树、橙子树、乌桕、枣树的品格和命运。散文用“有情”的眼光写历史中的人,如《哭的艺术》介绍了“哭艺”的形式、特点及变迁,在婚丧嫁娶与风土人情的描摹中,托出一位不善言辞的母亲,衬出人的艰难和隐忍。
而其中收录的诗歌大多克制洗练,通过对季节、植物、动物和小物件的细微观照传达出个体的志向、思绪和情感经验。在《并非所有的路都通向未知》中,作者将结实健康的玉米比作乡亲,把浮沉于人世的自己比作鱼,借异乡的景物表达乡愁:“夜晚水声如蚊,咬破了我的乡愁/让初夏第一次失眠”;《内心的铁》把个体生命和大千世界融为一体,剖析了广博的内心世界;《下午》则使泉水在体内流淌,平和且充满生机:“我只携着岩罅下/涓涓而出的泉流,上路/你会听见,它们在我的骨子里,欢腾地荡漾”。
这些小说都举重若轻地探讨了生命中的严肃话题。《马事》一文以马为叙述者,写出动物与人遭遇的生离死别、劳役和暴力;《春逝》将叙述者和老者的声音编织在一起,不时穿插着卡尔维诺的文本,通过多声部演奏出对衰老、死亡和虚无的思辨;《剃头匠》通过展示剃头匠老周的绝活、豆腐张的手艺来呈现生活的细节,温柔地看待流逝的生命;《大地耳》以儿童视角描绘童年和乡村,带着平淡的忧伤在记忆中钩沉同伴死亡的那天;《单桅船》在较短的叙述时间里,写出了跌宕起伏的时代和恒久的爱情;《田园杂兴》则写出了变迁中的农民对土地的坚守和依恋。
陆王光华:
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或重返家园寻找记忆的故地,或探访名胜古迹触摸历史的脉搏,或驻足于原生态的风光之中重审自然。其中《故乡的河流》《悠悠水下千年城》“乡愁”与“怀古”之音不绝于耳;而《虎跃南涧》通过对当地神秘南涧习俗的探访,边陲的风土人情尽在纸上。在品读诗歌时,得见作者们的诗歌技法探索、语言打磨与诗性之美,比如《内心的铁》《十二月》《并非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未知》情感冷峻、克制,善用隐喻,语言富有力与美,阅读即是在意象环绕、符号层叠的世界中寻觅诗人们的心灵符码,感受简练文字背后的种种博大;而《悬在人间的彩虹》组诗以情感为纽带,关注了庚子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饱含现实关怀。小说卷着重探讨了作者对文学母题的诸种新演绎,比如希望、爱情、童真、乡愁等等。小说卷很能体现创新意识,其中《乌鸦伊塔洛》轻盈、浪漫,赋予了乌鸦别样的象征意味和幻想色彩;而《大地耳》以寓言的方式将万物有灵的景象诠释得十分灵动,捕捉到了孩童灵光消逝的刹那;《剃头匠》关注市井生活的人情味与匠人的内心世界,有汪曾祺的味道;《田园杂兴》以农民与土地缠绕一生的复杂关系展开,主人公被命运“拨弄”的种种情状表达着作者对乡土境况的思考。
真诚、自然是《灯盏2020》整体的风格特色,也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作者们不少身处基层岗位,以地区作协的专职作家为主,更不乏乡镇干部、乡村教师、农艺师等业余写作爱好者。他们把许多以往我们注意不到的细节、题材纳入了写作中,丰富了文学之树的脉络。有些作品使用的语言尽管粗粝但却富有质感,能打动人。散文中洋溢的原乡精神,诗歌中蕴含的多重意蕴,小说中含纳的广袤世界,无一不佐证着写作者的精神和态度。而他们敏锐的洞察力、追求创新的热情与真诚的创作姿态则进一步表征出一种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基层文学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