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应该做,就把自己投进去,当作一根柴烧完为止,不计得失。” 许倬云的“十日谈” 纸上的学问 生命的学问

许倬云
《许倬云十日谈》近日出版了。
2020年7月10日,许先生90岁生日。《许倬云说美国》(以下简称“说美国”)当天上市,“十三邀”的第二次线上采访《寻得自己的世界|许倬云答十三邀观众》同期播出。彼时,新冠肺炎病毒在中国“骤雨初歇”,而美国、欧洲势已燎原。人心慌乱,世局动荡,国际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受到极大影响。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
大规模的瘟疫,往往也预示着社会大变革的开始,比如伤寒肆虐的汉末至三国时期,黑死病、鼠疫蔓延的中世纪欧洲。混乱的变局当下,个体生命该如何安顿?人类世界将走向何方?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而我个人,过年前后也被封闭在湖北老家,两个多月,亲见疫情暴发以来的种种不幸。彻夜难眠时读到梁任公的联句,悲从中来:“春已堪怜,更能消几番风雨;树犹如此,最可惜一片江山。”所幸母亲在身旁,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未料两年后的这个春天,国内疫情又大规模暴发。
7月12日左右,许先生说他想做十次线上授课,有关瘟疫、战争、全球化、大国博弈、科技与人文,以及我们未来的“理想国”。中世纪佛罗伦萨鼠疫大流行期间,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创作了《十日谈》,许先生说我们也用这个名字吧。先是在高山书院以zoom远程授课的方式,讲了两个多月,有数十位学者、科学家、企业家参与讨论;后来整理成书,就是这本《许倬云十日谈》(以下简称“十日谈”)。因其为讲稿,这本书的语言较以往更为“鲜活”“在场”。当然,限于时间和条件,很多问题也点到为止,未及展开论述。
其实,当时许先生也在承受着病痛,常常需要大剂量服用止疼药。记得有次课程结束时,他说:“接下来我要做个手术,如果顺利的话我们继续。否则,今天就是我与大家的告别。”此情此景,令我想起“总论”中的“夫子自道”:“只有不息的自强,才是真正的健康和健全。”
去年底我到匹兹堡时,他的身体已经相对稳定,生活和作息复归常态。谈起学问以及我们正在进行的《万古江河》“续编”,许先生眼神清澈穿透,非常专注而高效,“不知老之将至”。以致师母常说:“他是九十岁的身体,四十岁的心。”
薄伽丘在书中说:那场瘟疫“先在东方地区开始,夺去了无数生灵性命,然后毫不停留,以燎原之势向西方继续蔓延”,“瘟疫流行,哀鸿遍野”。面对瘟疫,有的人节制生活,“凡事适可而止”;有的人则“肆无忌惮地纵酒狂饮”,为所欲为(王永年译本《十日谈》“第一天”)。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在开篇序言,薄伽丘呼吁“给苦恼的人以同情”,予悲痛的人以安慰。我想,这也是许先生讲述这个系列课程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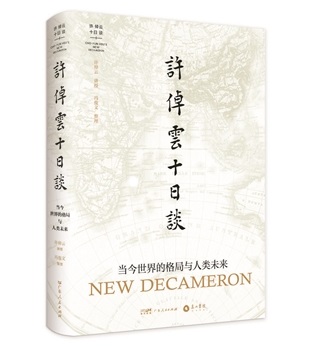
《许倬云十日谈》
纸上的学问,与生命的学问
除了正在发生的瘟疫,这本书还有更大的时空背景——近年来迅速败坏的美国民主政治,以及持续数年的中美“贸易战”。特朗普当选总统时,正值《中国文化的精神》截稿,在“后言”中许先生说:“美国两百多年的民主制度,强调人权、个人自由及种族平等。大家向来相信,这一代议政治即使不是完美的体制,较之帝制和独裁而言还是比较公平而安全的政治制度……这次选举中的民粹主义非常显著,选民只顾一己私利,公平、正义等更为宏大的价值,已经不在他们的关怀之内。这些毛病之所以产生,根源乃是西方文明长期建立在个人主义和物质利益之上。”
如此长篇累牍的引用,是因为这段话,似乎可以视为他晚年观察美国的“思想主轴”,也是“说美国”的写作缘起和动力——他们当年所亲历的那个开放、包容、理想主义、夜不闭户的美国,正在眼前一点点老化、崩解。而远在大洋彼岸的多难故国,终于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说美国”及《中国文化的精神》亦可视为这本书的“文化背景”和“延伸”,三者构成一“多元互动的秩序”。
“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这是战乱年代幸存者的刻骨之痛。近年来,我们时常能从许先生的著作包括这本“十日谈”中,读到其对中国未来的巨大期许。
作为接受过东西方最好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为:“不(仅)是招魂,而是迎接新文化的前驱喝道。”(《中国文化的精神》前言)然而,也有论者认为他是“民族主义”,尤其不能接受他对美国的批判。
这里有两个情况需要说明。首先,是写作者的“立场”。虽然自我身份认同是中国人,许先生毕竟在美国生活、工作了六十多年。似乎很大程度上,他是以“美国本土知识分子内部视角”,结合自己多年来所见所感展开论述。这也就决定了他的“批判性”立场——美国民主制度,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完美;当下在场的美国政治实践,与两百多年前、纸面上的美国政治,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此外还关涉到,许先生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规章制度和具体的执行,往往是“两层皮”。随着时势推移,二者间的差距可能越来越大,直至最后不得不调整改革——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所以他才反复强调,“看东西要看东西本身的意义,想问题要想彻底”(“十三邀”访谈),“我念书从来就不是在书本上念,而是在人的生活里看普通人的生活,看他们的生命里,遭遇何种困难”(“十日谈”总论)。
举例而言,本书第四讲引用安德森(Kurt Anderson)的观点说:“美国活力的丧失,是一种社会老化的现象。”当下的现实是:总统拜登已经八十岁,众议院院长佩洛西已经八十二岁。马斯克最近也吐槽美国政治被一帮老人把持,很难与人民建立真正的联系。前总统特朗普要限制新移民,然而如今的美国面临800万劳力缺口,有1200万人领着优厚的政府救济金不愿工作。人力成本居高不下,快递堆积在港口无人转运;货运中心洛杉矶的铁轨两侧,被偷盗的包裹碎片扔得到处都是——警察无能为力,因为预算和人力有限(《纽约时报》)。
以我在匹兹堡的亲身经历而言:房东Tom先生已年近八十,房产中介老板也已七十多岁。所以,他们不接受网络汇款、银行转账乃至现金支付,只能一次次送支票过去。最觉诧异者,他们至今都很习惯于用信件来传递信息,邮箱隔三差五收到历任房客的退款支票、银行账单、促销广告种种。或许这也是不得已之举:太多老人接受信息的习惯,已经固化在几十年前。当然也有好处——拿着带有姓名和地址的信件作为身份证明,就可以去卡耐基图书馆免费办理借书卡。
第二,是许先生对于“群经之首”《周易》里“变”的理解和运用。“不要理想地认为将来有东西可以完全替代什么,只有演化,只有无穷地追寻、改变,和因此而呈现更多的选项”(“十日谈”第三讲)。面对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扬美国模式所建构的“历史的终结”,许先生认为:“民主制度其实非常脆弱,任何一环松动就可能被其他制度代替”,堕入柏拉图所总结的军阀独裁、富人政治、寡头政治或僭主政治。“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不断更新的制度”(“十日谈”第十讲)。
有次提及这个问题,我请教许先生:“关于‘变化’,对于我们学历史的人而言,应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常识’,为什么您能够运用得如此深远广大?而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却熟视无睹?”他推荐我看法国“年鉴学派”的东西,并强调说“学历史要有common sense”,回归常识。
大同世界,修己以安人
关于中美之间的冲突,许先生认为是“文化之间的不协调,并不是文化冲突。东方文化没有办法反映到西方去,对西方没有冲击,或者冲击非常薄弱”。多年来,他出版的五本英文专著,除了《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65)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所写的博士论文,偏重于“社会阶层流动分析”之外,余者几乎都是围绕“将东方文化反映到西方去”这一目的而展开:
《Han Agriculture》(《汉代农业》,1980)的论述,早就超出书名所限定的范畴,致力于廓清“以精耕细作农业为基调”,两千年来传统中国的“基本盘”;《Westen Chou Civilization》(《西周史》,1988)则致力于解释这一“超越政治力量的共同文化”,如何最终形塑“华夏文化本体”——这两本书分别从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解释中国这一共同体的成因和内在机制,数十年来已成经典;《万古江河》则以梁任公的《中国史叙论》作为理论框架,讲述了“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作为许先生影响力最大的大众史学著作,各种版本累计销量近百万册,其英译本《China》(2012)成为美国大学中国史教材;新近出版的《American Life》(《许倬云说美国》,2021)及《The Transcendental and the Mundane》(《中国文化的精神》,2021),对美国历史与当下的反思以及中文文化的引介,在美国知识阶层引起的共鸣和反响方兴未艾。
在“说美国”和“十日谈”之中,常常感受到许先生对美国日渐败坏的哀叹,以及中华文明参与重整未来人类秩序的期盼。甚至《中国文化的精神》“后言”中,他都忍不住呼吁:值此人类文明转变关头,“西方文明已近削薄甚至毁损了许多其他文明。于是,我们必须要寻找新的因素,寻觅新生。此时,环顾全世界,能够对西方文明提出针砭的文化系统,只有中国这一处了!”
具体言之,“中国一直以来在政治、社会秩序上努力的方向,就是把乌托邦的政治理想与现实挂钩,把零碎的结构熔铸成为一张大网……广大区域共享福祉,这是中国人理想的结构”(“十日谈”第九讲)。
有关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许先生尤为关注“人心”,及其蕴含的无限可能:“你的心就是上帝,人心怎么想就造成你看社会怎么样。许多人的心合在一起就是众人的心,就是支配你、呼唤你、抑制你、鼓励你的力量。……修身修己到一定地步就要去照顾别人,安人、安民、安百姓”(“十日谈”总论)。这是明末东林以来,江南绵延四百余年的精神传承;也是许先生以一生的行持,所检验、亲证过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能理解许先生所主张“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毕竟在中国历史上,它从未真正实现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空有理念高悬,似乎并无现实可操作性。直到最近,有幸随侍先生左右,言传身教之下,才渐渐有了一点坚实的体会:理想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理想本身——“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勇气,得寸进寸的真履实践。“永远要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永远要有纠正错误的可能性。”
日前,他讲到当年参与台湾建设、变革时,内心秉持的信念:“认为应该做,就把自己投进去,当作一根柴烧完为止,不计得失。”也讲到晚年的严家淦先生与他的一番谈话:“不要求事功,不要求成就——只有求心之所安。事功靠不住的,及身而止,我们只能说那时候尽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做到了。”老骥伏枥,薪尽火传,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境界,于此可窥鳞爪。
最后,谨此衷心祝福,“烈士暮年”的许先生: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注:本文作者为美国匹兹堡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