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 《人世间》的叙事雄心和史诗传统的再兴

梁晓声 (1949~) 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生于哈尔滨。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八届全委会委员。著有《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返城年代》《年轮》《知青》等作品数十部,多部作品被译介到海外。长篇小说《人世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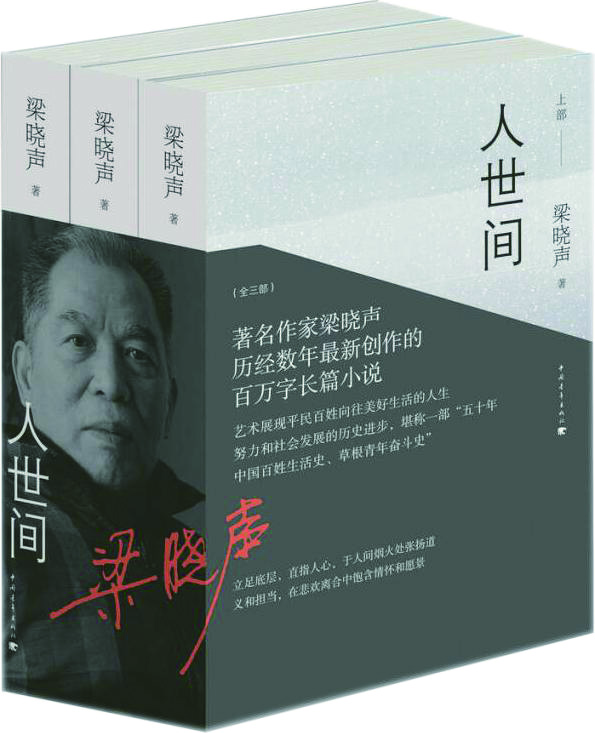
长篇小说《人世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梁晓声的三卷本长篇小说《人世间》2017年12月初次出版,2019年8月以最高票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出版之初和获奖之际,这部沉甸甸的厚重之作都曾得到过读者、文坛和图书市场的特别关注。但其强度和普遍程度,远比不上刚刚过去的虎年春节期间,由它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央视黄金时段首播后引发的这波收视热浪。这似乎表明,在社会传播和大众接受的环节上,直接诉诸视听体验的影视剧改编,对文本形态的原著,还可以一如既往地加持赋能、增光添彩。借此,从总结文学创作经验和评估文学创作得失的角度,对经由电视剧的改编而发生了形态或功能上的强弱显隐变化的原著成分,重新做些省察,或许能有镜中观像、他山攻错式的启益。这方面,容易在印象鉴赏式的评论中被忽略,而在实际的创作和作品意蕴生成的环节上却必须首先面对的第一要素就是叙述者。
在电视剧里,叙述者只是闻其声而不见其人的旁白。不过,著名演员陈道明的担当,让旁白的画外音带上了几分不出镜的特殊角色的意味。小说原著中的叙述者,则结结实实贯串了三卷文本的始终。他也是故事的局外人和旁观者,但他用周翔坦率的诉说和描摹,为整个故事开了头、煞了尾,为故事里每一个人物的言行举止配置了细致入微的心思神情,更时不时地站到俯瞰故事全局的“第三只眼”的高度,对故事中各色人物的遭逢际遇发表感慨和议论,最终使得他的声音和气息弥漫进了作品所有的缝隙和角落。按惯常的说法,这属于典型的全知全能型的上帝式叙述者。
相形之下,电视剧里的旁白显得节制、低调、收敛。第一集片头过后,旁白先声夺人地压着角色亮相的画面响了起来,像是要给全剧确定某种基调。但短促的时长和音色、腔调处理的局限,使得后续剧集中越来越零散的旁白在点明年代背景、解说画面细节和补叙人物内心感触之外,无法更多更自然地介入剧情,与配乐、台词和角色表演若合一契、相得益彰,达成渲染气氛和深化主题的组合效应。当然,这可能是从纸质书的阅读体验和阅读习惯中延伸出的一个过于苛刻的奢求。影视剧作为视听艺术和娱乐产业的结晶样式,原本也没必要像广播剧或有声读物那样倚重或者放大单纯的语言表现效能。
这里真正值得留意和琢磨的是:小说艺术的灵魂体现在叙述形态的构筑,追求现实主义史诗风格的长篇小说通常又把自身风格的构筑重点置于叙述者及其叙述方式的设定,可一旦要从小说改编到影视剧,首当其冲最先被剥壳似地大幅删减甚至彻底舍弃的,偏就是叙述者和叙述话语,嵌在叙述话语里原本被叙述者调遣摆布的人物和情节,往往倒能享受整体保留的待遇。
为了弥补这种损失,不少脱胎于现实主义史诗风格小说的影视剧,都精心保留并尽力凸显了在小说原著中起着统率作用的叙述者的声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茅盾文学奖得奖作品中,《钟鼓楼》和《平凡的世界》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同样都曾约请田春奎、张家声等资深的话剧演员和播音艺术家,配了极具表现力的叙述者旁白。近年重拍的《平凡的世界》在保留旁白的同时,还在片头加入了作家路遥本人诵读小说开篇语句的录音,流露出对小说原著深切的礼重之意。
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贯穿着现实主义风格的史诗叙事深耕力拓和不断转型的一条主线。“十七年”期间涌现的一批题材高度类型化的长篇小说,如反映解放战争的《保卫延安》《红日》,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反映农民觉醒和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红旗谱》《青春之歌》,反映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社会主义改造的《上海的早晨》,为谱写新中国成立前史和同步描绘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确立了异中见同而又同中有异的大拼盘模式。
进入1980年代,刘心武的《钟鼓楼》、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苦心孤诣之作,在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等潮流波浪相继、持续深化“十七年”模式的同时,另辟蹊径,为史诗气派的长篇小说蹚出了情节重心从紧张的社会斗争转向舒缓的日常生活、叙述语态从高调的“寓教于乐”转向平民化和个性化倾诉的新路。这种放低了身段、收窄了视野、穿行在家庭伦理和社会关系中偏向个体一侧的长篇叙事路数,在对于社会发展大趋势和大目标的把握、期许和信念上,与改革、反思和寻根潮流中激荡的宏大叙事旋律是同频共振的。但它们填补和充当的是高歌猛进的时代行进曲的低声部。在英雄人物领衔的传奇故事占满文坛“前台”的新时期初年,在亲情伦理的漩涡里打转的凡人琐事最多只能作为修饰、烘托主旋律的小插曲和背景音。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密集的商业关系和经济活动越来越宽广地抻开了人们彼此平视和横向打量世态的眼界,社会文化风尚和日常生活氛围中群体本位的理想主义气息渐趋淡薄,个人本位的现实主义旨趣日益浓厚,平民絮语式的叙事风格终于得其时而兴,在横跨小说、散文、诗歌以至话剧和影视创作的大范围里通行开来,绽放出“一代之文学”的几许光华。高冷严正的历史裁判官或沧桑阅尽的智慧老人式的叙述者,开始从文学世界里销声敛迹。先锋派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把叙述权分解成了歧见迭现的主观视角的自言自语。传统面目的长篇历史小说,也大都不再用事后诸葛亮式的史官或说书人腔调演绎全景视角和多线并进的“群英会”故事,取而代之的多是聚焦一点、单线叙述的人物传记,并且除了故事中的角色本身的自述和为此做情境补白的作者直接插话,无力也无心设置一个笼罩和掌控故事全局的元叙述者或元叙事层。被人物传记簇拥、堆积起来的历史小说热,好比秕谷满仓,算不得成色十足的丰收。
以“众语喧哗”的相对主义历史观相标榜的新历史叙事,跟拿着单线条的人物传记书写来处理历史题材的老派做法,实质上都在躲闪对历史进行总体性把握和总体性表达的繁难挑战。与此同时,荒诞或魔幻外衣的反写的英雄叙事和宏大叙事,却在文坛一角竖起了纛旗,若干长篇新作从传统现实主义史诗叙事的题材大本营里辟出飞地,更多的尝试则覆盖了传统史诗叙事似乎已无力涉足的文学取材的近景地带。
1980年代初,30岁出头的梁晓声因《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这两篇灌注了青春血气和英雄悲情的出道之作,接连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和优秀中篇小说奖而开始享誉文坛。随后三四十年,他在创作道路上可谓风风火火、马不停蹄,论作品产量之高、涉猎文体之广,均堪称同辈作家中的一流健将。仅长篇小说,自《雪城》以降,梁晓声就一直保持着至少每隔一年都会出一部新作的勤奋高产节奏。此外,他也以更加勤奋更加活跃的姿态,投身散文随笔和直击社会现实的时评杂感写作。
多数文学史教材和文学研究论著里的梁晓声,还停留在当年从伤痕、反思和寻根文学各大潮流侧翼掠过的知青文学的轻骑队中,而实际创作中的梁晓声,早已一路奔袭跌仆,走到了不得不向复归于新时期文坛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别的文学思维和文学观念的裂变地段。按他事后在《〈红色惊悸〉自序》中的回顾:“某一时期,我备感自己在现实主义这一条创作道路上疲惫不堪,而且走投无路,于是不得不踉跄拐向荒诞一径。”但就在再三试验所谓荒诞现实主义的新手法的同时,梁晓声从他反复写到的凡俗生活中的人与事中,渐渐确认了一点体悟:“少数伟人们,或可称为‘时代之父’;而我们平凡的人们,其实只不过永远是时代的儿女。顺应时代不可能不成为我们的生存法则……”
今天看起来,身为时代儿女的平凡人不能不以顺应时代为生存法则,这点体悟既关乎梁晓声的社会观,更关乎他的文学观。由此,在题材层面几乎扫遍了市场经济的激流所冲击到的各社会阶层生活样态的梁晓声小说,在创作方法和创作理念上,又重新回归并牢牢锚定在了现实主义传统的领地。与他早期创作的现实主义面目只是出于顺势而为的追随和模仿截然不同,近十余年梁晓声在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追求,带着深切的自我整合和自我反思意识。三四十年前流行的理想主义高调,随时代风尚莫比乌斯圈式的流转,已变声为日常生活情境下的平民絮语。梁晓声在《返城年代》里讲述的后知青故事,蜕去了特定人群的特定境遇这层外壳,跟他此前此后瞄准其他人群和其他类型题材所写的小说、剧本及非虚构的随笔时评,有了混融贯通的迹象。这意味着一个作家在人生和文学两条道路的长途跋涉中,终于走到了能够同过去的自我状态和过去的种种抉择逐一和解的境界。
于是,以往作品里那片被称作“脏街”的旧居之地,那些泯灭在贪欲和恶行中的人伦常情的幽暗扭曲之态,还有那些消退到唯功利是求的现实生活逻辑之外的美好理想和纯正信念,都纷纷移步换景,汇聚起来,拼接出一派温馨敞亮。而维系和凝聚这一切的能量,既不来自神祇所在的高渺的天上,也不来自暗沉沉的地下,它就在由一个个平常家庭组成的人世间。每一户和睦家庭的父母与儿女们代代传承的那分素朴平常的仁厚善良,就是人世间全部光与热的源头。在每个家庭里,都总是至少得有一个人为守护家庭的和睦而比旁人付出得更多。在《人世间》之前的作品里,梁晓声常把这个重要角色自然而然地派给母亲。在《人世间》里,这个角色从单数变成了复数,母亲之外,又加上了父亲,还有他们的小儿子周秉昆。
而这样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成立,创作机理上的微妙缘由就是整个作品的叙述者,其实是设定给了一个思想感情和认知水平都最接近大哥周秉义的隐身角色。周秉义对常年承担家累的弟弟深怀愧疚的心情,投射到对周秉昆苦乐交加的人生历程的叙述中,自有暖色滤镜或光晕衬底的一层增效功能。而周秉义从尖子生顺风顺水成长为高级干部的人设,也最贴近小说中的叙述者能够对光字片、共乐区乃至整个A城的历史纹脉娓娓道来,对1976年到1986年国家步入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意义也能作出精当评析的角色定位。
为了着力强化人世间的根基在普通百姓自身,有了官员身份之后的周秉义迅速远离了故事主轴,以至秉昆几次犯难遭灾,都没能得到大哥的关照;而一心奔着远方和诗去自顾自地寻找真爱的姐姐周蓉,以及曾深深吸引了周蓉的诗人冯化成,也都只是作为自否其能的扁平配角,衬托在秉昆和父母苦心支撑的家庭周边。与一生的职业履历顶点仅仅是一份大众文艺杂志编辑部代理主任的秉昆相比,后来任教大学的姐姐和名声在外的诗人姐夫都是货真价实的高级知识分子,但在维系和守护父母兄弟这个大家庭和他们自己小家庭的和睦幸福方面,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并不高明。在周家之外,秉昆硬着头皮求助过的姐姐的同学蔡晓光和下放老干部曲秀贞这两位贵人,用无私的行为证明:普通百姓和高级干部之间真诚的情谊联结并非没有可能,这跟周秉义与郝冬梅的跨阶层婚姻使秉义在仕途上得力不少的桥段有类似的意味。
秉义为官多地终于还是得到了调任家乡A城副市长的机会,毕业后本已留京任教的周蓉也因婚变而突然调回了家乡的大学。这些情节安排显然都是为了把周家儿女围拢在父母身边,让他们的故事和秉昆的故事交织起来,共同演绎成一个不被岁月长河冲散的大家庭的故事。这正遥遥呼应了通过讲述家庭和家族的兴衰起落来映照时代变迁和社会风云的明清长篇小说的叙事传统。其构思的诀窍,是在看似范围狭小的家庭和家族内部关系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关系之间,勾画出尽可能隐蔽而又尽可能深切的对应线索。
从以上简单列述的几组人设用意,《人世间》叙事架构的精心和雄心已可见一斑。相信对于宝刀不老的梁晓声以及众多抱负远大的长篇小说创作的年轻干将们,已经赢得高声喝彩和热烈关注的《人世间》都不是终点,而是醒目的新起点。诚望现实主义史诗风格的叙事传统由此再兴,史诗气派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逐浪竞起。
(本文得到北京市文联基础理论研究项目支持)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在《文艺报》所开设的“文学观澜”专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2022年3月18日第5版。)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