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学》2022年第2期 | 张锐锋:古灵魂(节选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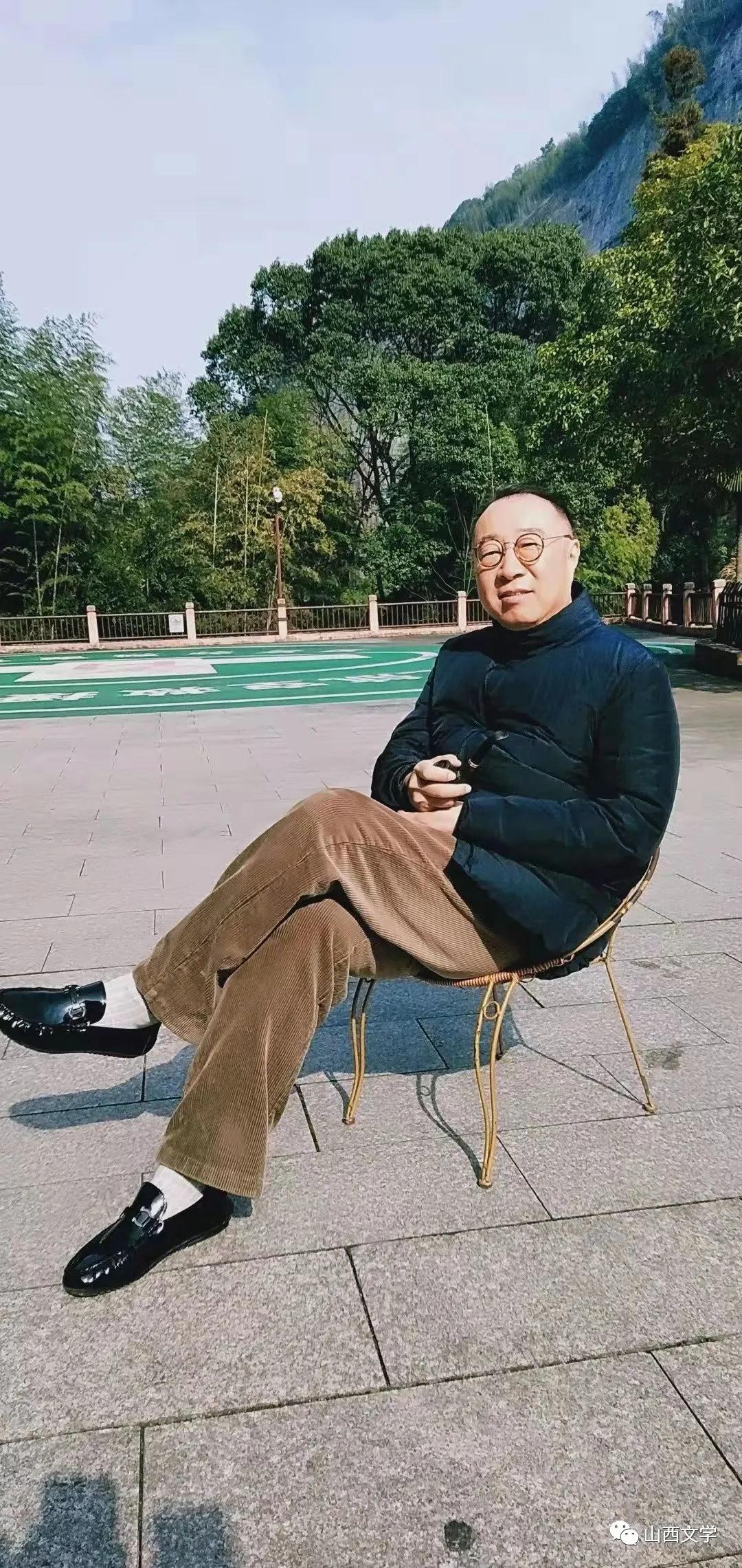
张锐锋,当代散文家。出版文学著作30部。曾获十月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
古灵魂(节选之二)
张锐锋
车匠
这是多么大的河啊!汹涌的河水卷起了巨浪,激起了巨大的轰鸣,两个人大声说话都不能听清。我从没有看到过这么宽广的河流,对面的河岸已经超出了人的视线,不知道它真正的河岸在什么地方。我跟随唐国的国君一路东行,要到他的封国去,可是要走多少个日子才能到达?我将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继续我的生活。据说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尧舜禹居住过,我们的先祖也居住过,可是我们为什么总是到陌生的地方?
在熟悉的地方一直待下去,这是最美好的。熟悉的房子和熟悉的工匠,熟悉的都城和街道,在天子之都能够见到最尊贵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那样神秘,以至于我们不需要知道别人,只要看着自己手中的活儿就可以了。
我的祖先一直到我,都是制作车辇的,我的手艺是上一代传下来的,我不关心别的事情,那是别人的事,我只是把车造得好用、结实、漂亮。这一件事我已经做了几十年,还要做下去。一个人这样活着已经足够了,除了天子和国君,谁还能做更多的事情?其实,即使是天子和国君也不过做一件事情罢了,不同的是,他们看上去做的事情很多。
史官把天下发生的大事记下来,并且传下去。天子把自己的江山守护好,并且传下去。武将拿好自己的兵器,要么把敌人杀死,要么被别人杀掉。农夫种好庄稼,每一天看着云彩,希望在干旱的时候降雨,又盼着在收割的时候每天有太阳照着。我当然在我的房子里,拣选着木头,看看哪一样适合装在车子的哪一个地方。我看着这些木头,有着说不出的欣喜,因为我的心中早已经从它们的形状中看出了它们应该成为的样子。与其说车子在我的头脑中,不如说它们早已存在于生长着的树木中,我只是动手去掉它们多余的东西,让它们一点点在我的汗水中现形。
我的先祖是黄帝的七个佐官之一,有着显赫的身份和不朽的荣耀。那时还没有车子,人们搬运重物的时候,往往需要众多的人们抬起来,既费力气,也挪动不了几步的距离。哪怕搬动一块巨石,也几乎不可能。要是这样一直下去,人们的一生中差不多什么都做不了。在人们面对石头或者其他重物无能为力的时候,我的先祖番禺不是像别人那样唉声叹气或者干脆放弃,而是昼思夜想,用什么方法做这些几乎不可能做的事情?他相信世间的事情都有它的理由,只要找到埋在深处的理由,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从居住的四周寻找着天神的启示,也不断祈祷上天赐给他灵感。
一些想法就像闪电一样划过,但瞬间就熄灭了。有一次他坐在湖边,看到独木舟上的渔夫在捕鱼,木舟是那样轻巧,那么小的舟竟然能够载着渔夫在水中自由地游荡,只要渔夫用一根木头轻轻一划,舟就轻快地转弯或者前行,水竟然有着我们无法理解的力量。他找到了事情的本来理由,他开始用一大堆木料制作了大船,只要把重物搬到船上,剩下的事情就是借助水的力量了。人们用树枝一起划动,就可以非常省力地搬运。这真是一个上天赐予的好主意。
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他的儿子奚仲出生了。奚仲从小就心灵手巧,显露出了非凡的智慧。番禺有时候就在儿子的身旁观察他玩耍。一次,奚仲用黏土泥巴捏制了一匹马,又捏了一艘船,把马拴在船上,并使劲儿吆喝着让马快跑。番禺就笑了,这是什么游戏啊,我造的船是在水里行的,你的马儿是在地上跑的,它们怎么能凑在一起?奚仲回答,你造的船的确是浮在水里的,可是我的马拉的是地上的船。儿子的话引起了番禺的深思:船不一定非要行在水中,要是地上也有水的浮力那该多好。
奚仲长大了,他像父亲一样热爱思考。人们经常看到他不是坐在河边的草滩上,就是坐在旷野的石头上,有时会整整一天发呆。谁也不知道他的头脑中究竟有些什么古怪的念头。可是,人们只要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奚仲总能给他们满意的答复,找到最好的办法。他一直想着造一艘地上的船,实现自己的儿时游戏中的愿望。这样,人们就再也不会因搬运重物发愁了。
一次,他看到深秋的蒿草被风吹得滚成了一团,在野地里不断地旋转。他还追了一会儿,感到了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事物是神奇的。还有一次,他又看到一块圆石从山坡上滚了下来,越滚越快,直到停在了不远的地方。令他激动的是,他们都具有一个特点:滚动。又一次,他在制陶的工匠身边看了很久,快轮带动着泥坯飞速旋转,他们用轻微的力气就能把一块泥巴弄得浑圆而光滑。
车轮……用车轮就可以让船行走在地上,简直是一个天赐的灵感。他在野地里兴奋地奔跑,直到浑身被汗水浸透了。是的,他早就知道,世界上一定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在前面等着。如果它没有,只是你没有想出来。
现在,我们就要登船了。这岸边的船多么大啊,我们几乘车都可以一起放到上面。我是骄傲的,无论是我们乘坐的车还是现在渡河的船,都是我们的先祖发明的。没有我们的先祖,很难想象唐国的封君怎样去大河的对岸,又怎样去到自己的国?这样,天子的分封和委派也就变得毫无意义。或者,根本就不会有天子,因为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家族,只能呆在一小片地方,一遇到大河的阻碍,他们的脚步就得停下来。这意味着,没有一个人可以一统天下,将万千山河以及它的居住者归拢到一个人的影子里。
你就想想吧,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伟绩,先祖的思考和发明改变了世界,我们也因此生活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朝代。这么说来,世界上真正的统治者是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活着的人们不过是死者的民,那些看起来有权支配他们的,实际上仅仅是死去的人们的暗影,只是一个没有具体面目的轮廓,他们的眼睛、鼻子、嘴巴乃是安放在另外的地方,要看到他们的真实面孔,要到厚厚的泥土下寻找。
好啦,刚才有人和我谈起制作车辇的事情,我的回答是简洁的,我只是简单地告诉他车的来历,剩下的该属于我。一些东西也该摆到外面的车辕上,另一些我需要藏起来,放在我的衣襟下面,我有自己的秘密。事实上,这些秘密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不能用语言说出来,我只有自己在制作大车的时候,选择木料的时候,仔细审视木头的直线和曲面的时候,才能将这些秘密说给我手中的活儿。我的故事都在我的工作中,这是充满了悬念的一个个冒险故事,比那些绘声绘色的讲述一点儿也不差,甚至更精彩。
我从父亲一代的传教中记住了车辇每一部分的形状和尺寸,还记住了它们的制作方法。这可不是容易的,但是记住还不能算一个工匠,还要在具体的操作中做到毫厘不爽。你要运用自己手中的斧头和锛,还要观察木料的湿度,鞣制车轮的时候还要借助火的恰好的热度,不能有丝毫的偏差,这需要你不断地做,才能找到锐利的感觉。比如说,战车和人所乘坐的车就不一样,要适合不同的用途。车轮的大小也十分重要,如果太大了,人们就不便于登车,借助高凳上车,那将多么繁琐,也没有必要。一个制车的工匠为什么不能做的尺度恰好呢?当然,轮也不能太小,否则骖马和服马拉起来就像总是爬坡一样,那样,马也就不舒服了,它们耗费两乘车的气力,却只能引得一乘车向前。我不能让车子在行进中耗费加倍的力。车辇是需要一点点改进的,它需要不断地融入我的思想,我的生命也一点点地注入到越来越好的车子的形象里了。
车子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讲究的,它的尺寸和样子不是任人打造的。没有一件事可以恣意妄为、信手而作,那样一切都会变得很糟。车辐必须一头粗一点,另一头细一点,不然在沼泽地上或者雨天的泥泞里行走,就会带起更多的泥土,最终让车子陷入无望之境。轮辐嵌入车轮的辙牙和毂,必须掌握好榫卯的尺寸,太长容易折断,而太短则不会牢固。车的牙辙要尽可能做得窄一点,它与地面的接触面越小越好,否则车就会因为路的摩擦不能奋马疾驰。可是,辙牙太窄了,就会在泥路上刀一样切削,也不利于行进。车辕的弧度也要做得恰到好处,太大了,揉辕就易于折损,太小了,辕马一旦倒卧就不容易重新站立。我越来越觉得,一乘车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那世上的学问该有多少。
你能做好一件事也是多么不容易啊,何况世上又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又有哪一件事是容易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为此付出全部心血的理由。即使是选用,一个部件的材料,也需要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技巧,不然你其他的技艺再好,也会因材料的选择不当而前功尽弃。营造一乘车的过程简直就是人生精华的浓缩,它的每一步都通向制造者自己。
我要用富有韧性又要耐磨的榆木来做车轮,车辐则采用外表美观、光洁而坚硬的檀木,车牙必须用橿木,它既有韧性和弹性,又经得起磨损。要是想得到你理想的材料,还需要你亲自去深山中寻找所适合的,伐取这些珍贵的树木还要注意恰当的季节,并不是每一个季节都属于你。树木若要生长在山丘的阳面,你就要在仲冬节令前往砍伐,这样树干中的水分正好适于制作,若是生于山阴,因为它所见到的阳光太少,就需要在仲夏斩之,还要将这些斩伐的木头耐心蒸煮,再用火烘烤。如此应时而行,揉曲车辕、辙牙和削制轮辐的过程一样不少,才能保证你的车子形状不变又结实耐用,经得起崎岖颠簸,也经得起路途泥泞和两军对垒的激战考验。一乘车是用来使用的,只有使用才会告诉你做得怎样。
这也仅仅是大功告成的一部分,为了加固车辇,还要在一个个连接处施以皮胶,在车毂上覆以皮革,还要在许多关键部位涂以厚漆,以及套上铜铸的车軎并贯以车辖……我不能一一说清我所做的每一个细节,但这些已经足够多了。即使一乘车做成之后,仍然要经得住验收,要套上上等的良马,在驰道上奋力驰骋,必须做到奔驰千里马不伤蹄,也不能让马匹在驰骋中感到疲惫不堪。在一年四季的驾驭中,御车者能够从容应付每一个可能出现的路况事端,他的衣衽不会因慌乱而敞开,也不会因处理事故而弄得衣衫不整,即使在松软的泥土中疾驰,也要保障车身的平稳,它的每一个部件都不能损坏或者折断,只有造出这样的车子,才能称得起世代传承的良工国匠。
这些过程以及一乘车所需的每一个部件,都有着长长的故事,有血的故事,也有泪的故事。因有血泪的沾染,它就变得完美而优雅。它是一乘车,难道它不是一部人生启示吗?我们在什么时候做出选择,什么时候开始制作,又在什么时候打开另一道工序……都要严密的、不可有丝毫失误的刻苦用心。重要的是一切都必须恰当,这是多么难啊。从一乘车的形象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即使你十分用心,世界并不会给你以分毫不爽的恰当之机。有人问我造车的秘诀,我只提炼了两个字:恰当。除此之外,即便最复杂的,也是很容易的,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就足以应对。
我就要随同我的新主人去到遥远的唐国了。那里将有新的家,新的造车之所。对于我来说,只要让我造车,我就拥有了一个永恒的家。我所居住的乃是有木料和制车工具的地方,我的睡梦是一个个即将完成的车的样子连成的。除此之外,不论到了什么地方,都会使我失去归宿。我所跟随的主人,是引领我命运的服马,在车的位置上,也许看到的不过是不断晃动的马尾,我不过是它后面的车,或者仅仅是车在灿烂的天光下投下的一片黑影,我虽然也在疾驰,但我疾驰的原因是因为马的奔跑。
现在,我已经在宽广的河面行进了很长时间了。驾驭大船的舟虞正向每一个操桨手发出命令,他们一起用力,有着完全相同的节奏,一个个大波浪被他们挥动的桨板压了下去,然后大船又冲上另一个波浪。今天我所乘坐的船同样源于我们先祖的智慧,无论是在车上,还是在船上,还是在徒步行走中看到车上和船上的乘坐者的欣喜,我的激动之情都会溢于言表。我的面容涌上了一阵阵微笑,我的内心浮现一个个波澜,这心头的大波浪要比大船下的波浪还要激烈,也拥有无数船桨压不下去的猛力。
舟虞
从大河的这一边到另一边,并不是十分遥远,尽管从岸上看去,河的波浪是无穷无尽的,你既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它最终的去处,它浩大的水势冲绝了一切阻挡,也冲开了如此宽阔的地带,让巨量的滔滔流水得以奔腾而去。对于我来说,驾驭巨舟就像行走在土地上,这不过是一片不断移动的土地而已。我从小就在河边长大,熟悉大河中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道暗流,我的双眼能够看穿水底的每一个转弯和暗藏的大石头。不熟悉河流的人不知道它的奥秘,实际上,每一条河流只要有足够的宽度,就必然有着它的道路。是的,大河中是有道路的,只不过它是隐秘的,不随便告诉别人。
我的舟船是巨大的,我还没有见到过比这更大的舟船。好几乘车可以开上去,排列在它的上面,让拉车的马儿和车上尊贵的乘坐者,目睹我高超的行船技艺。武王讨伐殷商的时候,就是凭借这样的大船渡过了盟津。八百诸侯汇集在武王四周,师尚父姜太公持着饰有黄金的大斧,另一只手握着白牦牛尾装饰的军旗,发出了盟津之誓。负责舟船的职官称为苍兕,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古怪的称呼——也许是面对苍茫的大河,就像虎兕一样凶猛?师尚父誓言说,苍兕啊苍兕,你们要汇总各自的军队,给你们最好的舟楫,出发吧!落后者将被处斩!可以想到,那么多的大船汇聚在一起,将是多么恢弘的景象!若是没有这样的舟船,又怎能一鼓作气荡平暴虐的商纣王?
我的舟船上载的是唐国的君侯,武王的儿子,天子的胞弟。这是怎样的人物,他将赶赴他的封国,治理他的土地和人民。我的舟船曾载着多少人渡河,这一次,我所渡的是一个非凡的君侯。他也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渡舟者,不过他的舟船更大,是整整一个国。他将把他的土地和人民渡向哪里?这个国的河岸在什么地方?我把他引向对岸的时候,还会默默地注视他的每一个动作。
我看到,他坐在舟船的前端,晨起的阳光在他的背后留下一片黑影,而他的前面则一片光明。他穿着彩色的衣裳,一动不动地面对着前方,好像一直盯着对岸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块山岩。不断翻滚的波涛,把光的幻影扑到他脸上,河风是猛烈的,有时掀起了衣襟,但他仍然一动不动,有着磐石一样的稳定。他一定在沉思,他的封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他的第一件事情将从哪里做起?也许,他根本就什么也不想,只是享受风浪中起伏的渡河历程。一只水鸟从船头箭一样飞过,他好像动了一下身边的弓箭,但还是恢复到了原来的静止状态……这个人,是水中的巨石,即使遭遇再大的激流也纹丝不动。
我在舟船的中部,对于前面的水路,即使是闭上眼睛也知道到了什么地方,船应该怎样行。顺着激流的方向,穿过波峰之间的低谷,绕过水下的大石头,避开汹涌的暗流,从一道弯曲的斜线向彼岸发去。我用一个手势告诉掌舵的人,他的双手用力扳动尾舵,舟船就偏离了暗藏的惊险。一切是顺利的,岸边的山岚从高处降下,就像有一些天上的神蹬着云走向人间。我们就要到了,赶来迎接国君的人们已经开始欢呼了,只是他们的声音仅仅沦为惊涛中的一阵沙沙声。
在一个操舟人的眼中,所有的乘客都是被渡者,他们现在在船上,一会儿就会下船,到他们应到的地方。他们是谁,已经不那么重要。唐国的国君也是乘客,所有的人都是乘客,我的责任就是把他们送到彼岸。我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剩下的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不知道人还有没有来世?若要人生不是一次,我也是在渡河中了此一生。不过我的河是真实的河,也是虚幻的河,而其他乘客们和我不一样,他们看到的彼岸不是真正的彼岸。
唐叔虞
路途是多么遥远啊,我不断地在车和船之间轮换,既经过了一望无际的平川,也路过峰峦起伏的群山,当然要在汹涌澎湃的激流中感受每一次惊险,又在脚步踏到岸上的时候觉得地上的实在。一片又一片沼泽,我从它的边缘小心翼翼地穿过,也在湖泊的湛蓝前停下车轮,我不让别人跟从,只是一个人来到湖边的石头上,静静地坐一会儿,这给我很大的享受。我觉得我的土地不仅是一种颜色,它给人的遐思也远不是一个方向,我的呼吸如此舒坦,好像空气中被神添加了香料。
我远远地看到了都城,我的都城,有着高高的城墙和雄伟的门,一条石头砌筑的大路通向其中。我站在城前问旁边的大臣,你们想象的都城是什么样子?他们给我绘声绘色地描绘都城里的美景,可我一样也不信。他们的话与真实之间是有距离的,因为他们所没见到的又怎能告诉我?我只是借此提醒自己,我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却要住在里面,成为陌生者的主人。
这里的旧主人已经被迁往别的地方。天子之所以把我遣往这里,就是让我把这块土地守护好,以防周朝的山河被夷狄侵扰。先王用怎样的智慧和武功赢得了天下,它是用马蹄踏出来的,用车轮碾压出来的,又用血来浸泡。现在我来到这里,依然能够感到野花下面的血腥,青草已经压住了敌人的墓冢,清晨又给它加上沉重的露滴。只有原本的颜色,血的颜色,还停留在开着的花瓣上,当然,这些花瓣也会凋谢。事情是为了遗忘才发生的,然而,我来到这里却是为了记住曾经发生的,以让它不再重演。
我巡视我的土地,它不算太广,不过方圆百里而已,人口也不是很稠密,但它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它的东面是十万大山,这些山峦一个连着一个,几乎没有尽头。它还有着无穷无尽的沟壑,以衬托山峰的巍峨。其间有着数不清的河流溪水,它们日夜流淌,不断汇集到了更大的河流中。群山在密林的覆盖中显得不同凡响,在四季中变幻着色彩,不论是谁都会在其中迷失了自己。我相信,山林里是没有路的,除了林中的野兽,我们都不知道路在哪里。好像我的土地为我布设了一幅古奥的谜图,让我感受世界的变化莫测。
我不需要懂得一切,我最需要的就是懂得自己。只要能够从自己开始推演,就能破解外部的难题。我聪明的先王就是在被商王囚禁的羑里,推演出了可以预知未来的卦象,我想先王不仅观察天上的星图,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的心灵。他发现,地上的心灵都和天上的星有着对应,这是万事万物变化的根基和原因。很多时候,人们太多地关注外部的变化,却遗忘了自己隐秘的心灵。
夏天来了,一场豪雨把地上冲刷得这样干净。太阳是这样炽烈,很快就将地上晒出了一片一片发干的痕迹,树上的叶子就像会发光一样,亮得有点儿让人晃眼。我已经在我的城中走过了,街道是整齐的,人们铺上了干燥的沙土,行人们已经躲开了我的车辇,四周除了我的大臣和侍卫,没有更多的人了。我叫来了一个城里居住的国人,他完全操着唐国的口音,我几乎听不清他说些什么。他似乎已经被我的威严和气势吓坏了,可我的口气是柔和的,一点儿也没有为难他的意思。我仅仅是想了解一下他们对这个国的看法,也想知道他们需要我做点儿什么。
我又在城墙上俯视这座国都,比之于天子之都,既不怎样广阔,也不怎样繁华,但这里可以望见不远处的翔山,山势的两侧很像一只飞翔的巨鸟翅翼,尤其是天色渐渐暗淡,它看上去还在飞,它似乎永不疲倦,和我现在的心一样,不知道究竟要飞向哪里。的确,这个国已经在我的手里,我将决定它的命运,它和我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满天的星斗,哪一盏是神用来照亮我的灯?
唐国的北面、南面和东面,还居住着尚未开化的戎狄,他们逐水草而居,在山野里过着野性的生活。他们心性不定,反复无常,有着我们很难理解的古怪习惯和剽悍的性格,随时侵扰我们的安宁。我们怎样能够安抚他们,才能让我们高枕无忧?唐国的旧族曾参与叛乱,被我周族平息,人心还不稳定,政局也十分复杂,我已经料到了翔山的险峻,也在星光下看到了路的暗淡,然而,我也听到喜鹊的叫声,它在高高的枝头上,不停地叫着、叫着,分明带着几分喜悦,也有一点儿忧伤——究竟是喜悦还是忧伤?
我在盛夏的日子里,来到了谷地里。我看到了农夫在炽热中在田垄里拔去野草,他们衣衫褴褛,有的几乎赤身裸体,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即使我以一国之君的威仪和他们说话,他们也不会微笑。他们的嘴角没有甜,只有苦涩的日子挖出来的深沟。仔细看他们的脸,发黑,没有光泽,却有着刀疤一样的皱纹,汗水顺着那些沟壑弯弯曲曲地流着……这些令人伤心的面容,简直是唐国山河的缩影。
我也看到了牧人,一只羊羔在他的怀里刚刚死去,他抱着这只蒲公英一样的小东西,眼角有着泪痕。他的羊群在山坡上,和野马一起嚼着草根。它们有着长长的脸,和放牧者十分相像。有的已经吃饱了,卧在树荫下慢慢咀嚼肚子里存放的食物。它们比自己的主人要快乐——我多么希望自己成为那个牧人,替那些伤心者伤心,又看护好那些快乐者,让他们不要有担忧,还给他们阴凉的树,他们好在下面一点点地享受已经获得的生活。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场景,我所渴望的正是羊群和马群所渴望的,我所忧伤的也是放牧者所忧伤的。我要坐在山间的青草地上,望着流水和蓝天,让一切所在的,依照原来的样子各在其位。应该是怎样的,还让它怎样,还有什么比原本的事物更美好呢?
我的土地是肥沃的,天上给我的雨水也足够。唐国的人民在苦难中煎熬,战乱又给他们带来了灾变,该是让他们休养生息的时候了。被大火烧过的荒田需要休养才能耕种,连续多年种植谷子的熟田,也需要通过休养才能重新获得肥力。我得到的启示是,一个人为了走更长的路,就不必一直用最快的脚步赶路。我需要慢一点,需要休息一会儿,喝点儿水,我的唐国需要积蓄那些从前被消耗掉的东西,需要慢而不是更快。它的心灵是焦渴的,云朵里的雨水,再多一点儿吧。
农夫
前些日子一直没有下雨,田里的谷子都快枯死了。田野的谷垄里被太阳晒出了一层层皮,它们就像河里的波,一丝丝地卷了起来。我每天都望着天上的云,看它们在什么时候飘来,又在什么时候离去。好多次,我以为要来雨了,先是从东面的山顶积聚起了云气,渐渐地浓郁了,有了发黑的样子,阳光也不那样强烈了。它开始离开山头向我头顶的方向移动,并将零散的云拢在了一起。然而,没有多久,它的颜色变淡了,又四散而去。这多么让我失望。我举起的头又低了下来。
唉,地上的事情尚且捉摸不定,又怎么期望天上的事情如愿以偿呢?我每天观察着蓝的天,它是这样蓝,蓝得让我感到发晕。在每一个夜晚,月亮也在没有云彩的地方行走,它一点点升起,把我的眼睛照亮。我坐在自己的屋子前,盼望着天神的恩赐,地上的谷子和我的愿望是一样的,我要的不多,仅仅需要一场好雨,把我的路打湿。
有一些日子了,每天都去地里拔草,但是这些野草也都枯萎了。它们卷起了叶子,露出了黄边儿,尤其是那些很小的、叶子很细的草,你只要拿起来两个手指一捻,它们就成为一些粉末。现在,我不需要再去理会这些小草了,每天早上开始就坐在田埂上,望着一片垂头丧气的谷子。微风吹动着它们,把更热的气息灌到它们的身子里,我内心的骚动越来越强烈了,这骚动来自隐隐的不安和忧虑。
我听说唐国新的国君就要来了,从前旧的君主已经因反叛周天子而获罪,他的军队已经被击败,他的家族已经被迁移到遥远又偏僻的地方,对于我来说,他们已经不存在了,将有另外的主人落入我的视线。作为一个农夫,他们对我是不重要的,不论是谁来治理,我仍然在地上敲土块。不论是哪一个国君都需要谷子,而这些谷子需要我的双手来栽种。何况,说不定新来的国君要比旧的更好一些?当然,你也不要指望一个国君成为你想要的,你没有这样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属于谁,要由弓箭和长矛来说话,也要天上的星辰说话。他的手中握着天命。我的手上只有耒和铲子,还有土地里埋下的种子,这又有什么用呢?我热爱土地,但不喜欢这土地让血来浇灌——而每一个国君的脸上都涂满了血污。
国君的变换远没有天上的雨云重要,因为国君不能让谷穗变得更加饱满,但一场雨就能够做到。可是,现在的国君据说是怀着上天之命,也怀着悯人之心,相传他武功盖世,但心却是柔软的。不然为什么他一来到这里,就带来了一场久已盼望的甘雨呢?我的土地上终于接纳了天上的雨水,我亲眼见证了那令人心醉的一刻:云气从东边的山背后缓慢涌起,翻过了无数山岭和沟壑,把阳光很快就遮住了。先是一些稀疏的雨点砸在地上,我听到了谷子的叶片发出刷刷刷的声息,好像它们要直起弯了太久的腰,要抬起头来了。很快地,雨越下越大了,整整一天的光阴,豪雨扫过了整个田野上的禾谷和山上的密林。
我的房屋背后有一条路是通往国都的,我只要转过房角就可以踏上那条路。而另一条路则通往山林,我经常上山砍柴,就会走上这一条小路。有一天,我打柴归来,沉重的柴捆把我的头压得很低,我的身体几乎完全埋在了柴捆里,从外面看去,就像一大捆柴自己在山坡的小路上移动。我听到一群人的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了。我放下背上的柴捆,眼睛里所看到的,是一些衣裳华美的人……他们一定从唐都而来,我赶快躲到了柴捆的后面,生怕冒犯了这些有权势的人们。
就在这时,一个人来到我的身边,对我说,这么重的柴火,你背得动吗?接着他招呼他的仆人帮我把柴捆扶起来,并把我送回到家里。我问那个仆人,你的主人是谁?他严肃地告诉我,我的主人也是你的主人,他是新来的国君,天子的弟弟。看来,这个国君还是一个好人,他会给我们多一点,不会像以前的君主,只知道在收割之后,打发官吏前来命我们交出最好的粮食,从来没有问过我们将如何生活。而且,我从来没见到过那个旧君主,他不是在有着高高城墙的都城里,就是在豪华的车辇里,即使从我的房屋后面的路上走过,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影子,一片盖在我身上的、取不走的咒语,我也没有从那个空洞的暗影里获得过一点温馨。
昔日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新的日子是被一场好雨洗干净的。我日夜想着我的谷子,听到的都是土地上禾苗的话,第一次听到了高贵的一国之君和我说的话,这话是温和的、悦耳的,就像干旱日子里的雷霆,使我的心灵感到了震动。
铸铜师
我看着炉火在燃烧,铜在釜中沸腾,那么坚硬的铜在我的火焰下变成了水一样的液体,我还要使它变成我所需要的形状,烈火真是无坚不摧。我是烈火的崇仰者,我却不知道火究竟是从哪里来的。火是无情的,最有力量的一般都是最无情的。它有时能够把一座宫殿焚毁,只要顷刻之间,那由万千人工建造的宫殿就灰飞烟灭,可是建造它是多么不容易。山上的树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燃起一场大火,从一个小小的地方蔓延,很快就把整个山头烧得通红,烤焦了林间奔跑的野兽,甚至连飞鸟也来不及逃脱。
可是这无情的东西也有温情脉脉的一面,每一家的屋顶冒出袅袅炊烟,意味着生活是温馨的,火又成为生活的缔造者。农夫们用火烧掉了旷野里的野草和树木,才能播撒良种,我们的陶碗里才会有香气缭绕的米饭。在火烧过的田野,谷子长得多么好啊。可是,我不仅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它从来没有固定的形状,永远处于最活跃的状态,火苗一闪一闪,让我们的手捕捉不到,也不能把其中的一片拿下来。它看起来是附在别的东西身上的,比如你拿一根树枝引来了火焰,可是它却有着自己的主见,至于要怎样燃烧,什么时候在哪里冒出一个小小的尖,那是它自己的事情。
那么必定有一位神主宰着火,火有着神的意志,它不让我们懂得它的奥秘,我们所做的仅仅是使用它,并且在使用它的过程中需要千百次地通过神的测试,不然,你不是煮不好饭菜,就是将饭菜煮糊了。据说我们的火种是从燧人氏开始的,他从火神的手里第一次接过了火,从此火就进入了人间,参与了我们的生活。冶铜也是这样,我要全神贯注地盯着每一个火苗,还要看铜水表面的渐渐变深了的颜色,火隔着炼铜的釜传递到了铜块上,竟然让每一块铜也燃烧起来了……事情是多么神奇。
我想象着火神的样子,它一定有着红色的头发和长长的脸,它的胡须也是红色的,它要是行走在旷野,我一定能够认出它来。我曾经在墙壁上画过它的模样,我还将我的米饭放在它面前,让它知道我的生活来自火的恩赐。我所做的就是把带火的铜水浇注到模范中,显现出神奇的形象。它会成为祭祀的国器,也会成为国君使用的各种器皿。看看那些用来饮酒的爵、觥和斝,再看看那些造型各异的盉与簋,还有那些各种各样的铜鼎……它们都是火的造物,栩栩如生的飞鸟,面容可怖的神兽,云起飞扬的花纹,以及各种令人心动的形象,都以铜的质料凝结在最合适的地方。这些形式自然有着独特的意义,它至少烘托了高贵者的位置,也划开了高贵与卑贱的界限。
高贵者还将他们的事迹铭刻在鼎上,也将他们的名字和记号铸在使用的器物上,因为铜是一种坚硬的、不易毁损的、也更能经得起时间磨蚀的物质,他能满足君王和贵族将自己的事迹传之久远的欲望。他们也许认为,人仅仅有一生是不够的,在一生结束之后,还需要用另外的方式延续自己的存在,铜是最好的灵魂寄寓物。可是,这些精美的实体将会流落到什么地方?又传至什么人的手上?
也许它还会成为曾经拥有者耻辱的见证,给他们腐烂的尸骨上涂上肮脏的粪。我们可以想一下不可一世的商纣王吧,他曾经拥有的,比以前任何人都多,他有最高的权力,有无法想象的酒池肉林,又有数不完的美女、珍宝、玉器和世界上最重的鼎。他也不缺乏文字的赞颂,在各种精美的铜器上刻满了他的名字,可是最终的结局呢?他被杀掉了,他的宗庙被毁灭了,宗庙里的彝器被得胜者夺去了,放在了别人的宫殿里。他的名字被唾沫洗了又洗,再落上岁月乌黑的尘垢,最后将埋在别人的墓葬里。
这是多么大的耻辱,拿着自己的光投向漆黑,又把灰烬放入充满了便溺的粪池。光荣和耻辱可能会在时间中转换,它的奥妙在于,你想把自己变成什么,却总是变成了你不愿变成的样子。所以,在我看来,最好的铜器不是放置文字的,它上面只有花纹和美丽的图案,它不记载任何事情,它只是用铜的光泽和耐久来告诉工匠的手艺,以及铜的形象和重量。有人说,你可以做成另外一种样子,我告诉他,铜只能是它本来应有的样子——我所做的就是铜的本意,任何违背和歪曲铜的本意的想法,都要受到铜的惩罚。也就是说,我所制作的一切铜器,不论它刻上谁的名字,也不论是否写了不该有的文字,最后的结果是,铜不会改变这些内容,而是在时间中静静地等待。褒扬和贬低,光荣和耻辱,都会在等待中获得评判。
现在,我又要把炽烈的铜水放到塑造它最后形象的模范里了,里面早已预备好了它的花纹、它的文字。其中有着世界上最完美的形状,有花草、树木、飞鸟和野兽,也有云气、雷电和饕餮,有我见过的,也有我从来没见过的,还有我永远不知道来历的,可以说世界上有的或者没有的事物,都已经应有尽有。一个铜制品的理想就是包含一切,将能够有的形象放在一个形象中。
唐国的新主人已经来了。我还是原来的生活,我的生活不会因国君的改变而改变,因而我一点儿也不关心谁来让我做工。我只是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工作,并把他们的想法放到我的想法中,这样,我已经就像我所做的铜器一样,我已经包含了他们能够想出的一切想法,并让我卓越的手工来实现它。我的制造物配得上一切君王,因为它将在所有的时代中存在下去,并让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来欣赏它。
屋匠
我们最初的祖先女娲就是一个屋匠,她不仅用泥土创造了人,使我们一代代繁衍,还炼制了最好看的石头补天,又用巨鳌的脚立起了四极。是的,我们需要居住在自己的天底下,这就是我们的屋顶。女娲也许是从鳌足的支撑中受到了启示,我们的房屋就立起了柱子,并撑起了屋顶,我们的头顶就有了遮挡,雨雪就不会漏下来落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都是泥做的孩子,就像我们在小的时候也用泥土捏制过人一样,当然,也捏制过其他东西。女娲之所以用泥土,是因为泥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东西,它既是最卑贱的,也是最高贵的。它卑贱,是因为太多的缘故,到处都有,你走到哪里,都会在泥土上留下脚迹,也会使它站在你的脚上。然而它的高贵之处在于,即使最高贵的人也离不开泥土,它提供我们食粮,也提供我们脚踏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了泥土,就会落到了无底的深渊里。
我是一个造房屋的匠人,已经营造了无数房屋,每当我看到人们住到了房子里,就感到无比快乐。我就像我的祖先一样,一生和泥土打交道,我把泥土兑上适当的水,把它变成了泥巴,然后将它们抹在墙上。我用树木的干作为房屋的立柱,也用树枝和草秸搭成了屋顶,我的手艺是人人称赞的,我做的活儿又快又好。我抹好的墙壁是那样平滑光洁,就像用石头磨制的一样,我造好的屋顶不会漏雨,也经得起时间磨蚀。在冬天到来之后,里面不会太冷。即使是在最寒冷的时候,人们也能从我的房屋中找到温暖,并在寒夜安然入梦。我看到,在无声的大雪降临后,一些房屋被厚厚的积雪压塌了,而我造的屋子总是安然无恙。
我既会在国君的都城里建造房屋,也会在郊外的地方施展身手。要盖好一座房屋,一定要将地基打得坚实,这样上面的房屋才能牢固。实际上,盖房子就像建立一个国家,必须立在地上。没有坚实的地面,你的柱子就不可能立稳,如果你的脚踩在了泥泞里,就容易陷落或跌倒。相传已经有新的国君来了,接管了唐国,他能否找到他的地基,并让这地基变得坚硬?又怎样才能盖上严实的屋顶?
听说当今的天子已经赐给国君众多的大臣,以辅佐他的新政。我不知道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才,有着多大的智慧,但有一点似乎是真的,那就是他尊重我们的习惯,使我们的生活仍然保持原来的样子。有人告诉我,国君是一个善良的、体贴我们的人,他鼓励农夫种植谷子,也勉励工匠做好他的手工,也让牧人专心看护他的羊群和牛群。不过,这些都是听说的,我并没有亲眼所见,也没有亲耳所闻。
多少年来,营造房屋的经验告诉我,最好的房子是那些结实的、并不感到十分华美的,当你居住其中,你甚至不留意它少了什么,也不会为它随时操心。在雨天你不会担心它漏雨,也不会在什么时候担心它的柱子倾斜了,房屋可能会塌下来。它既不会给你某种惊喜,也不会给你更多忧虑——你一旦拥有它,它似乎就不重要了。
一个真正好的国君也是如此,他坐在国君的位置上,却不显露他的模样,他路过我们的身边,我们却不知道车辇里究竟坐着什么人。他即使与一个农夫在一起,我们会以为他和我们一样,并不是一个地位崇高的人。当然,一个国君是尊贵的,他一定与我们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他所做的并不是可以要做的。我们不期望有一个让我们每一刻都能感觉到他的强大和力量,也不希望我们的生活被嵌入了一个高于我们的、有着强权的人,我们需要自由自在的、没有任何人干扰的生活,我们只要专心致志地做好我们本分中的事情。
我们新来的国君,好像有点儿像我描绘的样子了。我既没有见过他,也还没有感到他已经来到了我的生活中,他在高高的座位上看着我们,而我们又看不见他,这是多么让人感到惬意的日子。好了,我还是和我的泥巴打交道吧,国君的事情归于国君,我要为我的房子操心了,我的双手已经伸到了柔软的泥团里,其中有着别人不知道的温暖。
……
此为节选部分,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