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2022年第1期|曾攀:生命的无常与抒情的引渡——论巴金的战时散文

曾攀,文学博士,《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近年在《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小说评论》《现代中文学刊》《文艺争鸣》《当代文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上海文化》《上海文学》等发表文章近百篇。文章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著有《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人间集——文学与历史的生活世界》《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乐黛云传》等,参与主编《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等大型丛书。
01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巴金在抗战期间的散文创作,涉及他战时出版的散文集如《短简》《控诉》《旅途通讯》《黑土》《废园外》等。而所谓战时,对于巴金个人而言,主要包括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期间的散文写作,之所以将这段时间巴金的散文创作称为“抒情的迁移”,从大的方面来谈,主要从内部与外部两个层面进行考虑:一方面是从巴金战时散文的文本内部,往往存在着种种反向认知抒情形态的发生、运行与转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巴金散文中与战局、时局对应的抒情形态,其往往直接传递出感情的关切和关怀,将个人意绪情思寄寓于历史的变迁之中。
20世纪以来,中国的抒情传统就在现代文学中不断发抒,普实克1957年的《现代中国文学的主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指出中国新文学从抒情到史诗之变,“但普实克的观察有其复杂之处。他又认为‘史诗的’文学之得以兴起,有赖世纪之交文学秩序的解散,而这一解散得力于创作者主观意识和个人主义的萌发。吊诡的是,他强调所谓的主观意识和个人主义与其说是西方资源的输入,不如说是传统中国抒情诗学的下放。以往在精英话语中循环的抒情符码现在被挪至一个更广阔的,名为史诗的语境中,但并不因此失去其感时观物的命名力量。”抒情与史诗,两者并非截然有别,传统文化的“抒情”因素一直流播至20世纪内忧外患的中国,并产生了诸多新变。陈世骧的《中国抒情传统》《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等著述,以及高友工等学者的系统性阐发,再到后之来者的李欧梵、王德威、陈国球等人的开拓,关于现代中国的“抒情传统”已经愈发开阔。
在巴金的散文写作中,抒情并非不言自明的,而有其独特的生成机制与效用机制。“相形之下,只要对中国文学、思想传统稍有涉猎,我们即可知晚清、‘五四’语境下的‘抒情’含义远过于此。‘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因此对西方启蒙、浪漫主义以降的情感论述可以提供极大的对话余地。”⑴尤其是巴金的战时散文,在情感生成的内在机制、历史叙述的时空流转与抒情主体的精神构架方面,都表现了独异的个性。从文本外部看,巴金的战时散文创作,凸显了国度的跨越、有从个人到群体的发展、有虚实变化的多重维度的结合,由是创生出独特的美学话语构建,如是这般向外延伸的抒情模式,使内外结合疏密有致,相互贯通,在“无常”的境况与“有情”的抒情之中,构成了现代中国散文发展的新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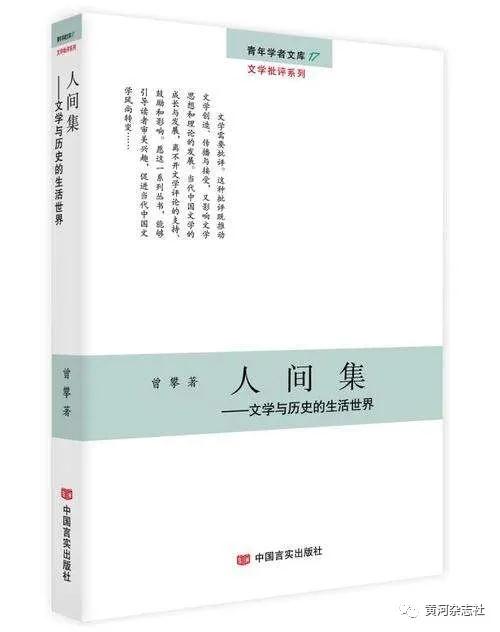
02
在巴金的战时散文中,一方面是反面的充满悲哀的“无常”,战争导致的人民生灵涂炭、流离失所,尤其是内心的悲楚和哀恸,打碎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流动。如《爱尔克的灯光》:“然而人的安排终于被‘偶然’毁坏了。这应该是一个‘意外’。但是这‘意外’却毫无怜悯地打击了年轻的心。”另一方面,则是正面的充满鼓舞的“无常”:“忽然在前面田野里一片绿的蚕豆和黄的菜花中间,我仿佛又看见了一线光,一个亮,这还是我常常看见的灯光。这不会是爱尔克的灯里照出来的,我那个可怜的姐姐已经死去了。这一定是我的心灵的灯,它永远给我指示我应该走的路。”灯光固然是一种隐喻,在暗无天日的战时历史中,需要照亮前路的光源。在巴金的战时散文中,“无常”是一种常态,战争的、人事的、命运的常态在特殊的时代境况中被扭转,甚而说,“无常”成为了战时情状下之常态,然而在巴金那里,这样的外在状态时常转圜为一种“有情”的观照。答应了姐姐回来看她并且相信自己的诺言可以兑现的巴金,在离家不到一年的光景,就收到了姐姐不幸逝世的噩耗。他认为这个“偶然”是“意外”,只想把它当成是一个“意外”。然而,这个“意外”让时隔多年返乡的巴金的心情变得更为沉重。物是人非,对姐姐的怀念只能化作梦里的一盏灯。思念姐姐,思念家人,是对充满悲哀的“无常”的“有情”观照。而对正面的“无常”的“情”,则从批判封建家庭的陈规陋习中体现出来。“长宜子孙”扼杀了年轻一代,祖父为他们创造了家业,临死还为儿孙安排周到的生活。“长宜子孙”历经几番风雨不曾褪色,是封建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财富容易消弭年轻的灵魂,拥有生活技能、崇高理想才是子孙后代繁荣发展的长久之计。“浪费,浪费,还是那许多不必要的浪费——生命、经历、感情、财富,甚至欢笑和眼泪。我去的时候是这样,回来时看见的还是一样的情形。”⑵用财富来维系子孙后代的发展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他们失去了追逐人生的乐趣,“我”匆匆来了,也匆匆离去。远处有明灯等待着我,为“我”的前进指引方向。封禁观念无法囚禁有坚定信念的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让作者带着喜悦之情冲破封建家庭的禁锢离开。“巴金散文始终以情感波澜的渲泄和奔流为本色。他的散文,无一不是炽热的情感与生活交汇熔炼的结晶。他的情感是无尽的源流,一旦打开闸门,就会飞流直下,一泻千里,任凭什么力量也不能把它阻遏住。情感的大潮,产生了巴金散文的动力。凭借它,巴金散文才成了一条滔滔不绝的,向着无穷无尽的生命之海喧啸着,奔腾着的江河。”⑶因而可以说,情绪的涌动在巴金散文中是一个重要的表达形式,他往往从抒情主体的观感与感知出发,通过景、物、人、事的交融触动,一层层打开情感的与激情的内核,最终达到情感修辞的适当之处。
《废园外》是通过“无常”传达“有情”的经典。抒情主体于散步时无意间又走到了墙的缺口处,从缺口望去,欣欣向荣的后面却是一片悲凉之景:楼房倾塌,花园变成了废墟。巴金用勃勃生机之景来反衬日军轰炸后的荒凉,本应是享受天伦之乐的人们,转瞬间就被敌人无情地摧毁了他们的家园。“但是望着一园花树,想到关闭在这个园子里的寂寞的青春,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着似的。连这个安静的地方,连这个渺小的生命,也不为那些太阳旗的空中武士所宽容。”花儿依旧在,人已非往昔。悲哀的“无常”从别人口中听来,从“我”眼中看到,心中的刺痛已经不是眼前的绿色可以舒缓。面对战火,人们是渺小的,是最不能经受摧残的群体。通过描写这些悲哀的“无常”,他细腻地传达了对弱小生命的惋惜以及对战争的厌恶、对日军暴行的强烈愤恨之情。巴金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残暴,而是从年轻的生命的逝去切入,以此控诉暴君的罪行。不能永远停留在悲伤中,头顶滑落的雨滴把他从黑暗中拉回到现实。“脸颊上一点冷,一滴湿。我仰头看,落雨了。这不是梦。我不能长久立在大雨中。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⑷同时,这也是巴金对人们的点醒:我们需要赶紧从悲苦中走出来,不能任人随意践踏,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团结起来反抗黑暗和邪恶,这是战争的流毒在戕害人们的生命,而抒情者巴金的情绪也随着情节的推进愈发激越。
革命战争时期,巴金对死亡有了新的体悟与思考。《死》中没有畏惧死亡,没有感慨死亡,而是从“死”中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寄寓了他要实现人生意义、活出自己的可期之情。“我用了‘放心地’三个字,别人也许觉得奇怪。但实际上紧张的心情突然松弛了,什么留恋、耽心、恐怖、悔恨、希望,一刹那间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那时心中确实是空无一物。”⑸对于很多人来说,死亡可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历经无数次的意外,“我”都存活下来了,使他对“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炮弹随时会从天而降,穿透屋顶,砸落头上,这时的“我”更多的是拥有了一种得以解放、解脱的心态,紧绷了无数次的弦终于可以放下。全文围绕“死”说了多个话题,有幻想的“死”,有加本特对“死”的描述,有“死而复生”的真实显现,还有古田大次郎的《死之忏悔》。“我”虽然说了很多关于“死”的话,但是还想活,“我”还想看见阳光、天空,春光、秋景。巴金先生的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渲染死的恐怖,也不是赞叹死,而是给人们传达一种信念:有限的生命,无限的价值。我们无法控制悲哀的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在它的到来之前,在有限的生命中绽放光彩。继《死》后,巴金阐述了对生的认识。《生》中阐明了他对“生”的理解,每个人都要认识自我,实现自我。他认为,生命如流水般,一旦有了开始,它就一直在运动,一直在创造。“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⑹这是巴金从正面鼓舞人们要发现自己,寻求自己的亮点。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间轴上生息、奋进,聚焦个人体验,实现人生价值。这是巴金散文中常见的正面抒情,召唤人们有目标、做奉献,在其中建立自我及主体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价值是建立于死的威胁与生之搏斗之上的,因而其精神的强度和生命的硬度层面都呈现出非同一般的状况。
巴金作为战争亲历者的“体验”并不是简单的个人经历,而是如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体验”不仅是“直接性”的“只是为解释提供线索、为创作提供素材”,而且应当具有“一种新的存在状态”(Seinsstand),“显然,对‘体验’一词的构造是以两个方面意义为根据的:一方面是直接性,这种直接性先于所有解释、处理或传达而存在,并且只是为解释提供线索、为创作提供素材;另一方面是由直接性中获得的收获,即直接性留存下来的结果。……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种东西就属于体验。”⑺对于巴金和他的战时散文创作而言,那就是在地理/情感/美学迁移中的战时抒情形式建构。巴金从上海到桂林、昆明、成都、重庆等,其行迹及散文自身叙述的铺衍,正是以一种文本的抒情的迁移,印证革命的行旅的曲折多变,更表征现代中国的跌宕起伏,不同的地方性书写间杂着战争所反射出来的普遍性的精神情绪,在巴金的散文中呈现出既相对稳定的情感基调,同时又由于行旅和迁徙的差异,具备了更为丰富复杂的质地。如《桂林的微雨》《贵阳短简》等,记录了巴金在桂林、贵阳等地的经历,多为目睹了各地的革命情况。在《贵阳短简》中,巴金体验了贵阳午后阳光的灿烂,夜晚美丽的星天,还有热闹的街道,可是,这仍然阻挡不了人们逃离的步伐。“大家抢先恐后地挤到一个无形的热海里去洗一回澡。头上是汗,心里是火,大家热在一起,大家在争取时间,大家在动,在战斗。大家都疯了。”⑻人们为了离开,需要经过无数漫长的等待;为了离开,需要搭上无数的痛苦;为了离开,甚至斗殴起来。在等待中,人们情绪失衡了,确乎如此,战争状态下的漫漫长路,背负着生命艰困的行旅之路更是不易,从巴金的战时散文中,也体会到了民众的苦难,这成为了巴金写作的丰富材料来源。在这个过程中,巴金以抒情的笔墨将苦难加以引渡,这是非常艰难的,也并非都是有效的,现实的苦闷并非通过文字的抒发就能排解,尤其战争中的精神困境,文学甚至往往只能敲敲边鼓,略为抚慰。在《月夜鬼哭》中,巴金直接描述了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并对之进行控诉,在巴金的散文中,还有另一层更为深切的关心,他时常能够通过自身的叙写形态,游走入历史的深处,一方面是揭示战争的现实并揭示未来之期冀,点亮明灯之指示;另一方面则是对人们的砥砺鼓舞,是充满人性的关怀和生命的悲悯,透露出非常强有力的生存意志。也正是如此,巴金的战时散文具有非常强烈的精神引渡之功能,而且其中如金子般的意志和情感,在整个抗战文学史中,都是非常值得珍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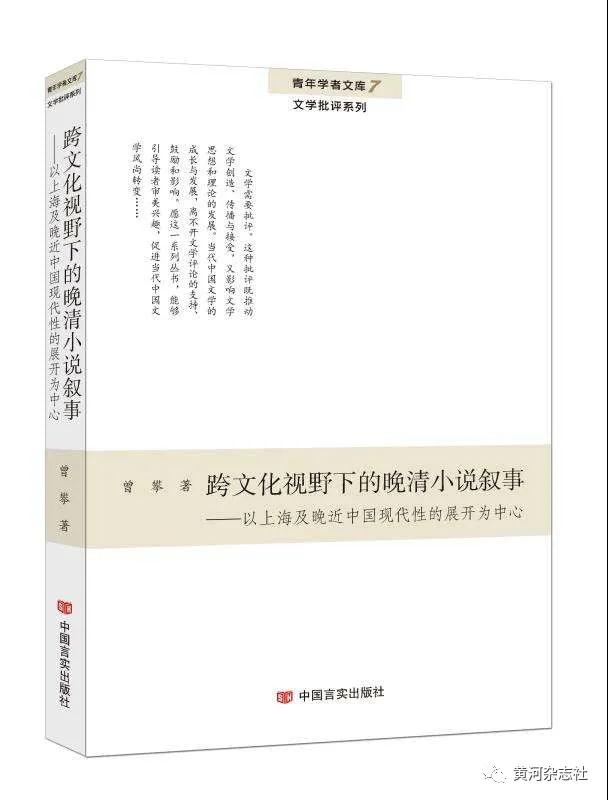
03
时间的迁移所形成的新的历史意识与当代关怀,构成了巴金战时抒情的最重要的形态。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在“无常”的战争情势下,散文的或说文学的形态是如何参与其中的,文本与语辞内部的运转又怎样参与到“抒情的引渡”之中,这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在《桂林的微雨》中,巴金说到:“这个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梦。我回顾四周,没有朋友,没有守夜的人。现在不是在夜间,我也不要找人和物件。我不要到这里来。但是回忆把我不知不觉地引到这里来了。”⑼白日与黑夜、回忆与畅望、历史与当代,在与时间无尽的周旋中,吐露情感。在这个过程中,巴金的情感仿佛从流动的时间与自然的迁移中脱落,从而使得巴金的战时抒情,既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充满现实的关切。更重要的,我们明知道巴金在战时的书写必定附着种种诉求和情绪,整体的抒情却又是如此的自然贴切。可以说,综观巴金的战时散文,其情感生发的自觉意识是如此的浓郁而强烈,然而丝毫不着刻意为之的痕迹,这其中存在着一种章法自在的抒情形态。
而且,巴金散文中还表现出动荡与迁徙中的在场感与亲历性。巴金抗战时期的散文并不由于情绪的宣泄和情感的抒发,而丧失逻辑与文法,现实的困境并没有将文学内在的话语讲述和情绪发抒阻隔,相反,外在的刺激成为了文本内部涌动之情感的一个重要出口;在这样的境况中,巴金散文的文体与美学自觉,往往蕴蓄于内在的情绪、大众的情感与家国的情怀之中,散文文本内部的时间/空间流动与情绪/情感推移紧密勾连,从而具备了更浓郁的情感和更阔大的格局。从生活场景到社会场景,再到战争景象,现实的与虚幻的镜像叠加。成为了巴金战时散文的抒情模式。甚至,我将之命名为一种“迁移的迷阵”,在迷阵中牵引自我,觅出方向,尤其是建构出了一种逐级向上的抒情样式。
如《从南京回上海》,巴金从上海到南京,再从南京返回上海,这期间蕴含着他复杂纠葛的情感。这篇散文中的时间叙述得很清晰,“一月二十九日早晨四点钟”“二十九日过去了,三十日也过去了”“三十一日的早晨”“二月一日早晨”,可以说,随着文本时间的推移,作者的情绪也不断发生变化。相较于南京的安静、寂寞,上海传来的悲惨画面,使巴金渴望早日回到上海。从一开始地慢慢寻找机会回上海,到后来的有途径时就立马动身的急迫,渗透着他深深的责任情感——与大家同呼吸、共命运。“不是打算在必要时交出自己的生命,就是准备做一个难民,等候慈善家来收容。”⑽巴金在回答朋友见面的问题唏嘘感慨,其中凸显出极为浓郁的情感流动。战火无情,巴金将个人感情投入到抗日战争环境中,一同抗战,全民族抗战,而不是坐以待毙,更不是讨取可怜,其中既有着种种个体的意志精神于其中,同时又始终贯穿着国家民族的情感,因此,寄寓其间的悲痛事实上不断求得更多的共鸣。在南京,“我”常去旅馆旁边的贴满电讯的地方关注上海的消息;人们没有受到影响,准备过年;电影院开映巨片;饭店坐满了客人……然而,上海传来的是罄竹难书的日军残杀讯息,市民被无辜杀害,房子被焚烧,对人们带来的只有无尽的痛苦,憎恨的根深深扎进“我”的心里。南京生活一派祥和,而上海却是惨不忍睹的侵略场景,空间切换对比,是对草菅人命的侵略者的厌恶,是对顽强抗战人民的敬佩,还有自己“隔岸观火”的无奈。“烧吧,让它痛苦地烧吧。让它烧热我的血,烧热我的血来洒到那些屠杀者、侵略者的脸上。”⑾黑烟弥漫在上海的天空中,痛惜的感情已经殆尽,然而在这种条件下,奔腾的热血却在身上流淌,确乎要将充满哀怨与悲愤的感情转变为誓死拼搏的坚韧,把对人民与祖国的挚爱书写得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巴金散文文本内部的情感、情绪与情思的迁移同样值得注意。细读巴金的战时散文,抒情的迁移,最后不是幻灭,而是引向理性,引向生之坚毅,承载着不可消解的信念甚或是信仰,正如《在泸县》中写下的:“一个中国的城市在废墟上活起来了,它不断地生长,发达。任何野蛮的力量都不能毁灭它。我怀着这个信念回到了船上。”⑿这个也关涉到巴金的思想一贯性,其中的美学的“迁徙”,一直流播至后来的《随想录》等作品。可以说,从文本内部而言,巴金战时散文的所谓“抒情的迁移”,构成了充实的文体结构、宽广的叙事视野与丰赡的抒情形态,并进而延伸至外部的“迁移”,内外贯通、彼此勾连,当牵扯到外部时,则涉及到如下几个维度的“抒情的迁移”:首先是跨越国土的迁移,在《黑土》中可以找到印证,其中借中国茶房的嘴讲述了一个俄国人对着黑土垂泪的故事。朋友看过这样的场景,“我”也在法国影片里看到类似的场面。“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在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草原,沉默的,坚强的,连续不断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动着无数的黑影,沉默的,坚强的,劳苦的……”⒀俄罗斯的土地孕育了朴素的俄罗斯人民,而作者流落别国,心里却记挂着国家的土地,体悟着国土的气息,那一堆黑土应该还蕴含着小草的芬芳……人从哪里来,总会想着回到哪里去。我们从红色而温厚的土地中来,终归要回到土地,回到祖国,回到母亲的怀抱中,这是每个国家儿女的心之所往。尽管生活再糟糕,有“黑土”伴随,就有希望可言。俄罗斯有“黑土”,我们祖国的南方有“红土”。看着俄罗斯人对着“黑土”垂泪,不禁让巴金回忆起南方“耀眼的红土”。黑土带给俄罗斯人希望,红土给巴金带来独异的生活回忆。在红土上,“我们”尽兴讨论着令人热血沸腾的话题,大家充满着献身的热情。阴暗的房间里,有着照亮他们前路的明灯。俄罗斯的“黑土”和中国南方的“红土”都是一样的,它们都能给国人带来希望,只是洒落在世界的不同纬度。用外来“黑土”抒发对“红土”上的自由、充满希望之情,内外相勾连。第二个维度的迁移体现在群体上。有自我牺牲意识的巴金先生把群体利益放在了个人利益之前。“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忌。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在太阳底下走十多里路,汗流浃背,他们没人顾及自己的难受之情,只知道“我们”要去那个陌生的地方,那里充满新奇,满是前路的期望。陌生的地方,熟悉的人,谈话让他们愈加兴奋。他们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大家说话坦诚相见,从陌生到熟悉,成为了兄弟姐妹,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时也变得单纯、贴切。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忘记一切阴影,朝着远方的胜利出发。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只有团结起来,以朝气蓬勃的态度才足以抵抗外部侵略。在《生》中,巴金认为,人生在社会,为他人奉献,生命才有意义。在黑暗的年代,奉献自己、牺牲自己,也是实现人格尊严和价值的一种道路选择。巴金亲眼看见过日军轰炸的情景,亲眼目睹血肉横飞的惨状,亲眼望见同胞的恐慌逃跑。对于一位只能用笔来为战场贡献的作家来说,何等痛心与无奈。这样,个人的利益在这个关头变得无足轻重,民众的利益才是首位的。“友爱包围着我,也包围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这是相互的,而且是自发的。”从“我”起,从大家起,鼓舞大众站起来,未来可期。不仅是巴金认为这个民族的未来是有希望的,还有一群热血的青年,抑或有更多的平民百姓建立在共情上奋战,表现了民族的团结之情。
第三个维度的迁移则是虚实迁移。在巴金的作品中,“红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原野,在这孕育着一切的土地上活动着无数真挚的、勇敢的年轻人的影子。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的朋友。”⒁作者在回忆南国红土上发生的事情,眼前浮现的红土感动了他的内心。时代更迭,瞬息万变,如今的青年敢于冲破内心的藩篱,内心虽有恐惧但毫不犹豫,敢于在风雨飘摇的乱战中传达自己内心的想法。红土飘曳的场景是幻想的,但青年朋友的激情是真实的,那片红土激励着“我们”,动荡会过去,持久抗战、永葆磅礴气势,慌乱会远去。描写幻想的场景语言朴素自然,是对南方土地最真实的感受,抒发了对朋友的怀念以及他们依然在作战的欣慰之情。不管是什么维度的迁移,贯穿全文的中心只有一个:巴金的爱国情怀。巴金谈到他的创作说,不想用血淋淋、悲惨的画面去折磨读者,通过人物、生活、命运来表现社会现实,以此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且每篇文章都有一个情感的中心,在《黑土》中,贯穿全文的中心就是:“我”爱这个民族,“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里的人民,这样的爱恋通过巴金的抒情话语不断升华,涤荡灵魂,召唤人心。
04
在巴金的战时散文中,摧毁生灵的战争带来的悲戚的人事与悲哀的情境,由丰盈的主体进行吸纳与吐露。在这个过程里,一个丰盈的“看”的个体,演变成有着自我体验的现代主体,从而构成一个形而上的抒情装置,引导出新的具有引渡功能的精神文化形态。《在泸县》这篇散文是巴金在重庆追述四川泸县的情境:“这个不设防城市的毁灭必然包含无数凶残的暴行,烧夷弹点燃的烈火一定会像嗜血猛兽似的吞食了许多人的血肉。这都是说着我熟习的语言、过着我熟习的生活的人们的血。血涂在墙上,血也涂在我的心上,是这些人的血自己在向我讲话,是这些人的血自己在叫喊复仇。”⒂激越的情绪在巴金的散文中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表达形态,这样的情思经常长久的蕴蓄,在一瞬间奔涌而出,构成巴金战时抒情的另一重境界;散文《灯》则以灯光酝酿和触发感情,进而凝聚力量趋向光明。然而,细细想来,以“灯”而达致希望,似乎是颇为虚妄的。但是巴金的灯,勾连思绪、牵引人事,化无为有,游虚入实。从而生成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力量。
收录于《旅途通讯》中的《在广州》,巴金讲述了在广州感受到炸弹袭来的经历。伴随警报声的到来,你永远不知道头顶的飞机什么时候会扔下炸弹,你永远不知道它会落在什么地方。面对炸弹的掉落,巴金以极其冷静的文字来叙述他的生活活动。“我在这里用‘震撼’二字自然不恰当,因为房间不过微微摇动一下,我还觉得一股风吹到我的腿上,别的就没有什么了。”他认为用“震撼”形容炸弹的落下过于夸张了,只是轻微的摇动。面对轰炸的大无畏,更加突显爆炸的平常,仿佛与死为伍。冷静之余,巴金先生还是走向了“灾区”。悲惨的故事从朋友口中得知:一个人从地上爬起来拾起自己的断臂接在伤口上托着跑;一个坐在地上的母亲只剩了半边脸;手里还抱着她的无头的婴儿。惨不忍睹的“灾区”:房屋断壁残垣,家人“流落四方”。但是这个城市给了作者镇静体验,不怕死,炸弹过后,街市还是往常一般热闹。从出版社到咖啡厅,再到出版社,都不断有飞机在上空盘旋。可是,这个城市的人民就是那么地倔强,“风雨过后”依然可以从容生活,巴金在早晨被警报声惊醒后依然可以沉沉睡去。这是广州这个城市给巴金带来的生活体验。
然而,战争带来的悲惨不言而喻,巴金无奈中接受了这种紧张的空气,需要冷静地去接受生活中要面对的一切,并且他还要告诉读者:人要成长,人要接受现实,最终实现一种精神摆渡。另一篇同样收录在《旅途通讯》中的《在轰炸中过的日子》,也是巴金先生的广州经历描述。“有一次警报来时我看见十几个壮丁立在树下,十分钟以后在那里只剩下几堆血肉。有一个早晨我在巷口的草地上徘徊,过了一刻钟那里就躺着一个肠肚流出的垂死的平民。晚上在那个地方放了三口棺材,棺前三支蜡烛的微光凄惨地摇晃。一个中年妇人在棺前哀哭。”⒃从自我体验中抒发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对未来生活寄予无限厚望:战争结局固然悲惨,它们都带着阴郁、衰败的气息,但是,战争过后,我们依然要生活。他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深切思考:炸断老树可以长出新芽,那么,这个城市被炸后也可以重新焕发生机,新的房屋会被建好来替代炸毁的旧房屋,大街会热闹起来,人潮涌动。这个城市给了巴金不一样的生活体验,给了巴金生活的信心。他十分满意这个城市,即使在动乱的时代,依旧可以进行创作出版工作。在这种特殊的体验下,巴金还锻造了自己的乐观情绪:我们多做好一件事情觉得心情畅快,于是兴高采烈地往咖啡店或茶室去坐一个钟头,然后回家睡觉,等待第二天的炸弹来粉碎我们的肉体。展现自己面对不确定的积极态度,是对大众的一种关爱,社会意识得以呈现。巴金在文末还提到,机器未停止转动,我们也要转动起来,这是他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通过形象的与画面的描写,把灾难下的人们的生活苦难充分展现出来,同时也是对日军野蛮行为的仇恨悲愤,家国情仇汇于一处,构成了巴金战时散文最深切厚重的肌理。
“既然在‘现代’的情境里谈抒情传统,我们就无从为这一传统划下起讫的时间表,也无法规避西方理论所带来的冲击。更重要的,抒情传统所召唤的历史意识必须持续与时空经验里的——而非只是本体论的—‘当下此刻’相互印证。”⒄巴金战时散文中透露出来的,是一种真切的在场,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某种“本体论”,当然这是其整体立意抒情的基础,但更重要的地方还在于“当下此刻”,更在乎深远广大的国族命运和生命关切。可以说,巴金的战时散文,代表了现代散文抒情形态在三四十年代的抒情转向与美学流变。巴金继承了五四以来的论理文、演说文、杂文、美文、小品文等并有所超越,其中不是知识的堆叠与理性的铺展,不仅是美的感知与爱的烘托,也不局限于简单的观看和冷峻的论析,而是置身其间的感知和诉说,有过往也有当下,有现状也有幻像,在抒情形态上隔离歇斯底里的呐喊,避开复仇情绪的肆意蔓延,以浓郁的心绪统摄冷静的控诉,最终构成一种真与善、爱与痛、悲怀与怜悯同在的抒情形式。展现了战时抒情最高的艺术水准,也代表了现代散文的历史新变,进而建构了一种战时抒情的新范式。考察巴金战时散文文本中的“无常”与“有情”,既呈现了一种现代中国散文写作的抒情形态与美学嬗变,构筑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谱系;而且映照出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史与战争史,辐射20世纪中国的文化史,更是百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的重要表征。
参考文献
⑴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三联书店2010年,第14、5页。
⑵巴金:《爱尔克的灯光》,载巴金《散文随笔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97页。
⑶冒听、庄汉新:《奔向生命之海的激流——巴金散文论》,《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⑷巴金:《废园外》,载巴金《散文随笔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38页。
⑸巴金《梦与醉》,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17年8月第1版:4-5页。
⑹巴金《梦与醉》,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48页。
⑺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⑻巴金:《贵阳短简》,载巴金《散文随笔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82页。
⑼巴金《旅途通讯》,东方出版中心, 2017年,第161页。
⑽巴金《控诉》,东方出版中心, 2017年,第36页。
⑾巴金《控诉》,东方出版中心, 2017年,第34页。
⑿巴金:《在泸县》,见《巴金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89页。
⒀巴金《散文随笔选》,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年,第185-186页。
⒁巴金《散文随笔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88页。
⒂巴金:《在泸县》,见《巴金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⒃巴金《旅途通讯》,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6、18页。
⒄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三联书店2010年,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