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来”之处“走出”:黄开发散文的行旅体验与记忆书写

云友读书会:有书友自“云”中来,不亦乐乎?云友读书会成立于2020年5月,是中国作家网在疫情中联络策划的线上跨校青年交流组织。此读书会面向热爱文学的青年,通过线上学术沙龙、读书分享、主题演讲等活动,推动青年学人的文化与学术交流,力求以文会友,激荡思想。云上时光,吾谁与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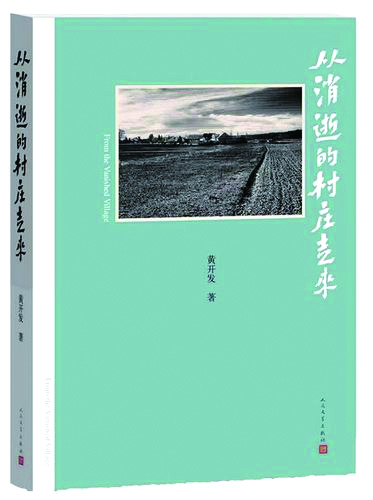
《从消逝的村庄走来》是黄开发近年来的散文结集。作者从行动和精神上重返家乡,不断回溯自我成长与乡土记忆,书写故乡叶集美好时光的同时,叙述曾经的艰苦生活际遇。那些深刻的生命体验坚定地扎根于作者的精神土壤,释放出源源不断的生命能量。
郭晓斌:黄开发的散文娓娓道来,并无虚饰,是个人生活及精神世界的真实呈现。散文中写到作者不同情境下的几次落泪,正见其内心的细腻深情。无论是写年少时的艰难困苦、求学时的忧郁多病,还是家庭生活和旅途中的缤纷色彩,情感皆力透纸背,赤子之心坦露无余,视野也远远逸出书斋之外。散文集的文风既有幽默风趣又有抒情伤感,抑或平和冲淡,因篇制宜,无不自然妥帖。
作者有着敏感精细的观察力,将生活之细节剪裁适当,从容形之于笔下。一位手法纯熟的画家创作工笔画,一笔笔皆细腻描绘。如《中年得子》,文笔简洁,细节生动,爱子的活泼可爱跃然纸上,舐犊情深,感人也至深。其实这自非偶然。作者“年少的时候做过作家梦”,即便选择从事文学研究以后,他“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对文艺女神的眷恋”。他很早之前就写作散文,如《住办公室》就是1992年的作品。这是一篇很好的散文,笔法幽默,富有情趣,1993年即被收入到一本散文选中,与李泽厚、肖复兴、斯妤等名家的散文同列。作者说这些散文是写给文艺女神的半箩筐失败的情书。真的如此吗?我暗暗地相信,这位女神是早已降临了海鶄楼的。
锁立明:《从消逝的村庄走来》中的童年场景让人仿佛回到了小学课本上的那些画面里。“棒打狍子瓢舀鱼”的物产丰富伴随着水乡风景,如今重新回味,仿佛再一次置身童年。童年的视角是最珍贵的,其感受也最为深刻。人们永远在怀念中前进,成人后所寻找的一切快乐,某种层面上都是以童年的快乐为摹本。
在《从消逝的村庄走来》里,“寻觅”是一个贯穿全书的概念。不同于单纯的乡土叙述,作者对“乡”的“追迹”同时也是对“城”的“寻觅”。在对往昔的追忆中,此刻与彼时发生交汇。这其中不乏对往事的谅解,也充满对当下境遇的思索。从农村到城市,从“乡下人”到“教授”,作者在找寻两个空间之间的平衡。这种精神之路的探索不是个案,而是这一代曾出走于农村的青年人所共有的精神困顿。作者的“乡愁”正是中国农村两次转型之后的结果。第一次是伴随着90年代经济发展的农村“进化”,如今则是在信息科技的影响下,农村的诗情画意已逐渐被“0”与“1”的代码所遮蔽。作者的叙述始终徘徊在城乡之间。每一次返乡都像是一次告别,每一次告别都又重返精神上的故乡。书名中的“走”揭示了一种人生的态度,它规定了节奏、心境和步子的大小。居住空间的不断变化,时间的层层绵延,都使个体需要检索“来路”以定义当下。人生的循环与变化本该如此。回到故乡的任何人,都含有几分赤裸的色彩,这种本真的“底色”溶解于血液骨髓之中。在回望一切的同时,也在和过去和解,作者以最直白的叙述将自己的内心呈现在读者面前。高考复读、结婚生子、城市生活,人生的步调由急到缓,青年时的慌乱与彷徨已化作今日对人生新的达观。“消逝”是此书的主题词,某种程度上,村庄的“消逝”意味着个体的“消逝”,对那些存在于记忆中的符号和印记的重新探寻,是对村庄的一次挖掘,也是对个体的一次全新建构。
刘 璐:在作者的精神土壤里,“史河”无疑是乡愁的具象与化身。史河作为叶集古老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既是“我”众多童年乐事的重要载体,也是家里经济来源的重要工具,更是“我”精神成长决定性瞬间的重要见证者。《史河上的小木排》详细记述了那次进山贩树的经历,史河上漂流遭遇的场景逼迫“我”思考未来的出路,“我”决心告别祖父辈们生活过的土地,去追寻一种有尊严、有价值的人生,这是“我在社会现实中所接受的人生哲学第一课”。多年后现实的史河难逃工业化的侵袭,河水变黑,鱼虾绝迹,作者面对史河和村庄隐退及至消亡的阵痛,行诸笔端,不能自已。这也让记忆中的史河永远定格,成为个体永恒的精神家园。
如果说现实中村庄的一切都在被城市工业化浪潮裹挟,那么作者抵抗失望、守护精神家园的方式便是铭记每一份珍贵的情感。作者以朴素细腻的笔触记录下给予他无限情感滋养的人们,比如外祖母、母亲、父亲、毛桠、果果、大舅、妹妹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作者散文的叙述主体,每个人物都有坚韧的精神以及那个同样坚韧的“我”,铸就了作者散文的灵魂。作者没有走抒情散文的路子,而是把深厚的情感融入在生活的细节和日常的事情中,就像《叶集》里写到父亲母亲送“我”上大学的场景,尽管老车站已消失,父母渐渐老去,但是彼此内心的情感可以跨越时空变迁,在历史和空间的缝隙中顽强生长。我想,作者以写作的方式郑重地向记忆中的故乡、亲人致敬,并带着坚韧的精神继续前行,走过一程又一程。
刘 佳:提起欧洲的西北部,我会首先想到世界地图的左上角,地球仪的顶端,破碎岛屿的漫漫长夜,如今脑海里新添了一些更鲜明的色块,由这本书里的几篇游记点染:五月狂欢节的橘黄、十月奥尔堡的橙红、北欧民谣、层叠冰山……我也在和作者一起走出习惯的空间。
也许是语言系统的切换钝化了听和说的反应,更可能是作者擅长调用视觉切换视野,令人觉得沉静的地点不只有北欧。德国呼啸的高速公路上,司机的怒吼,冰雹的骤降,都被棉絮状的白云隔住了音,不太顺利的自驾经历即将结束,除了遍地的残枝败叶,作者还能看见远处风车对金黄麦田的守望。作者的视野不只集中于自然景观,还注视着丹麦居民的离婚现象、韩国女生的化妆意识,还有儿子在养兔子的时候对生命的繁衍产生好奇,作者对因纽特女孩去不去大城市发出疑问,一些关于来处和归途的思考,在每代人这里的叩问都如此响亮。
梁鸿威:从奥登堡的秋到格陵兰的冬,从首尔的一场比赛到茨中的一座教堂,空间被凝缩为雕塑的故事,故事成为时间的艺术。走出“习惯”,如同走出梦幻,灵性的人文观照着这本学者的散文之书。书中,游离、而后记录,直至汇聚成为了不同种族信仰或亲友气质的契合,也如书中的文脉,在古典和现代的重叠风格中同样也促进某种印象或象征的黏合。恰如作者说,在视觉文化盛行的时代,他在对自然的“执着”中减少“我执”。或许,在中国邻居中觅见遥远的民族精神,在地球的另一边审度国家民族的意识,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他的执念的“脱落”,也会化作诗人冯至所谓的“青山脉脉”吧。
如果说作者已给了我们多封信,让我们诉诸理性而走出惯性牵引的“空间”,那么,在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一场狂欢节“礼券”的赠送下,读者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对这场狂欢节的感性迷恋,这是书中最令人身临其境的情节之一。它的光芒浸染在文本之间,将会同众多山上的日出日落一样,建构出有别于罗兰·巴特的“文之悦”。
苗 帅:就文学气质来说,《从消逝的村庄走来》是一部水中之书,《走出习惯的空间》是一部山中之书。《走来》始自对“水”的追忆,首篇《一条小河、一条大河与两个村庄》以村庄南面的两口水塘为回忆的端点,延伸向“水塘两边通着的两条水沟”,“沿水沟向东三百米有一条小河”,“小河再下二里路,就流进了后面要说的大河”。书中弥漫的对于失落乡土的哀悼心绪,也往往受到水流的触发。如果说这样的伤叹来自作者个人的今昔之感,那么当他携子返乡,目睹小河变成死水、发现“故乡已经没有一片可供游泳的自然水域”而对儿子心怀歉疚时,则负载了更多沉重的文明省思。《走出》则开始于作者童年时遥望远山的遐想:“我倚门而望,远处天际线上大别山峰峦叠嶂。大山那边是什么地方呢?”走出村庄,成年后的作者开始自由地穿行藏北高原、近观格陵兰冰山、涉足无数山峰,以双脚探索陌生之域。
然而,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不同,就两部书的思想气质而言,无论取“知者动,仁者静”“知者知人,仁者爱人”还是“智者知己,仁者爱己”之义,水性的《走来》都更像一部仁者之书,山性的《走出》则纯然一部智者之书。《走来》向内在的自我探源,是写给昨日之我与昔日故人的秋日家信,写信的人并非一个现代知识精英,而是在城市侵蚀农村的进程中被“抛入时代”的无数游子中的一个。不同于《走来》中那个仿佛一脚踩在柏油路上、一脚踏进黑泥土里迷惘嗟叹的离乡者,《走出》的书写者是个脚步坚定的行路人和对世界、他人、自我多有洞见的智者。书中对外部世界观察描摹的细致、对不同社会文化差异的思考、在旅程和生活中对人心之微的体察与理解以及对自我认知不加矫饰的表达,都呈现出一种敞开式的智者气质。
追念逝水和憧憬远方是人类心灵中极具张力的两种基本情感,它们的共生性基于一种“超越当下”的欲求,“此刻”之所以常常使人有逃逸的念头,并非因其庸常,就像《走来》中充满日常叙事,而趣味恰在日常之中。“此刻”的真正问题在于虚假的充盈,它借用“真实”的名义与“现实”的形式紧紧包裹“伪”之内核。尤其在加速时代,人与人的隔膜、人与自然的敌对关系,使得“伪”的膨胀也日益加速。在这种境况中,仁者将对真的追寻寄情于昔日,智者则寄意于远方,二者在“求真”处汇流,并以修辞立诚的文学驱力持续向前流动……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2021年11月24日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