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1年第9期|韩东:箱子或旧爱(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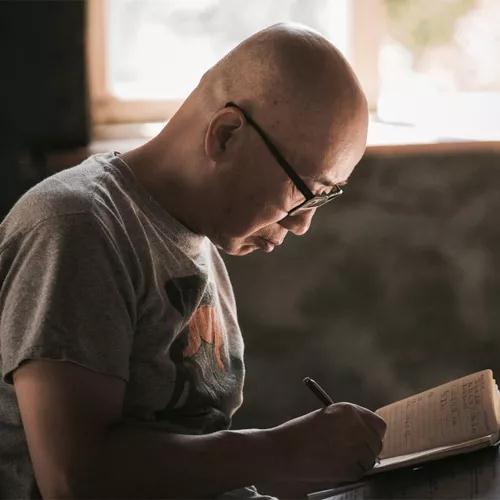
韩东:一九六一年生,小说家、诗人,“第三代诗歌”标志性人物,“新状态小说”代表。著有诗集、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随笔言论集等四十余本,导演电影、话剧各一部。
箱子或旧爱(节选)
韩 东
我和崔茜谈了七年恋爱,从她读大三的时候开始谈,两年后崔茜本科毕业。当时我们的感觉都不错,意犹未尽,这样崔茜考了所在学校的研究生,留在了群都。我们继续恋爱,这又是三年。崔茜研究生毕业,再次面临去留问题。也不是说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也许是年龄关系,到了真正抉择的当口。如果崔茜留下,我们势必就得结婚,但两个人都没有结婚的感觉,心理上没准备好。同样不约而同,当崔茜说她可以回西塞一边工作一边找机会出国时,我并没有提出异议。崔茜的父母在西塞颇有一点儿势力,取道西塞肯定比在群都要方便。崔茜在西塞待了两年,果然走成了,先去新西兰,目的地是美国或者欧洲。这样算下来,崔茜本科两年,研究生三年,回西塞两年,我们差不多在一起七年。
崔茜在西塞的时候,我们是恋人关系,实际上没有待在一起。两年间她来过群都两次,一次是办事,一次是最后道别。后面那次其实也是办事,顺便和我道别。崔茜奶奶病逝,父母和姐姐回老家奔丧,崔茜一人留守西塞,她让我过去陪她几天,我也没有去。何必呢?我觉得在此阶段没有必要再增进彼此的感情了,渐行渐远挺好的。我们的确是准备相忘于江湖的。
我们会写信,大概三天一封,也是从每天一封演变来的。收到崔茜来信的当天我就会回信,信要走三天,她给我回信时我正好收到她上一封信,如此错开,平均是三天一封。信的内容不免例行公事,我们已经过了肉麻阶段,也就是谈几句彼此的现状,她如何上班、我在写什么专栏之类。再就是聊聊以前认识的朋友熟人。
我们不通电话。崔茜家的电话我不方便打,因为两人的关系是瞒着她父母的。我的电话崔茜也很少打,大概是出于某种平衡需要,互不打电话肯定比一个人总是打给另一个人更加公平。
或许她父母能猜到崔茜在群都有男朋友,但具体是谁应该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始终处于地下状态。当然,我这头对家人朋友毫无隐瞒,也隐瞒不了。崔茜在群都五年,我们总是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崔茜不仅在我父母家吃过饭,我们还一起在那儿过过夜。也不能算过夜吧,大年三十守岁,过了凌晨十二点我们才离开的。
那年崔茜考研究生,寒假借故复习没有回西塞。
应该说我们的第一阶段(崔茜本科)相处还是很不错的。崔茜的长相无可挑剔,可说是他们学校的校花,或者是校花级别,又那么懂事、有教养。大家都说我们是男才女貌,天生的一对。无论去什么地方我都会叫上崔茜,她只要没课也一定欣然前往。其实两年以后我们也是这样的,一直如此,崔茜在群都的五年都如此,没有大的变化。换句话说,我们恋爱的模式相当稳定,可以说是恒定,有我的地方必然有崔茜。如果某次聚会我一个人去了,身边没有崔茜,大家肯定会问:“崔茜呢?”这就像我去任何地方都会背一个双肩包,偶尔没背,对方肯定要问:“你的包呢?”没背包我自己都很不习惯。
这是在“公共场合”,私下里也一样,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甚至没拌过嘴。崔茜性情温和,很照顾我的情绪,也许有一点儿冷淡吧,我的意思是她不是那种喜欢表达或者善于表达的人。我不一样,脾气不好,容易激动,和崔茜在一起说实话有那么一点儿压抑。当然,根本原因还是上面说的恒定,一成不变。她每天上完课就会来找我,在我的住处继续学习,复习课堂笔记或者写作业,要不我们就一同前往某处参加朋友聚会。日子就这么过着。到了寒暑假,崔茜肯定回西塞(复习考研那次除外),她一走我突然就感觉到了自由,连吹过来的风都不一样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问题,崔茜一离开我才感到了缺失,不是她不在身边缺失了什么,而是,她在我身边缺失了什么。我会倒回去体会一些事情。
比如有一次她临时有事回西塞,告诉我第二天赶回学校。我思考很久,最后还是拗不过自己,给前女友打了一个电话,约她吃饭。前女友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就像她一直坐在电话边上,在等这个电话),我反倒踌躇起来。想来想去,我给童伟也打了一个电话,约他吃饭。因此当童伟走进我住处附近的那家路边餐馆时,看见我和一个并非崔茜的女人在一起,他自然非常吃惊,嘴巴都合不上了。童伟也没有机会问我,“崔茜呢?”我觉得让这哥们吃惊一下也是挺有意思的。那天我们喝了两瓶葡萄酒。饭后我提议去我的住处坐坐,喝杯茶,前女友同样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并且说:“你现在过得到底怎么样呀,我倒是要看看!”
她熟门熟路,走在前面,我和童伟故意落后。童伟这才有机会问:“崔茜呢?”我简单说了一下,童伟说:“那我就不上楼了,不打搅了。”他的意思是我和前女友有事要办,他就不当电灯泡了。其实当时我还在犹豫,没有想清楚,因此死拉活拽非让童伟上去喝茶不可。
请注意这个关键点,我是因为犹豫或者踌躇,没想清楚,可事后童伟一口咬定我老谋深算,并且到处宣扬我的第六感太好了,难怪能吃上自由撰稿人这碗饭。(有关系吗?)看起来是夸我,其实是在骂我。我真的不是有什么第六感,我觉得崔茜那会儿人已经在西塞家里了。
崔茜没有走成,因为上系里的机房耽误了,赶到火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大概家里也没什么大事,因此崔茜决定第二天再走。她直接从车站来了我的住处,开门进去想给我一个惊喜。我不在,崔茜就烧水洗了一个头,我们进来的时候她的头发还湿漉漉地滴水呢。那天真是惊险,幸亏了童伟,如果他没跟我们上楼我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还在楼梯上,我就发现有异样。我住的那栋楼很破旧,楼道里没有灯,可竟然有灯光从我那套房子的门板缝里泻出。难道我忘记关灯了?但离开的时候天色很亮,我没有开灯又谈何关灯?正这么想的时候,前女友已经走到了门边,我赶紧挤到她前面,掏出钥匙开门。童伟这时也赶了上来,不由分说拉住前女友的胳膊……
见我们一拥而入崔茜有些吃惊,童伟马上介绍前女友,他说:“这是我女朋友,童伟的女朋友。”崔茜没有往其他方面想,也就相信了。实际上童伟的破绽很大,过于急切了,哪儿有一见面就这么介绍的?崔茜在这些地方一向缺乏敏感,对我尤其放心,所以我才会说她有一点儿冷淡。我们在一起七年,崔茜从来没有因为其他女人表现出嫉妒,对我从无怀疑,哪怕是一种纯精神的游戏呢。
我说的精神游戏其实就是恋爱游戏,彼此都有一两个假想中的情敌,怀疑来怀疑去,嫉妒来嫉妒去,但又都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崔茜去厨房烧开水泡茶,之后四个人就坐下来喝茶。童伟故意挨前女友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不时地拉过对方的手搓揉抚摸;前女友是老江湖,非常配合。两人卿卿我我的,真的很过分,不是人前亲热很过分,是表演得太过了,差一点儿就穿帮了。我自然没有说前女友是我的前女友、现在是童伟的女朋友这类画蛇添足的话。
聊了点儿什么不记得了,总之,局面安定后不久,童伟和前女友就站起身来告辞,刚泡的茶也没有喝。他们告辞的速度非常快,这也是破绽。整个过程说起来就是:童伟介绍前女友是他女朋友,然后坐下表演二者的关系,以证明的确是他女朋友;见崔茜没有异议,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火急火燎地起身告辞。当然,他俩也不是那种顾前不顾后的人,走的时候没忘记一个揽着另一个的腰,另一个侧身贴靠,就这么亲亲热热地下了楼梯。我们目送的显然是一对情侣的背影,并且是处于热恋中的情侣。至于出了这栋楼两人是如何走的,就不得而知了。
说来奇怪,当我有了大把自由,比如崔茜回西塞那两年,我反倒不那么急切了。她回西塞的两年,我一个人生活,基本上没有找过其他女人。可以找,也有机会,但就是懒得找。可能是牵挂西塞那头吧。我和崔茜的事情没有了结,就不能轻装上阵重新开始。我自忖自己还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反倒是和崔茜整天纠缠在一起的日子,空气令人窒息,所以才发生了我约会前女友的事。那件事发生在崔茜读研究生的那几年里,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
除了我觉得崔茜不够热情,我们的相处就没有不愉快了。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小事,小到不值一提,那也是因为我比较敏感吧。比如有一次我和崔茜在楼下的面条摊上吃面条,我先吃完,问崔茜有没有餐巾纸——女孩一般都会随身携带餐巾纸的,崔茜头都没有抬就说:“没有。”然后崔茜吃完了,却极其自然地拿出一张餐巾纸擦了嘴。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当时我什么都没有说,但非常生气,我觉得崔茜太自私了,一张餐巾纸还要留着给自己用。她完全可以一撕两半,两个人都可以用的。也有可能崔茜的确是无意识,觉得自己没带餐巾纸,等她吃完了,习惯性地一摸,身上正好有一张餐巾纸,就用来擦嘴了。她肯定忘记了我向她要过餐巾纸。实际上她用过的餐巾纸我再擦一下也是可以的,但崔茜擦完嘴就把餐巾纸窝成一团扔进面条摊旁边的垃圾桶里了。
就是这么一件事,太小,说起来似乎我小肚鸡肠。但我的确认为崔茜很自私,也可能不是自私是冷淡吧,根本上是冷淡,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对我的整个用心是冷淡的。
崔茜去新西兰留学,有手续要在群都办,我们顺便见面道别。她甚至连我的住处都没有去。崔茜办完事已经是下午了,还要赶回西塞回家吃晚饭,回程的车票她也已经买好了,留给我的时间大概也就三个小时。我们约好在钟楼见面,之后逛了一下那一片的商店,就往火车站一路走过去。
在一家商店,我买了一个眼镜盒送给崔茜,作为临别纪念。非常一般的眼镜盒,也是因为那会儿崔茜又戴眼镜了。她本来是戴眼镜的,但在群都的那些年里,在我的要求下崔茜开始戴隐形眼镜。对她来说,戴什么眼镜或者戴不戴眼镜好像都无所谓,而我觉得崔茜戴眼镜和不戴眼镜(包括戴隐形眼镜)简直就是两个人。虽然崔茜戴眼镜(有框架的)仍然很漂亮,但不戴眼镜就不光是一个漂亮的问题了,可说是光彩夺目。崔茜由于眼睛过敏,后来隐形眼镜也戴不住了(流泪不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干脆就不戴眼镜了,无论是框架眼镜还是隐形眼镜。崔茜总是瞪着一双本来就很大的眼睛,努力看向眼前的一切,又肯定看不清楚,那种懵懂和专注兼而有之的神情实在令人难以言表。大家都说崔茜就像一个洋娃娃,说我带着一个洋娃娃到处炫耀。崔茜回西塞后,没有了我的监督,可能也因为上班需要吧,她又戴回了框架眼镜。
然后就是走路,一路往火车站而去。我记得途中有一道很长的围墙,刚刚粉刷过,白得晃眼,我们沿着那道围墙走了很久。没有坐公交车,因为还有时间,但如果去我的住处可能就没有时间了。我似乎也提了一下:“要不要去我住的地方待会儿?”崔茜说:“太仓促了,等我以后回国吧。”我又说:“你的箱子还在我那儿呢,要不要取走?”
两年前,崔茜离开群都的时候,放了一只箱子在我住处,说是以后会回来取的。那只箱子我打开看过,都是她的私人物品,包括一些衣物、布料、课本、洋娃娃以及我写给她的信。我们刚谈恋爱那会儿,虽然在同一个城市里,天天见面,但还是会写信,每天一封。信的内容也不乏激情,比较肉麻,和她回西塞以后我们的通信不一样。那些我写给她的信放在一个纸盒子里,纸盒子放在箱子里,都留在我这儿了。此外还有崔茜的一本日记。
无论是那些信还是崔茜的日记我都没有看(对那些信而言是复习,我没有复习),她没有带回西塞显然是怕她父母看见,寄存在我这里是对我的信任,也说明我们的关系还在。崔茜一再强调她会回来取箱子的。对了,还有照片,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拍的照片,崔茜也都留下了。当然经过了一番挑拣,我的单人照和我们的合影留下了,她的单人照都取走了……
我问崔茜要不要把箱子取走,是一种试探吧,但也可能是一个借口,想让她去我住处待一下,毕竟这是最后的道别。我有点儿伤感,思路似乎不是很清楚。
如果这是我们的结束,崔茜理应取走她全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试探,想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可崔茜说,等她以后回国取,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箱子她就不用回来取了,成了一家人,放在自己家的东西回来取是不成立的。如果说非得回来取不可,就说明我们肯定会结束,也许不是现在……总之崔茜的回答令人费解,也充满了伤感,至少我听上去是这样。
我的确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就这么内心纠结以至有点儿麻木地把崔茜送到了火车站,买了站台票把她送上了火车。我们甚至都没有拥抱一下。我是想拥抱她的,在她耳边说点儿什么,但觉得拥抱太生疏了,就像在表演。可不拥抱总该亲热吧,由于没有时间去我的住处,亲热也没有机会。当众吻别更难以设想……正患得患失,火车进站了,崔茜回头看了我一眼就进了车厢。从她镜片后面闪烁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和我一样,心有不甘,也许刚才她也在犹豫,要不要抱我一下。终究谁也没有抱谁,手都没有碰一下她就离开群都回西塞了。这次见面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尴尬,实在尴尬,非常尴尬。你说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又是什么意义上的分别?恋人,朋友,熟人?暂时别过,又一次分别,还是永诀?一时半会儿我无法正确理解。
回西塞后不到一个月,崔茜就去新西兰了。在她去新西兰之前还在西塞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依然通信,三天一封,日子就像回到了道别以前,压根儿就不存在她要去新西兰这回事了。谁也没有再提。然后,超过三天没有收到她的信,到第五天的时候我暗想,崔茜大概已经走了。半个多月后,我又收到了崔茜的信,用的是那种红蓝条边的航空信封,寄件人的地址也是用英文写的,显然她人已经到新西兰了。这封信崔茜写得很长,密密麻麻写满了两页信纸的正反面。她初来乍到,凡事新鲜,加之一个人孤悬海外不免孤单,就多写了一些。崔茜甚至对比了奥克兰(她前往的城市)和西塞以至群都的副食品价格。崔茜说,一周以前她就到了,直到写这封信才初步安顿下来。
为防止我回信写错地址,崔茜特地将她的地址打印了,也是两大页,每页上有二十个同样的地址。崔茜说,我给她写信的时候,只要裁下一条地址,贴在信封上就可以了。她之所以这么做,是考虑到我的英语水平,以确保她的地址准确无误,我的信能正确寄达。一页纸上二十条地址,两页纸就是四十条,可供我给她写四十封信。“这些地址用完了,”崔茜写道,“我会再打印了给你。”
我只裁下一条地址,写了一封信,其余的地址都没有用。
崔茜写这封信是去了新西兰一周后,我收到距她上一封寄自西塞的信是半个月。也就是说,从奥克兰寄一封信到群都需要一个星期,以后我们的通信频率就会变成一周一封,和崔茜在西塞的时候也差不了太多。三天一封信和一周一封信有什么区别?天数是多了几天,但模式不变,不过改变了一下节奏,只是量变而没有质变。我本来想崔茜出国是一个契机,我们的关系会有一个全新的变化,现在看来——如果按照她的设想,还是一成不变。如此前景真是令人绝望。这种绝望或者压力反倒激起了我的“求生欲”,义无反顾地给崔茜写了最后一封信。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正式提出分手,诀别、断交。信也不长,我斟词酌句,几易其稿,大致内容就是两人没有必要再耗着了,目前就客观情况而论,彼此的人生轨迹已经岔开。崔茜取道新西兰,将来不是去美国就是去欧洲,而我这辈子是不会出国的——出去也是游览观光或者参加有关的文化活动,绝不会是去国外生活。在心理上我们有必要适应这种有关未来的动向,不可一厢情愿……总之我挖空了心思,话说得冠冕堂皇,我想即使崔茜不乐意也无法反驳。最后我也说了,这种事总得有人提出来,作为一个男人我有必要主动,就像当年也是我主动追求的她,现在分手亦应该如此。我承担所有的责任,希望她多加保重……
对了,在这封信里我特地提到了箱子,我说我会为她保存好的,等将来她回国的时候取。“回来取”变得名副其实,不再暧昧有歧义,那是她的东西,我帮她保存,有朝一日从我这里取走,因为已经是两家人了,天经地义。她不是把东西放在将来有可能是自己家的房子里。“回来取”变得必要,就是不回来取,也是没来取,落下了、遗忘了,而不是放在自己的家里没有必要取。寄完给崔茜的信,我再一次打开崔茜留下的箱子,把她寄自新西兰的信以及两页为我打印的她的地址放了进去;关上箱子,我们的事就告一段落了,除了一件事,她回来取箱子或者不回来取箱子。取箱子的事在未来很可能不会发生,总之已经堕入到虚无缥缈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只会更加虚无缥缈。
我的感觉还行,除了有点儿牵挂箱子的事就没有什么了。但很快,那箱子也被我置于了脑后。的确有一种轻松之感,此外就是虚无缥缈,过分轻松了,不那么踏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愉悦。后来我经过分析,明白自己是在等崔茜的回信(我的潜意识),不是说盼望她写信给我,我是在等她收到我那封断交信后的答复。分手毕竟是两个人的事,一个人提出,另一个人理应有所回应,比如说同意分手,或者不同意分手。同意分手就不说了;不同意分手也是一种回答,如果我不同意对方的不同意,从此就可以置之不理。总之应该两个人签字画押,文件才能生效,哪怕一个人签的是“同意”,另一个人签的是“不同意”呢。我没着没落的心情大概与此有关吧。至于说到痛苦或者后悔,那肯定是没有的,直到一个月以后。
崔茜的回答果然来了,她给我回了一封信。崔茜的信很简短,但可以说是字字血泪,这也不是形容。崔茜说她收到我的信后哭了一个星期,什么事也干不了;说像她这样的一个人爱上一个人是不容易的,但尊重我的决定。最后崔茜祝我一切都好,让我多加保重。就是这么一封信,让我不再淡定,真没想到她的反应会这么大。于是我就想,是不是自己做错了?就算分手的提议没有错,如此操之过急、急不可待是不是错了?那可是崔茜去新西兰以后收到的我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就是断交。想起她为我准备的那四十条地址,我觉得自己太不够意思了,做得太差劲了。崔茜孤身一人、新来乍到,原本是想从她的爱人也就是我那里获得某种精神支持的……
我没有再回信给崔茜。如果那么做,我们不就又回到以前了?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不可能再回信解释,我的心情糟透了,就像我杀了人,或者像一个肇事司机撞倒了人,因为这样那样一些原因比如正在执行拯救人类的任务,还不能施救,任对方倒在血泊中挣扎呻吟……
收到崔茜那封信的当天,我横穿马路,真的差点儿被一辆车撞了。不是汽车,是自行车,我被一辆自行车的车把带到,自行车倒地,骑车的小伙子跳起来要跟我打架。后来也没有打起来,大概是因为当时我的面目过于狰狞可怕,小伙子改了主意,退却了。他扶起自行车一路骂骂咧咧地推着走了。我自然没有回骂,甚至没有说一个字,道歉也没有说,只是用目光逼视对方,把小伙子逼退了。也有一些骑车的停下来想看热闹,没有看成,就又骑上走了。他们无不绕道(绕我)而行,被我眼睛的余光捕捉住。就这么我在来往不息的自行车车流中站了六七分钟,像根木头或者神经病似的。终于心情有所平复,听见车铃声了,响成一片,不知道什么时候天已经黑了,树丛后面透露出沿街商店里刺眼的灯光。
站在那儿的时候我在想,我完全可以把事情办得缓和一些的,没有必要这么突如其来、不由分说。完全可以给崔茜多写几封信,逐渐拉长通信频率,甚至也无必要明确提分手。一周一封信变成一月一封,再变成半年一封、一年一封……我又没有新交女朋友,又不急于再谈恋爱,干吗这么着急呢?七年我都挺过来了,还在乎这一时半会儿吗?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1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