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上半年当代长篇观察
“当代长篇观察”是《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增设的新栏目,密切关注文学现场与出版动态,摘录关于最新长篇的精彩评点。以下内容选自《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1—3期,所推介的长篇小说均为上半年发表或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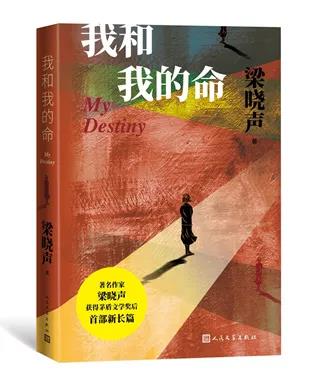
《我和我的命》,梁晓声 著
《当代》2021年第1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
王春林评《我和我的命》
作为梁晓声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仍然秉承作家一贯的平民立场,在把个人命运与城市发展以及时代特质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成功地书写表达以移民方式进入城市的早期深圳人真实的人生和精神轨迹,可以说是一部带有明显成长小说意味的社会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一位出生在贵州山区,后来进入城市打拼的80后女青年。在其人生打拼的过程中,既找到了爱情,也收获了友情,更感受到了真切无比的亲情。正如小说标题所明确标示的那样,作家从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立场出发,通过“我”和好友李娟的奋斗故事,深度思考表现个人与命运的深度纠葛。读来既能够让读者心生感动,更可以引发读者对人生的深入思考。
——选自“探照灯好书”微信号

《有生》,胡学文 著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第1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版
谢有顺评《有生》
《有生》厚重、扎实、雄心勃勃。具独创意义的伞状结构,百年家族史的曲折繁复,祖奶形象的异样光彩,乔大梅的承担与反抗,共同讲述了历史苦难中个体的泪水和坚忍。既然死是如此容易,那就用生育来反抗死亡;既然困境才是人生的常态,那就告别那些浅薄的乐观,以更有韧性、更有质量的活着来为生存安魂。胡学文创造了自己的“宋庄”,也为另一个乡土中国写下了灿烂、悲怆的叹词。
——选自《南方周末》2020年度十大好书评语,2021年1月21日《南方周末》
何同彬评《有生》(胡学文)
胡学文一旦写到故乡,那里作为一个完整的图景和世界就会显现出来,人、风景、营生、表情乃至气息,用他的话说:几乎不需要想象,是自然而然的呈现。正是这样一种最朴素、本真的“自动”“自然”,让《有生》的乡土世界真正触及了坝上、北中国的“根”,也给读者带来了一个长篇小说独有的真实、丰富又浩瀚无边的文学世界。在《有生》中我们能看到上百年时间跨度里的数十个生动的人物,他们不是“农民”,也不是“底层人物”,胡学文拒绝把他们符号化、阶层化(甚至只是保留了最低限度的历史化),而是用自己全部的感知、理解、同情和尊重,把所有人物还原为文学意义上的“自然人”。环绕着这些人的那些植物、动物、昆虫、风景,以及人们赖以谋生的那些手艺、职业,赋予他们地方性的风俗、风物、民间文化……所有与他们的“道德、理智、灵性生命”有关的全部内容,都经由胡学文沉稳又灵动的叙事,结构为《有生》的壮阔和浩瀚。
——选自《〈有生〉与长篇小说的文体“尊严”》,《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群山呼啸》,季宇 著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第1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
陈振华评《群山呼啸》
长篇小说《群山呼啸》书写从晚清到抗战半个多世纪大别山地区革命历史进程的波诡云谲和艰难复杂。小说的结构没有采用线性的情节故事,而是采用以人物为中心的团块状叙事。一方面凸显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带动了故事,“爷爷”贺文贤和“大伯”贺廷勇两代革命者最后在抗战的时代形势下历史地合在了一起,完成了精神信仰的汇聚。另一方面,章节并非是按照时间顺序线性排列的,而是随着人物故事和情节的变化交叉、往复、重叠或有意并置,这样的非线性叙事赋予了文本比较大的叙述自由度,并且每个章节的故事留有悬念或伏笔,其草蛇灰线在通读全文后才能意脉贯通。与此同时,小说采用了贺家第四代子孙“我”的叙述视角,通过“我”的讲述和追溯将革命年代的信仰、理想、人物、故事和当今时代产生意义关联,从而让历史的正当性、复杂性、苦难性、艰巨性具有了重要的现实认知和启迪的意义。
——选自《多重意蕴“革命叙事”的诗学建构》,2021年3月16日《北京晚报》

《洛城花落》,周大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孟繁华评《洛城花落》
《洛城花落》是一部极具现实感和时代性的小说。周大新将长篇小说封笔之作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最深处,也是最隐秘的领域,以奇特的构思走向私密生活和私人情感,不仅使小说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同时隐含了现代人在日常生活和情感领域的危机,探讨了这一领域不可穷尽的神秘性和多样性。袁幽岚和雄壬慎的婚姻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青年婚姻的某种状况。因此,《洛城花落》是一次大胆的实验和探险。它探讨的情感、性爱、婚姻形式、门户、相貌、物质生活与情感生活等等,确实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小说中作为历史研究学者、也是当事人的雄壬慎,毕业后即确定个人研究题目“离婚史”,在小说中是一个隐喻,也是小说走向的暗示。具有仿真意义的“法庭”,由于不同身份人物的参与,也表达了不同阶层或人群的婚姻价值观。男女的聚合史和分离史是永恒的主题。周大新对这一主题意犹未尽,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杰出作家对文学、对小说理解的深度。他对这一领域的时代性、新知识、新困境的发掘,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无论人在情感领域遭遇了怎样的新问题,他坚信人性的柔软犹在,人性的善永在。这就是周大新对“永恒主题”变与不变的理解。
——选自《新时代“永恒主题”的变与不变》,2021年3月17日《文艺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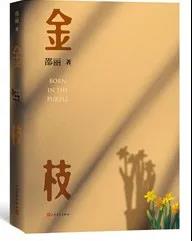
《金枝》,邵丽 著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第2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
陈晓明评《金枝》
“金枝”作为书名显然富有诗意,似乎也暗示着某种鲜妍美好。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书名背后却晃动着那么多的阴影和苦痛。谁是“金枝玉叶”?谁的“金枝玉叶”?这部小说写了一大群人物,写了一群女性,至少三代女性。同出于周家,但是她们的命运、性格如此迥异。
诗人奥登曾说:“一本书具有文学价值的标志之一是,它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阅读。”我想《金枝》是这样一本书,我们可以从中读出现代历史巨变给传统家庭伦理留下的伤痕;可以看到以“金枝玉叶”之名掩盖的苦痛艰难的女性生活之书;可以读出一位知识女性如何认识父辈的历史;可以看到现代社会进程中城乡的差别,它也有可能搭建自强不息的未来之桥。这部作品让分崩离析的往事富有诗意,又如同挽歌,歌咏那消逝的历史和乡村。
——选自《谁是金枝玉叶?》,2021年5月18日《新民晚报》

《五湖四海》,石钟山 著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4期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2月版
潘凯雄评《五湖四海》
《五湖四海》的结构与叙述并不复杂,无非就是一个出自农家且还是一个有手艺活的农家军人刘天右成长的故事。刘家的手艺活儿用老话讲就是吹鼓手,得到父亲真传的刘天右也因吹得一口好唢呐而经历了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复盘刘天右一次次化险为夷的过程,两个鲜明的共同点凸显出来:一是他自己身上那股永不服输、绝不放弃的执着劲儿,二是一路总有“贵人”的适时出手扶持,而这些“贵人”又都还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即战友。这些“战友”有的来自同一支部队、同一单位,有的则是素不相识的转业军人。这些军人形象出现在石钟山笔下一点也不奇怪,这是他的擅长,因为他终究也是军人。在我看来,我们当下的文学方阵中,站立着这样一群阳刚、坚韧的人物群像有着十分重要的审美意义和现实价值,这就是《五湖四海》所具备的价值。
——选自《终究还是军人》,2021年3月11日《光明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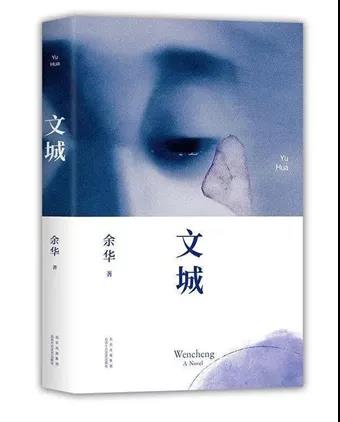
《文城》,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版
杨庆祥评《文城》
小说家的思想、知识和观念不应该溢出小说这一有机体本身,昆德拉有一个比较饶舌的解释“小说只能发现小说所能发现的。”余华对此有清醒的自觉,《文城》的故事、人物和行动构成了一个圆融的有机体,这一有机体折射出丰富多元的主题。首先是“信”,既包括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也同时包括对某一种事物的信念,对某一种情感和理想的执着。《文城》其实是由几组不同的信任关系构成的。林祥福和陈永良、林祥福和纪小美、纪小美和沈阿强……正如《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和他的孩子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的亲密程度却超越了血缘,《文城》中的这几组亲密关系同样也建立在非血缘性的信任关系上,这种“信”既是文化的养成也是人类的本性。与“信”相关的是“义”。小说中主要人物行动的逻辑都在于“义”,讲义气,有情有义。除了主要人物是如此行动以外,小说中的次要人物甚至是反面人物,都遵循这一行动的原则,比如土匪,有情有义的土匪最后得到了善终和尊敬,而无情无义的土匪则只能曝尸街头,受众人唾弃。这一情义原则与上文提到的“信”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但余华没有浅薄地给这些原则冠以高头讲章,小说没有任何关于情义、信任的说教,而是通过那些小人物、底层民间的人物来静默地呈现这一文化血脉是怎样地流淌在我们先民的生活和生命之中。有朋友在读到小说中“独耳民团”保卫战之后不禁潸然泪下,情义由此穿透了历史,直接对当下构成了一个提问。在这个意义上,《文城》的所叙时间固然是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但因为有了这种对普遍人性的深刻描摹,它又直指当下的时刻,它并非固态静止的历史演义,而是以镜像和幽灵的形式活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选自《〈文城〉的文化想象和历史曲线》,2021年3月18日《文学报》

《春山谣》,张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
曾念长评《春山谣》
《春山谣》借回忆者视角讲述了一段青春故事,借儿童视角引出了一段青春歌谣,又借人类学视角将一段青春岁月还原成广阔的生活场景。三种视角相互交织,构建了一部完整的青春主题小说。我们不妨回到故事起点——春山小学的孩子们扭着秧歌舞,迎接上海知青以部队的整齐阵容出现在村路口。这个秧歌舞迎知青的场景,既是儿童视角与知青视角的最初交集,也是人类学视角的第一次试探发微,将一派热烈的民间狂欢引向历史深处的革命记忆。众生不可避免卷入时代洪流之中,《春山谣》却以一种平静笔调呈现出每一个人的细碎生活和成长体验。
——选自《一段青春三种视角》,2021年5月17日《文艺报》

《民谣》,王尧 著
译林出版社2021年4月版
程德培评《民谣》
《民谣》聚焦一个少年短短几年的成长片断,在漫长的书写过程中,故事的跌宕起伏早已化为历史的烟云,留下的只是琐碎的细节和无法复原的碎片。不断流失又不断修复的感受,不断遗忘又不断被想象所修正的记忆,是小说的叙事依托。少年的故乡与故乡的少年来回于村镇,出入于队史、革命史与家族史,落地的则是个人的成长教育史。而准自传的借用,双重“我”的叙述,幻想和梦魇的介入,杂篇、外篇的补充和镶嵌插入形成了层层叠架的结构,则成就了作品的完整性。《民谣》说了太多的东西,同时又让我们听到了没有说出的话;《民谣》之中有着太多的秘密,有些秘密在阅读中会解密,有些秘密则永远是秘密并吸引着我们。
——选自“收获”微信号

《受命》,止庵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孙郁评《受命》
止庵写长篇小说,完全出人意料。《受命》酝酿了三十年,让人恍然觉出,大半生笔墨的挥洒,都是为此书准备的序曲。先前写的文章,都是谈别人的学术与文本,《受命》却有所历的生命经验,生活观与审美观均在此感性地显现。
止庵处理记忆,显得有些克制,自然也抑制了灵动感的散出,本该奔放的地方却有点矜持。这是与流行写作不同的地方,他或许觉得,这样可以防止滑入前人的套路里。京派作家有过这类笔法,知堂的文章也是点到为止,宗璞的小说喜欢裹在旧诗文的意境里,思想自有边界。知堂与宗璞最终指向静谧之所,止庵却在静谧中进入惊魂动魄的暗河里,在不动声色里,让我们获得一次反省生命与历史的机会。这样看来,说他改变了京派写作的路径,也是对的。我们都在前人的影子里,但不是人人都知道。他以读者陌生的方式,告诉我们曾有的时光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形影,唯在被遗弃的废园里,才刻有曾存的隐秘。
——选自《旧岁冷弦》,2021年4月23日《北京青年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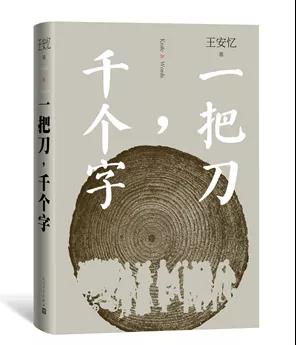
《一把刀,千个字》,王安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张屏瑾评《一把刀,千个字》
与王安忆过去的作品多设定一时一地不同,《一把刀,千个字》表现时空跨度极大:纽约法拉盛、上海、淮扬、北国,革命年代、拨正时光,异乡与旧日,物质遗产与精神狂飙,交替叙事,竟能纹丝不乱,高潮迭起。从特定空间或历史场景进行解读的方法可能会失效,须从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潮流之前因后果出发,才能应对这种书写强度。与此同时,这也是一部很能体现王安忆艺术特色的作品,无论是语言思辨力的再次展现,还是作者近几年所着力塑造的一类人物,很多方面都更趋于圆熟。
——选自“文艺批评”微信号

《回响》,东西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
孟繁华评《回响》
东西长篇《回响》是一部推理和心理齐头并进的小说,奇数章写案件,写与夏冰清被杀有关的推理和侦破过程;偶数章写感情,以侦破负责人冉咚咚和教授慕达夫的情感纠葛为中心。两条线的人物在推理和心理活动中产生互文关系,于是便有了“回响”。具体的写作方法上,强大又具体的细节,复式交叉的结构方式以及精准的文学语言,使小说具有了极高的艺术品格。东西以极端化的方式将人的情感和人性最深层的模糊样貌呈现出来,他找到了潜藏在人性情感最深处和最神秘的开关,这也是所有作家最关心和一直在寻找的关键事物。我们可以说,东西通过冉咚咚、慕达夫等,看到了我们内心最隐秘的情感,我们似乎已经没有秘密可言。如果是这样,那么,东西已经找到了他希望找到的东西。这是人类的基本困境之一,福楼拜、司汤达、托尔斯泰、菲茨杰拉德、纳博科夫等,都在这个寻找的谱系里。而这些作家作品,是东西内心的“绝密文件”。如果将这些“绝密文件”公诸于世,你会发现,那里无论怎样错综复杂深不可测,但最终写满的是人类的同情、悲悯、宽容的大爱,这些“秘密文件”就是人类大爱的回响。
——选自《在“绝密文件”的谱系里》,2021年3月13日《文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