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和池鱼》:锦鳞绣羽,水陆藏心

本期读书集结“和光”四位成员,探讨海外实力派作家张惠雯的最新小说集《飞鸟和池鱼》。不同于“在他乡”主题的《在南方》,该作品集将视线收归于故乡或旧地,以多种身份的“我”作为叙述主体,拨开往昔的帷幕,勾勒出目之所及、心之所念的旧事故友。记忆和现实穿梭,幻想与真相缠绕,互为因果,也互为深渊及救赎。故事里的人,应和着里尔克诗歌的倾诉:“我的感官像鸟一样,我用它们从橡树高攀到多风的云天,而我的感觉仿佛脚踩鱼脊,沉入了池塘里被窃取的白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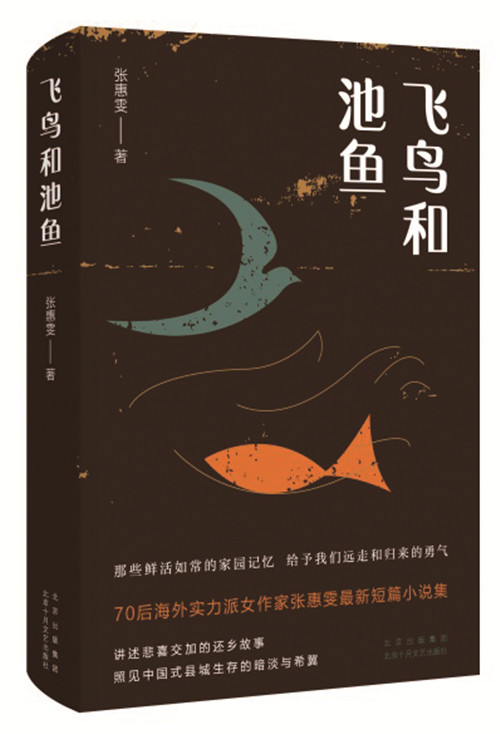
@赵鼎:渡“池鱼”为“飞鸟”:爱的和解与救赎
在小说集中,张惠雯将目光聚焦于日常生活及其内在维度的本质上,以探求更具普遍性意义的人性问题,尽管她也描绘了人性中鄙薄丑陋的一面,但总体而言,她始终保持着真、善、美的伦理价值追求。
在作者笔下,“飞鸟”与“池鱼”的意象颇具象征性意蕴,“我”以“归乡者”的身份凝望审视着故土小城的种种困厄,呈现出由“飞鸟”——“池鱼”——“飞鸟”的转化过程:作为个体的“飞鸟”陷入某种道德伦理困境而滞化为“池鱼”,几经挣扎后最终凭借人性的爱与善摆脱囹圄,重归自由的“飞鸟”。事实上,小说里部分主人公始终未能彻底挣脱现实生活的泥淖,他们的蜕变源自思想的转换和心灵的超脱。正如罗兰在探究文学作品中“鸟”的意象时曾指出,“小鸟代表着不朽的灵魂,而不是身体,鸟代表着精神世界,而不是世俗。这种观点非常普遍。”张惠雯的小说也是如此,所谓“飞鸟”并不单指身体层面的解放与逃离世俗困扰后的自由,而更倾向于强调历经沧桑后,个体从外在的矛盾与冲突转向对内在空间的探索与叩问,进而达成的一种释然豁达的心理状态与精神世界的主体性超越,即个体与自我、他者、生活乃至命运的和解。因此,从“池鱼”化作“飞鸟”之过程,就是一次个体对自由和谐心境的曲折性探求,并最终以“爱”完成的精神领域补偿性言说。
在其同名短篇《飞鸟和池鱼》中,爱与孝成为“我”折翼的主因。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身为人子的责任义务和母子间的亲情羁绊将原本生活在“更好更广阔的地方”的“我”逐回故乡小城。母亲精神的异常与前景的迷惘使“我”的生活始终浸染着一丝忧郁灰暗的色彩。看到池中游鱼,母亲欢欣雀跃仿若孩童,而“我”却“宁可池子永远是空的”。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在疾病生死面前,人性的矛盾与挣扎往往会暴露无遗。尽管“我”未曾放弃,但长期的生活压力和精神折磨早已令“我”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母亲已从昔日的庇荫凋敝为难言负担与压力之源,将“我”彻底缚为一尾难见天日的“池鱼”。然而,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还是为这不知期限的困局泻下一线光亮:“我”于一片“巨大、黑暗的安宁”中焦虑地寻找着母亲,担心她真的会如鸟儿一样飞走,当她安然无恙地出现在阳台时,“我感到心脏重新在我的胸腔中平稳地跳动”,在“我”抓住母亲的那一刻,“我和她又连在了一起,无论是身体还是命运……这比什么都好”。在那一瞬间,久违的安逸与轻松得以复归,压抑扭曲的母子关系得到缓和修缮,亲情最终平复并超越了平日的幽怨和苦难,渡“我”与生活谅解。
在其他几篇小说中,读者同样可以窥见与之相似的转换轨迹:《对峙》中原本是警察的“我”因冲动杀人而面临法律制裁,轮番心理博弈中,道德理智终占上风,遂选择死亡作为赎罪和解脱;《昨天》《良夜》《天使》的主人公则是通过邂逅记忆中的幸福与憧憬,依据善与美完成了对当下裂隙或创伤的疗愈;《涟漪》中的教授陷入情爱和责任的两难抉择,在家庭与生命“永远不可能交融”的孤独中,曾经的爱恋成为他余生的温暖与慰藉;《寻找少红》《临渊》皆以充盈着爱意的美好想象来弥补现实的缺憾,赋予人们跨越深渊、继续生活的勇气信念。
当人们坠入晦暗渊薮,唯有爱可成为救赎,无论是在现实中转瞬即逝还是只留存于幻想虚构之中,哪怕只有一瞬的光明与温暖,也足以点亮一个寂寞迷惘的灵魂,将其从“池鱼”再次拯救为“飞鸟”。于失落绝望中探求爱意与希望、在伦理困境中坚守真善美的追求、为踌躇彷徨的心灵指引迷津,这正是张惠雯小说中人文关怀精神的内涵之所在。
@于明玉:庸常者·沉沦者·救赎者
当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述,人群的微妙区分便隐藏着写作者的主观介入。小说通过持续性回忆建构出周边环境,在平铺直叙中显现不同生存空间的本真状态。因其独特的生活体验和自觉的旧日重审,亲人、故友、爱人、陌路人,都难以逃开作者对其是否沦为平庸的评判。“庸常”作为生活的中轴,任由低贱与崇高上下翻腾,而边缘模糊的三类人就此浮现。他们围绕“我”再现,粗略地涵盖了生存的每一姿态与侧面,也揭示了文学所能折射出的无限现实空间。
围绕“重返故土”这一过程,通过认知偏差体现了叙述者的心理落差,这不仅针对环境,更是直接指向“老家的人”。人物的无知和浅薄往往具有不自知的属性,因此极易诱发“我”情绪的放大与复杂化,进而从尘土飞扬的书写中流露出刺痛与贬损的意味。“痴愚”“势利”“衰颓”的形容与“怜悯”“厌烦”“悲哀”的心境相呼应,呈现出一抹面对故土内心矛盾的情感色彩。“我”与爷爷奶奶的对峙(《寻找少红》)、与史涛关于结婚成家的辩论(《昨天》),主人公的持续性发问省思了乡土文明和人性伦理,在纯粹道德感之外又留存着从时代浊流中解救个体,实现精神独立自由的意图。透过“外来”投射的目光,小县城里继承陋习、流于世俗的人们逐渐扁平、黯淡,单向度地对应着鸽灰色世界的每一条棱,最终沦为活生生的“庸常”。
“沉沦者”的出现或许是作者对现实进行突围的一次尝试,即一口气下潜到生命最晦暗处,见证着无法挽救的下坠与痛苦的徘徊。他们从社会的边缘缓步攀爬,向围观者显露出羸弱又苍老的面目。这种尖锐的揭示在叙事中却往往是以“理应如此”与“不期而遇”的形态出现,肉体与精神的悲惨处境被日常化,缩短了读者与悲剧的距离。而在重复体验个体苦痛的异质世界中,“我”从悲剧顶点回落,劫后余生的释放感也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我”与平庸和解的推手。
由于“我”在小说中的身份多样性,“俯视”的叙述立场可以转瞬更变为“仰视”。一如太阳因高悬刺目而于眼中轮廓模糊,来自于心理波谷的倾诉也呈现出一片因情绪外露而失去清明的迷蒙。当“我”撩开精神衰败的垂幕,重见澄彻往昔,理性的言语被缠绵裹挟,尊严的防线为软弱陡然侵入,新的情感体验从带有“救赎”意味的人群中矗立起来。
在作品集中,“救赎者”出现于“庸常者”与“沉沦者”之中,将我从苍白的生活中解围。需要注意的是,人总是在极为微妙的处境中与美好短暂相触,“救赎”一词本身就蕴含着被救赎者的感性言说,尤其是过往与当下两条时间线交叉行进,真实情景的记录与主观感受的虚构相互依附,而内心独白又使得现实与想象的混淆拥有了合理的存在方式,为形象的失真创造机会,换言之,这类形象的背后隐藏着扭转视角后就沦为平庸的可能。
但作者竭力将这美好凝固。她所使用的技巧就是塑造“片刻”。
人与人的相逢即是命运线的交错,在短暂拥合后迅速背道而驰。当模糊陈旧的碎片记忆成为描摹独立个体的惟一素材,针对确定对象的写作欲望又抹杀了全盘虚构与中立叙事的尝试,此时原本属于“人”的片面便过渡为文本中情景事件的瞬间。《昨天》中的“她”被“我”封存在有所指向的“初冬早晨”;在《良夜》里,属于“小安”的善意仅于两个夜晚扑朔浮现,在当下与记忆共同的折射下泛出一片梦幻的瑰色,二者都在推向过去的书写中凝结为主人公霎时的人生高亮;《涟漪》与《天使》则竭力放纵感觉的震颤与急转,“一个下午或几个小时”“极其封闭、狭小、温暖的空间”共同为扎根灵与肉的重逢提供了合适的温床。一切叙述刻意地绕过岁月与世俗,有关过去的铺垫与对未来的规避在此时此刻迸发出奋不顾身的勇气。追逐幻影的原始冲动与“可望不可及”的悲观情绪反复推拉,使得“他”或“她”的完美侧面在极端明亮中消弭了扁平的缺憾。当最终其“存在”于特定的节点猝然定格,便强行还原了情感初次觉醒时的朦胧往昔。被极力压缩的时间与空间共同营造出远超当下的对象,恰到好处地填补了主人公灵魂与理想的裂缝,而这也许就是其仅在瞬间存在的真正原因。
@高瑞晗:天使在人间
小说集很多篇都有“天使”的存在,它是美好女性的象征。张惠雯笔下“天使”有三类,她们大多是交织着幻想与现实的成熟少妇,也有存在于父亲记忆中的女儿和奋不顾身保护孩子的母亲。她们美丽、善良、温柔,但并非超尘脱俗,而是生长于真实的生活,有些沾染了世俗和岁月的痕迹,有些富有母性的温情,有些已成为美好的定格。
《天使》中,她曾点燃过少年的“我”,又让死灭的“我”再度燃烧。多年后,她已经没有那种让人心惊的美丽了,失去了曾属于少女的“惊心动魄”的美,但依然有天使一般、属于女性的特质——温柔、成熟、风情万种。与此相似的是《涟漪》中的情人,她温暖而羞怯,是光或梦想,诱惑稳态生活模式中的“我”,使我甘愿背离信条。《昨天》里的“她”是“我”记忆中的“天使”,曾有一个初冬的早晨,我们的心灵曾经向彼此敞开,重遇时“她”已沾染岁月的痕迹成为走向衰老的平庸少妇,眼神里的热烈天真被倦怠取代,“像一朵完全干燥了的花”。
面对死亡、瑟索、污秽的生活,她们是美好的幻影。幻影来源于并归属于过去,交织了幻想,短暂地出现于当下,但不会长久驻留。在支离破碎的世俗生活中,她们不露痕迹地带来稍纵即逝的深情。她们“是别的维度里的别的生活……在此处,我们似乎仅仅有权决定爱,却无权决定生活”。
另外两类“天使”,她们在小说集中所占篇幅较短,形象却足够生动。对于《临渊》中的老人,去世的女儿就是他的“天使”,老人以女儿为傲,逢人便聊起她,将她成长的点滴整理保存并视若珍宝。老人主动制造一次次谈话,令女儿从人间复活,擦亮命运深渊。《对峙》里的母亲是小男孩的“天使”。她在这场漫长的对峙中不卑不亢,尽己所能地保护孩子,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展现出柔(外表)与强(内心)的对峙。
@张林:两条时间线的对位写作
对位法是音乐写作中使两条或多条独立旋律同时发声并相互融洽的创作方法,在乐曲中形成复调效果。在作品集里,张惠雯将过去与现在两条时间线“对位”,两个时空交杂并置,互相渗透,交响出复杂而丰富的情绪体验。
“过去”由“现在”进入,切入点皆是主人公人生中“节外生枝”的一次“停顿”,是游离于主流生活之外的部分(如因母病父亡短暂归乡、因事而故地重游、无所事事的垂钓等),“一切都停顿在这个点,一切陷入困局……全都卡在这里”。但这停顿却极具“日常性”,可以是一次相聚(《良夜》《昨天》《天使》)、参观(《涟漪》)、出游(《飞鸟和池鱼》)、垂钓(《临渊》)、散步(《街头小景》)、远行(《寻找少红》)。过去经由“日常”的入口渐次降临。
在日常场景中,作者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寻觅着现在与过去共同的载体。它可以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如傍晚,在《飞鸟和池鱼》《昨天》等篇章里,作者将现实中“傍晚”的嘈杂混乱与过去的宁静美好比对,勾连出怀念之情的同时也指向了记忆的虚幻性质。它也可以是某个地点,如《天使》里的老屋,旧物依然,但今时和往日感受迥然相异,而更多的情形是时间使地点变化,甚至面目全非,只残留着一些零散的昨日证据以供辨认,如“名字”,《涟漪》中,“街道的样子变了,但名字依旧,那些字就像一根根突然擦亮的火柴,照亮了我心里连接往昔的幽暗通道”。在《关于南京的回忆》内,尽管“我”再没回到过那座城市,但“听到这城市的名字,那些鲜明的东西就突然苏醒……”再如“树”,《街头小景》提到“这些树自我中学时候就在……它们让我想起过去的光阴”。有些媒介则是更具体的,《良夜》老友聚会时,“我”和小安的座位排序与多年前一样(“和那晚一样,我坐的位置和小安之间隔着大超。”);《对峙》中那孩子的呼吸声让“我”想起儿子小时候;《飞鸟和池鱼》里“我”想起那封保存多年的旧信。当今与昔在某个细节上重逢,过去也就在现实的身体里轰然而至。
“对位”作用下,过去与现在两条时间线独立存在却也彼此包纳对方。从“讲述者”角度(书中故事皆为第一人称叙事,讲述者即主角)来看,体现为一种“干扰”产生的“噪声”。一方面是现在对过去的干扰,“这一路没有半点我熟悉的东西,它不仅无法和我往昔的印象有丝毫的交集、重叠,还形成一种痛苦的干扰”,当下的时间里,承载记忆的载体因变得陌生而对回忆造成间离,而当现实环境被弱化,过去将再次照临,即当“我”和“她”走在因感应灯坏掉而漆黑一片的楼道里时,“那个初冬早晨的感觉又会在心里全然苏醒过来……连气味都不曾改变”(《昨天》);另一方面也是过去对现在的扰乱,在《临渊》中,“我”讲述回忆时,两次捏住烟盒却又松开,反映了心绪之混乱,而在《天使》里旧人重逢也扰乱了“我”平静的生活,《关于南京的回忆》讲述了发生在南京的旧事,这旧事塑造了现实中“我”对男性和那座城市的看法。
整部作品集常出现的一个意象似乎可以为这种“噪声”作一个注脚,即“烟雾”。在“少红”所在的村庄中,“一切都蒙在一层又冷又潮的雾气里”(《寻找少红》),《昨天》中“我”记忆深刻的那个早晨“浮着一层奶白色的薄雾”,《涟漪》里故地重游那一日的末尾,“灯光和暮色交织成一团半灰半蓝的烟雾”,《临渊》那片钓鱼的河面上,有“要散不散的雾”,在《天使》里,作者提到了“时光的雾霭”。当过去和现在同时奏响,于文字间和谐交织,一种雾气般轻柔又沉重的阅读感受便翩然降临了。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2021年5月21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