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新势力 | 林培源:写小说从来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过程

编者按:
3月30日至4月1日,大益文学院与中国作家网联合主办“新青年•新势力”中国青年作家峰会,13位青年作家与8位文学导师,聚焦我们这个时代青年写作的归途与来路,航标与远方。
中国作家网特邀13位青年作家进行独家专访,探索属于他们的青年成长,倾听他们的文学故事。

林培源,1987年生,广东汕头澄海人,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2017—2018),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小说叙事研究。曾获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作品入选《2019短篇小说》《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等。201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202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小镇生活指南》,获评《亚洲周刊》2020年度十大小说。
林培源:写小说从来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过程
小说是林培源的乌托邦,真实和虚构缠绕、生长,形成一个存在于现实之外的世界。尽管两者姿态和色彩不同,近作《神童与录音机》(2019)、《小镇生活指南》(2020)却都发轫于同一个“原型故乡”,林培源曾经朝夕相处的、偏爱的、为之“迷狂”的潮汕。
作为一个从潮汕走出来的小镇青年,林培源的生活轨迹与同龄人大同小异,如果非要找出不同,那大概是“选择了写作,选择了文学”。十几年辗转求学的经历,让他在地理距离上离故乡越来越远,却在情感上与它越来越近——林培源说,“写小说从来就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过程,虚构、真实、现实和艺术,总是会有叠加、交融和互相激荡的时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些时刻仍与无尽的潮汕有关。
向着文本中存活的人、事、物写,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作家网:你的社交圈是怎样的?你认为如今被频频提到的“破圈”是必要的吗?对文学来讲,“破圈”是个有讨论价值的真命题吗?假如文学“有圈要破”,那该是什么?
林培源:我的社交圈还是以写作者、文学研究者为主。“破圈”其实是个老话题了,80年代的先锋小说家的作品借由电影走向大众也是一种“破圈”。“破圈”有必要,但那一定是建立在好作品基础上的“破圈”,没有好作品,再怎么破圈,都会适得其反。
中国作家网:你的写作习惯是什么?
林培源:小说的话,一定是想好了开头才往下写,每写完一部分,隔天会从头看起,对标点、字词、节奏等做修改,满意了再继续写。小说完稿后,放一段时间,发给信任的朋友看,接收反馈意见,再接着改。其他类型的写作譬如文学批评、书评这些,习惯是在读完书、做好笔记、摘录的前提下,有了想法再一气呵成。
中国作家网:写作时你心中会为读者画像吗,你认为这种潜在的交流是重要的吗?
林培源:实际上,我认为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和读者的交流已经暗中完成了。但这不是写作最根本的目的,我的文字、语言最主要的是向着文本、向着文本当中存活着的人、事、物,只有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作家网:谈谈你的阅读习惯吧。
林培源:读小说的话,如果是长篇、而且文本和故事相对复杂的话,我会在书页边角用铅笔写批注,写下阅读时候的感受,或是贴上便签纸,在上面涂涂写写;读学术著作、理论著作就更不用说了,除了贴便签纸写批注外,还会在电脑上用软件做笔记和摘录。这是读硕、读博期间做学问养成的习惯。这样看书很费劲,也很慢,不过就像老话说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本书读厚了,再读薄,有了笔记,今后基本可以不再翻,即使丢了也没关系。
当我们谈论一部小说,是将之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审视
中国作家网:当我们谈论一部小说,最可能会谈到的有语言、结构、节奏、故事、气质等等,你最在意小说的哪个部分?请谈谈你对小说的看法。
林培源:如果是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我读一篇小说,或者自己写小说,首先映入我意识的是小说的技巧层面,譬如“视角”、“人称”和“声口”这些。也就是说,你通过什么样的角度在观察故事(视角)、是什么人在“说话”(人称),还有这个小说的叙事声调、声音、语气是怎么样的(声口);其次是小说的故事层面,故事讲得通不通,有没有硬伤、逻辑上的矛盾和漏洞?小说写了哪些人物,这些人物彼此的关系是什么?这些人物在故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对话写得如何,贴不贴切等等。最后,就是这篇小说的语言配不配得上故事,形式上有什么巧妙之处,哪些细节是着重处理了的,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它能不能立得起来?
中国作家网:你的小说语言辨识度很高,有时像一位急于讲完故事的人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倾吐,有时又用相当长的段落去表达人心复杂的情绪,请谈谈你是如何掌控书写的节奏的?
林培源:叙事节奏的调整从文本上来看,取决于你是用“讲述”还是“展示”,讲述一般会加快节奏,因为你会用说书的口吻,把眼前发生的事情清楚交代,叙事人、作者的声音,相对响亮,而展示则会让时间慢下来,这时候叙事人会躲起来,作家的声音也会相对隐匿,为了传达场景、刻画人物,就不得不动用描写、甚至是繁复的、冗长的深描。当然,调整节奏的方法还有很多,譬如小说里的“省略”。但在我看来,书写的节奏和人称的使用关系也很大:如果我用第一人称在写,会不知不觉加快叙事的进度,让故事写起来很畅快,像水流一样,这是因为,我们的心理习惯、潜意识就像河床,第一人称就像河水,它是贴着河床流动的;但如果换成第三人称,那么作为写作主体的人,他和故事、人物之间就有了一定的距离,因为有了距离,就不得不花多一些笔墨去写人物的行动、心理和意识的流动等等。当然,这并不是说用第一人称的时候,就不需要写这些。这些都取决于个人的写作习惯。有时候,一则小说写的几乎全是人物的行动,心理是隐藏在行动背后的,这时候,行动的推进,也会让故事节奏加快。读者无暇去顾及和思考,人物此刻的心理是什么,只能任由行动带着他往前走,直到小说结束,人物的行动终止或者暂停。
目之所及的未来,仍与无尽的潮汕有关
中国作家网:目前最满意的是自己的哪一部小说?对未来的写作有怎样的期待?
林培源:最满意的其实是2019年出版的《神童与录音机》和2020年的《小镇生活指南》(获《亚洲周刊》2020年十大小说),它们是两部独立的小说集,但从我个人的写作历程来看,却是同一个小说观的不同侧面。我在一份创作谈里提到,这是“反常识”(《神童与录音机》)和“常识”(《小镇生活指南》)的写作。前者带有一些传奇、寓言和实验色彩,同样写的是潮汕,但试图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提炼出某种抽象的、甚至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后者,则用的是相对克制、朴实的“现实主义”的方法,老老实实讲故事,小心地写人物,试图传达某种更为鲜明的地域色彩,在小说中,也会加入一些潮汕方言作为人物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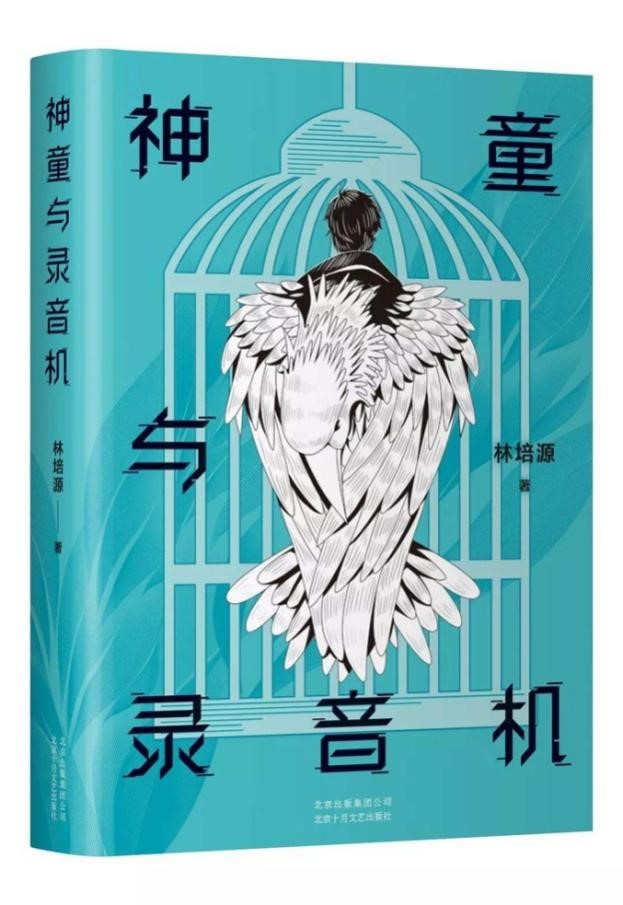
《神童与录音机》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8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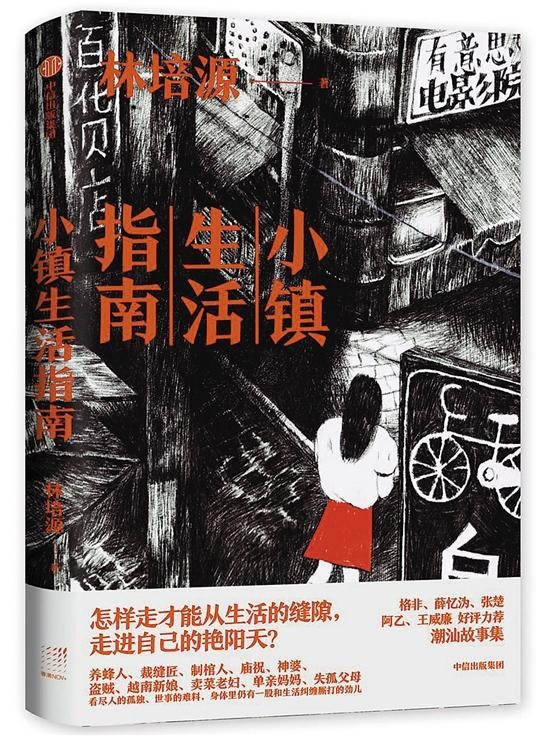
《小镇生活指南》 中信出版社 2020年7月出版
未来的写作,还是会把目光聚焦在潮汕,但相比之前两部小说集较为单一的人物和故事,我会把重心放在写不同阶层、身份背景的人物,注重拓展故事的复杂性,把小说的格局和视野打得更开一些。事实上,我已经在这样尝试了。
中国作家网:把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写作集成《小镇生活指南》可以视为对生长土地的回馈吗?除了绝大多数对故土的书写蕴含着思念和回味以外,你小说中的土地也好,人也好,文化也好,显然也包含了讽刺、批判,亦或同情,怎么恰当地掂量小说的温度和反思?作为已经离开家多年的人,怎么做到“站在外面”回头看待当初那个地方?写作是你再认识熟悉事物的方式吗?
林培源:谈到小说和故土的关系,鲁迅当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乡土小说的书写和兴起,源自那些居住或者迁徙到城市中的“侨寓者”。小说家如何面对故土、如何书写故乡?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和五四一代的“侨寓者”们类似,不同在于,在时代变迁和时间的洗刷下,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了,写作的对象也不尽相同。写小说的时候,我不会预设一个特定的立场,譬如这篇小说是要批判,哪篇小说是要讽刺,这些其实都应该首先“悬置”起来,小说最主要的还是人,在我看来,“人”永远大于“故事”,也大于“小说”,当我把目光落在我要写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体会到的是他们的悲喜、苦闷和希望……具体到如何写,如何拿捏尺度,就是小说技术层面的问题了,当然,背后是你的小说观在决定,在支撑。
如何“站在外面”回望“最初的那个地方”?成年以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求学和生活,基本上只有寒暑假才回潮汕老家,这个时段对我来说特别宝贵,因为这是我和故乡重新“联结”的过程——以一种在地的、身心相连的方式,不过除此之外,我和老家的联系也没有完全断裂。我现在在广州生活,平时也经常能遇到老乡,这种被“包围”的感觉是很奇妙的。我觉得写作者应该一直保持某种陌生化的观感和触觉,熟悉的事物不一定就能写好,就像贴在视网膜上的物体,看起来一定是模糊一片。所以,保持距离、保持某种抽离的视角对写作者来说是有帮助的。经由写作,熟悉的、陌生的人和事,会和你的生活体验,或者如普鲁斯特区分的“自觉”和“非自觉”的记忆融合在一起。写小说从来就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过程,虚构、真实、现实和艺术,总是会有叠加、交融和互相激荡的时刻。
在迁徙与变动中,我们自身经历着从内到外的“改造”
中国作家网:你有过海外交流的经验,简单说说你观察到的交流中的中国文学。
林培源:说来好玩,我在Duke的时候(曾于2017-2018年在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访学),导师Carlos Rojas带的做中国研究或者中国文学、东亚研究的硕士生,大多是来自大陆,或者是台湾、香港的人,面对同一个文本,其实大家的观感、态度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文学处在何种位置,这是一个很庞大也很难回答的问题,有一次我去西校区逛书店,看到了书架上Chinese Literature一栏上有格非老师的《隐身衣》英译本,也有鲁迅和其他当代作家的书,但总体而言,买的人、看的人特别少。我们也在积极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但真正能获得巨大关注的,似乎并不多。
中国作家网:有人说我们处在一个“文艺泛滥的时代”,有不少与文艺相关的概念被解构,意义上出现了与过去大相径庭的理解,这是时代带来的。这些变化在青年一代身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比如,今天人们对“文艺青年”这个词的理解并不单纯。你是文艺青年吗?在我们的时代,你怎么理解文艺和文学?
林培源:如果按照惯常的解释和定义来看,我理所当然会被划分到“文艺青年”的标签下面,譬如对小说的痴迷啦、对电影的热爱啦,对有关的文学话题的敏感啦,等等。不过在我看来,人都是复杂的,单一的、固化的标签无法完整地概括一个人,我也反感用某某标签来定义某个人。对写小说的人来说,这种刻板化的、简化的思维也是需要警惕的。我理解中“文艺”的范畴要大于“文学”,可反过来说,二者并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它们的关系,就像“文艺”和“青年”,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也有相互背离的部分。我觉得不管是文艺、文学还是青年,最重要的还是“生活”。离了生活,文艺就是死的,文学也是死的。
中国作家网:还是一个关于时代发展带来变化的问题。乡村和城市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界限分明——乡村青年背井离乡到城市讨生活、某种程度融入城市,或者有的村镇进行了整体搬迁、过上了与传统认识中的乡村生活不一样的日子……这都是我们能够见到的现实。在你看来,这对于生活本身意味着什么,对以乡村生活为观照对象的那部分写作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林培源:实际上,我本人也处在这样一个大变动、大迁徙的过程中,求学对我来说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或许我的生活就和其他生活在乡镇、村里的青年人没有多大的差别,可能会外出打工,也可能在某个领域混出名堂,但这些都是我现在无法想象的那个“可能的世界”。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经验在变化、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在改变,尤其是多年的写作生活,已经几乎把我从内到外都“改造”了,一方面我借此获得了兼顾本职工作和业余写作的平衡,拥有了写我生活的潮汕小镇的“资格”;另一方面,又好像是“失去”了什么。这种获得和失去,我甚至找不到标准来衡量到底是好是坏。
出离患得患失,写下去,剩下的交给时间
中国作家网:我注意到你曾经接受过不少媒体的访问,其中除了平面媒体,也不乏以文学或写作为主题的线上直播,以及“一席”这类较多受到青年群体关注的意见表达平台。在与传播媒介的接触中,你对传播作用于文学和写作者的影响有怎样的看法和思考?对豆瓣、微博等更注重以不同人群喜好为评价标准的社交和意见表达环境,你的态度和参与度如何?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或有趣的事?
林培源:我从2009年就注册了微博,一直使用至今,豆瓣是2008年注册的,现在它们变成了我最经常使用的社交媒体,我在上面和读者交流,分享生活、阅读和写作,也在上面收获了来自陌生人的暖意。在新媒体的时代,很多时候,我们是靠这样的方式和素不相识的人取得联系的,在文学无法抵达的地方,媒体提供了一个相对便捷的渠道。包括我和一些写作者,也是在豆瓣或者微博认识的,后来在现实生活中见面,成了很好的朋友。眼下,有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通过豆瓣这样的平台“出道”,被读者大众所认识,我觉得对写作者来说,这是很公平的,不像十几年前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给杂志投稿,被退稿,有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被发现”的过程。
“一席”的演讲,也是这样机缘巧合的情况下促成的,我和节目策划人在豆瓣上“互关”,互动了很久,某天他们给我发来邀请,让我受宠若惊,后来才答应下来去演讲。整个过程,特别难忘,是很新奇的体验。
中国作家网:你有获得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奖项的经历。与“快男超女”等一夜成名的选秀行为类似,当时“青年写作者在获奖之后可能迅速成名”,积攒相当的人气,这类经历对青年写作者的影响是什么?如今,获得人气好像越来越成为一件无法被准确预料的小概率事件,那么你认为今天还会有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文学新人身上吗?如果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你认为它发生的契机是什么?
林培源: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写作者造梦的时代。2007、2008年的新概念之后,我还参加了The Next文学新人选拔赛,这个比赛更像“快男超女”,当时我还在读本科,因为参加比赛,被很多读者认识,经常有读者在微博上给我留言、发私信,也有人给我寄信,我还回了信。2019年在郑州松社书店做《神童与录音机》活动的时候,有个读者专门带了我大概十年前给她回的那封信,让我特别感动。这样的经历其实有好有坏,一方面它给足了你写作的信心和勇气,另一方面,在刚开始踏上写作之路的阶段,巨大的关注和目光,容易让人迷失自我。现在回望这段经历,我反而变得更平静了,当你经历过巨大的荣誉,被众多目光关注之后,你反而能从那种灼热中退出来,保持冷静和客观,更专注于你的写作,而不是患得患失。毕竟,没有好作品,获得再多关注都是虚的。
眼下这个时代,这种情况在新人身上还是经常发生的,要么从某些平台上被发现,然后进入所谓的“主流”文学圈,受人关注,发表、出书;要么就是走传统的路子,在期刊上发表作品,一步步踏上写作之路。说回来,“一夜成名”的背后,都是无数的努力和沉默。我的看法是,首先要写出好作品,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采访:中国作家网 杜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