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大隐于西·五湖四海 ——新世纪20年欧洲华文文学
编者按
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
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
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
(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文章即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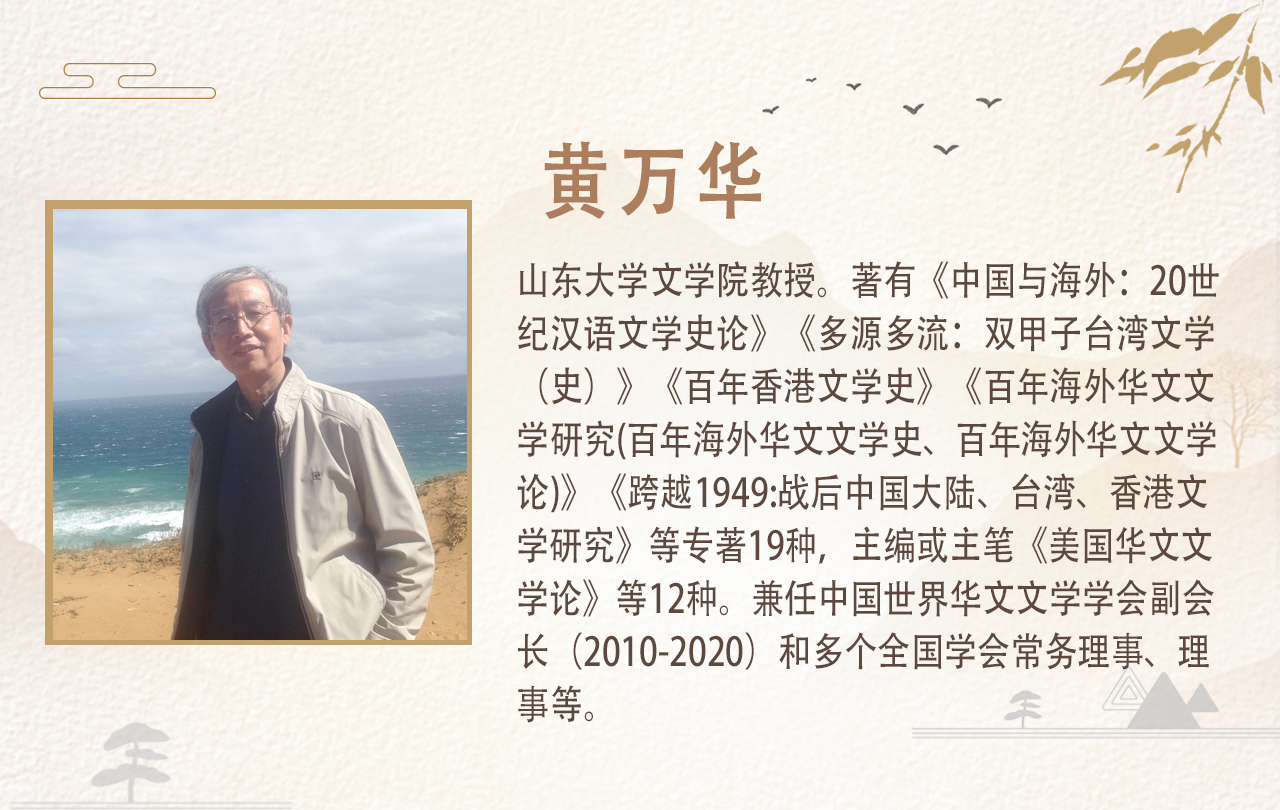
中国国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后逐步扩展到北美等地,欧洲华文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大版块,是最迟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事实上,欧华文学已有百余年历史,更是华文文学藏龙卧虎之地,甚至可以说,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在世界享誉最高的可推欧华文学,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传统最有成效的也当属欧华文学。而欧华文学作品在21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中井喷似的涌现,书写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厚重一页。这里,只叙述我观察到的21世纪欧华文学的三种现象,从中却可见欧华文学“远行”走来的坚实身影。
“出土文物”,改写文学史
这里的“出土文物”,指的是长期湮没的文学作品被重新发现,重新以各种方式出版,获得新的价值。欧华文学的百余年历史正是在21世纪得以呈现,早期欧华文学的诸多重要作品在2000年后第一次在中国大陆问世,为中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所接纳,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看,是新世纪欧华文学的重要展现,也改写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某些重要篇章。
海外华文文学有两种主要形态,一是所在国的少数族裔文学形态,它由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华人作家(既有第一代移民,更有在海外出生的更多代移民)创作,可进入外国文学范畴;一是中国作家的“海外语境”创作。这里所言“海外语境”创作是指作品的创作目的、产生过程、传播影响等都不同于我们所熟知如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老舍等有海外经历的作家创作的海外背景的作品,“海外”成为其作品创作、传播最重要的语境。它主要产生于这样一种情况:晚清后不同时期,一些中国文化人较长时间居留海外,他们大多从事双语创作,其写作动机往往并非参与中国国内的思想启蒙、变革救亡等社会潮流,创作常常发生在跨文化对话之中,作品面向海外读者并被广泛接受,世界由此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其中文版本返回中国,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早期欧华文学主要就是这样一种形态,而它在21世纪返回中国。
晚清陈季同(1852—1907)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在海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他的法文版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1890)和“中国独幕轻喜剧”《英勇的爱》(1904)在欧洲反响强烈。以《黄衫客传奇》为例,出版当年,法国《文学年鉴》《费加罗报》等报刊称赞“作者以一种清晰而富于想象力的方式描绘了他的同胞的生活习俗”而充满“新意”,出版的翌年4月,他成为法国《画刊》杂志的封面人物。这部小说问世百余年后,才被赴法的中国学者发现,带回中国,2010年出版了中文译本。中国现代文学界视《黄衫客传奇》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起点,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因此提前了好几年,因为陈季同在将原作《霍小玉传》中的负心人改写成《黄衫客传奇》中陷入困境的有情人时,已经自觉进入到了现代小说的创作:小说所描写的,无论是心理活动的内容、心理分析的方法,还是人物悲剧的命运,在中国文学中都前所未有,而其细腻、深入,在日后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呼应;叙事语言则有对古典汉语诗意的保存和现代法文资源的汲取。《黄衫客传奇》对中华民族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发生在海外写作的语境中,呈现出“中国与海外”的文学新格局。
五四至二三十年代,中国作家在欧美真正享有盛誉的有四位,一位在美国(林语堂),三位在欧洲。最早的一位是五四那年,以“五四运动嫡系的延续”勤工俭学的身份来到欧洲的盛成(1889-1996),旅欧时间长达20余年。他的重要作品在欧洲出版,同时期也在中国出版了中文版本,称得上第一位双语写作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盛成处女作、长篇传记《我的母亲》1928年在巴黎出版,当时法国最负盛名的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瓦雷里作长篇《引言》,热情称赞《我的母亲》以一种“最高最上的情感”在“吾人”(欧洲人)面前“宣传中国民族的文化”。作品发行达百万册,法国《世界报》《巴黎时报》《欧洲杂志》等数十种报刊以及《纽约时报》等国际性媒体和罗曼·罗兰、萧伯纳等知名人士,都撰文评价。《我的母亲》被译成16种文字,一些章节被收入法国中小学课本,《我的母亲》迄今仍是法国高校文科必读名著。
《我的母亲》以“我的母亲”写出“中国的本来面目”,其中所体现的,无论是从近代科学出发去看待女性,还是立足个人感受深切怀念母亲,都突破中国家族制度的历史局限,让欧洲第一次从中国作家笔下感受到经受了五四洗礼的胸襟和视野,反封建、尊人性的五四精神更在以“返魂梅”为中心意象的日常化叙事中得到鲜明表现。当时盛成在法国还出版了4部纪实文学和散文集,统一结集为5卷本《归一集》,以东西方的对话、沟通探求人类的“大同”、世界的“归一”。《归一集》中所体现的“五四”精神的延续,在海外语境中,又沟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恰如盛成在《意国留踪记》中所说,五四的中国面对“外来居上”,自然也该“使固有的文化,重新复活起来”。就此而言,盛成的海外创作无疑丰富了五四文学史。
另外两位是蒋彝和熊式一。蒋彝(1903年—1977)1937年在英国出版了《湖区画记》,这是他44年旅居欧美生涯中出版的13本《哑行者画记》系列的第一本,以包含中国书法和传统水墨画的“画记”这一文图互释的形式,呈现一个中国旅欧者眼中的西方(伦敦、牛津、爱丁堡、巴黎、旧金山、波士顿……),以中国诗画的丰富资源表现出包括五四新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东学西进”,在欧美长期拥有广泛的读者。2010年后,蒋彝“画记”在中国大陆问世,恰逢文学与图像关系成为文学界关注的焦点,图文互文成为文学史的重要新内容,而蒋彝“画记”以其跨界的成功让现代文学史获得了一种新的起点。。随后,曾与冰心、林徽因并称为“民国文坛三大才女”的凌叔华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古韵》(中文简体译本2005年出版)也采取作者自己配画的形式,《古韵》之画所展示的雅风秀韵,与《古韵》叙事相呼应,将欧洲读者领入一个古老文明的诗意国度,凌叔华也由此被称为“第一位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
西方文化界有“东林西熊”的说法,主要来自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在美国享有盛誉,熊式一(1902-1991)的《天桥》则在英国广受青睐,两部小说都诞生于二次大战期间。长篇小说《天桥》是熊式一继其四幕话剧《王宝川》(1934年起,《王宝川》在英国连演三年,达900多场,后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并被一些国家列为中小学必读教材)后又一次轰动全英的作品,1943年在伦敦出版当月即售罄而重印十余次,也很快有了法文、德文、西文、瑞典文、捷克文、荷兰文各种译本。英国桂冠诗人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更是为《天桥》作诗为序,表达英国社会对《天桥》的喜爱和解读。《天桥》的创作和《王宝川》一样,表现出极为自觉的“让西方了解中国”的创作动机,无论是讲述主人公李大同32年人生经历所呈现的中国社会变革,还是小说章节安排所包含中国传统的智慧、信仰、伦理等,都让欧美读者真切感受到古老国度的新生。《天桥》2012年在中国大陆首次出版中文版,连同20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宝川》,再次让21世纪的中国读者看到欧华文学传播中华文化的强大成效。
大隐于西,走进寻常百姓家
2002年,作家程抱一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法国思想文化最高荣誉机构370余年历史中唯一的亚裔院士,可谓与孟德斯鸠、伏尔泰、雨果、大仲马、泰纳、法郎士、柏格森、尤奈斯库等大师并存的“不朽者”。这恰是欧华作家“大隐隐于西”的成果。
程抱一是最典型的“大隐隐于西”,他1948年旅法后的最初十余年中“一无所有”,中国大学毕业文凭在法国无效,更无职业。那时候中国文化、艺术在法国远未受人瞩目,致力于中华文化传统的延续不会带来任何现实功利。就在这种环境中,程抱一潜心于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又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本土古代艺术、绘画和诗歌传统的意义,由此展开自己的文学创作。在这种文化“隐居”生活中,程抱一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而影响最大的是他对语言,尤其是汉语资源的深入开掘。
程抱一最初在法国有影响的著述,就是运用结构主义、结合唐诗研究汉语的《中国诗语言》。之后,他一直视“美”为“生命内在喷发出的向着让其此在的生命完美的冲动”,而文学作为一种“第三元”(“第三元”思想是程抱一从“道家和儒家共同之道”中提升出的“人类的宇宙观”)的存在,不断趋向生命大开的过程,实现以语言呈现生命“至真”状态的历程。语言的探求,就是要将文学反映人生命最终“大开”历程的门扉打开得更大。他从传统最悠久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开掘汉语“得以表达人与世界的微妙的互相依存关系”的潜能,并在汉语与法语的“相遇”中,将汉语潜能转化为现代诗歌和小说表现的方式。他的长篇小说《天一言》(1999)获得法国极有权威的费米娜文学奖,2004年和2009年,中国大陆出版了两个版本的中文《天一言》,成为新世纪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欧华文学作品。小说以主人公天一和他的三位挚友(玉梅、浩郎、薇荷妮克)的生命历程,呈现出生命的永恒正是存在于来自生命源头的写作,而整个叙事以“语言的力量”实现对生死二元的超越,达到生命的永恒。叙事语言更有回归大地的至美,融汇着中西文化深度沟通后的智慧,展现出“从无以探测的土地深处,仅靠语言的力量”来呈现中国人一生“所累积的珍宝”的魅力。
程抱一另一长篇小说《此情可待》(2001)使他成为首位获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法语文学大奖的亚裔作家,被法国文学界视为“传世之作”。小说传达出的中国民间男女恋情故事被明末中西文化交流所激发出的爱的真义,正是人的生命“大开”的境界。他最新的小说《游魂归来时》(2015)以“荆轲刺秦”的历史“积淀”探寻“友情和爱情是否能并存?‘三’的关系是人类所能及的吗?”这一人类生活的根本性问题的答案,小说叙事采用的戏剧独白体在“荆轲刺秦”的史传传统中融入了中国抒情传统,让人们所熟知“荆轲刺秦”的历史故事在人物独白所深入的内心世界中生发“在灵与肉的对话中得以实现”的“真正的三”。而其戏剧独白体叙事的成功甚至完美,在于形式与内容的水乳交融,尤其是以诗画合一的风采传达出中国文化的精华和神韵。
程抱一的诗集《万有之东》2005年列入法国伽里马出版社《诗》丛书。《万有之东》包容、超越的高远意境,将一种从个人心灵深处喷发而出的跨文化对话转化成神韵生动的中西山水画,揭示了永恒存在于主体之间的“生命真谛不应是一物对另一物的主宰,而是彼此间的融通。”恰如他2009年的新诗集《真光出于真夜》所呈现的,“真光,∕从黑夜里喷涌而出;∕真夜,∕孕育喷涌而出的光”,于天地万物交流中实现生命大开的诗意,始终充盈在程抱一创作中。
程抱一成就于“大隐隐于西”中,然而,他的作品却能走进法国“寻常百姓家”,为法国各界所喜爱、接受。他的作品一再售罄,2006年,他在法国作了五场关于“美”的公开演讲,来自各方的民众,“东方通或中国通,以至对东方或中国一无所知的人”,聚集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共享程抱一“美的沉思”。
旅欧四十多年,创立了欧华作家协会的赵淑侠曾在散文《书展》中,表达了希望中国文学作品和作家“真正能够像西方作家”那样,“进入西方的‘寻常百姓家’,为社会上一般消费者,像阅读他们自己国家的文艺小说一样,能引起读欲并喜爱的”的心愿。这种希望和追求,使许多欧华作家的作品脱出了以往留学生文学表现“无根放逐之苦”的传统,努力体悟人类之情、人性之根,显示出开阔的艺术视野。赵淑侠的20多部作品就一直有着这种追求。她2009年的长篇新作《凄情纳兰》取材清代词人纳兰容若的爱情生活,表达了对“情”超越现实功利,甚至超越生死的看法:“情是天地间的灵气凝聚成的最美的精神”。小说将纳兰容若这一形象刻画得血肉丰满,不只是因为作者历史考据功夫甚深,更因为作家理解了纳兰容若的情感世界。作为满族达官贵人的子弟,纳兰容若的“情”完全突破了族群、门第、性别等传统世俗观念,包容起人类的共同性。小说在台湾的《世界日报》和大陆的《作家》杂志同时发表,更被欧华文学界称为成功塑造了“跨越时空”的融合“文学人类”的“阴和阳”的历史人物形象。
如程抱一那样,“隐居”中全身心投入写作,孜孜以求守护文学精神的欧华作家大有人在。例如定居荷兰30年的林湄“十年磨一剑”,创作了长篇小说《天望》(2004)、《天外》(2014),持续展开对人性和自我超越现实的探寻,也在中西文化交流等问题上提出思考。作品走进欧洲“寻常百姓家”的欧华作家也大有人在。例如出生于北京的山飒旅居法国25年,她创作的小说有如当年林语堂的作品一样,先在西方传播中华文化(如2001年获法国青少年龚古尔奖的法语小说《围棋少女》被译成30余种文字,并被改编成话剧在德国上演;2003年的长篇小说《女皇》也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日本、韩国、美国畅销),再被中文读者所接纳。这种语言、传播上的“远行而回归”来自山飒极其自觉的文化交流意识,其作品题材一开始就切入纯然的中国故事,用“古典法文”表现中国文化的内在意蕴,“远行”至异种语言之中而表达自己灵魂中的“根”,叙事方式上则往往“越界”而出,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同构也被她发挥得淋漓尽致。
“五湖四海”,丰富的地域路径
欧洲华人来自“五湖四海”。近20多年,海外一些地区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文学颇有“一枝独秀”之势。而在欧洲,上世纪80年代后从中国大陆移民的作家固然十分活跃,从个人性的创作到荷比卢华人写作协会、欧华文学会、欧华文学笔会、欧洲新移民华文作家协会等文学社团的创立,一大批大陆新移民作家在崛起;但从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甚至东南亚移民欧洲的华人作家也未沉寂。以上世纪70年代后从台湾移居欧洲的作家为例,定居德国的陈玉慧的长篇小说《海神家族》(2004)获香港第一届红楼梦奖评审团奖(2006),并被译成德文出版。这部多线索交叉讲述台湾移民和被殖民历史的小说成为新世纪德华文学的重要收获。旅居瑞士的朱文辉20多年前开始在一系列长、中、短篇推理小说中塑造了旅瑞华人名探张汉瑞的形象,两度获“林佛儿推理小说奖”。他创作的侦探推理小说,从他当年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接受的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中,运用有别于西方侦探推理小说传统的方法,去解剖人类的共性,同时也寓阅读趣味于富有诗意的“中国智慧”中。现居荷兰的丘彦明曾任联合文学杂志总编辑,久居台北的她移居欧洲后,却创作了《浮生悠悠》《家住圣·安哈塔村》《荷兰牧歌》等一系列乡村田园散文集,在自家“种地”的生活中再次回归中国人最悠久的田园情结,在海峡两岸均获好评。旅法作家郑宝娟创作的丰硕,早被林燿德称为“天下第一捕快”,海外生存环境强化了其小说所写的人性沉沦、灵魂救赎,她将侦探小说视为“最贴近文学就是人学”的作为,展开对深层人性的求索。新世纪以来,除了继续创作了小说集《桃莉纪元的爱与死》(2003)、《极限情况》(2005)外,她更多转向了散文创作,《在绿茵与鸟鸣之间》(2001)、《无苔的花园》(2003)等散文集,对生活、社会的种种观察、体悟,温婉细腻而又笔锋犀利,文化思考独特,更有汲取中西文化营养、于现实生活中提炼新鲜感,被认为“在质、量上甚至超越了小说”,成为她“创作的新高点”(台湾张瑞芬语,2006)。专写散文的吕大明是欧华作协“第一个会员”,旅欧后创作了15部散文集,有着浸润于中西艺术想象中的“绝美”。他晚年体弱,却依然创作了《世纪爱情四帖》(2012)、《生命的衣裳》(2014)等散文集,其艺术质量之高,入选了台湾九歌出版社的“九歌100年散文选”。这些台湾旅欧作家的创作,无论是从欧洲回望台湾,还是在欧洲重温中华家园梦,或是让中、欧相遇中升腾起人性、人类之美,都在他们原有的民族、地域文化资源中融入了欧洲不同国家、区域的文化养分。
从香港旅居法国40余年的蓬草,迄今仍被视为重要的香港作家,就因为香港人认同蓬草所写的海外生活,即使香港“不在场”,也是有独特香港见解的海外。至于中国大陆的移民作家,其祖籍或生长地分布广泛,而欧洲各国语种之多(2015年前欧华文学分布的22个国家中共有16种官方语言)、文化传统之别,又远甚北美或大洋洲的华人旅居区。这就给欧华文学带来了丰富的“地域路径”,即我20多年前就描述过的,华文文学,尤其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基本格局是由几个大的文化迁徙群体的流向决定的,这些文化迁徙群体都将自身原先拥有的文化资源“旅外”迁移至现时文化空间,与原先的当地文化相遇、对话、交融,形成华文文学的丰富性。尤其是文化的交融,往往越过国家的层面,而发生于“地域”层面。来自“五湖四海”的欧华作家,与多元的欧洲文化相遇,碰撞出丰富的文学话题。例如出生于瑞士、成长于中国、1988年后长居欧洲的杨炼,从“斯洛文尼亚只有二百万人口,却有数种方言能用自己的文字书写”中悟到,方言“在所在地域扎根深”,同时“又向周围文化敞开”才极有活力,而“没有真正的‘地方文化’,更逞论‘个人文化’”,于是身体力行地去推动汉语“方言写作”,成就了他个人创作,同时也是汉语文学的一个重要突破。
欧华文学“地域路径”的丰富还在于孕成于祖居地或幼居地的作家个性甚至天性与欧洲文化的多样性碰撞形成的创作个性。例如虹影,在21世纪继续贡献了《一个流浪女的未来》《阿难》《孔雀的叫喊》《上海之死》《好儿女花》等小说佳作,其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河流”,从流过家乡的长江、嘉陵江,到三峡河流、长江入海处,再到印度恒河、欧洲塞纳河……成为她笔下精神品质、审美意蕴、文化认知最丰富深邃的意象,承载着从巴蜀山水向世界扩展开去的广阔人生,跃动着虹影叩问、追索历史和命运的身影。同样从川地走出的戴思杰,他那部获法国“费米娜”奖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0)在中外皆有影响,就在于小说借“小裁缝”的命运变化写出了作者所经历过的中国西南山村文化与法兰西文化之间的对话,不是文化胜负的较量,更不是文化征服,而是在生命的自由境界这一文学的终极追求上的沟通、呼应。
本文尚未一一述及新世纪20年欧华文学中诸多创作有成、值得关注的作家:关愚谦、祖慰、简宛、万之、友友、章平、绿骑士、黎翠华、池莲子、王露禄、老木、穆紫荆、郭凤西、谭屏绿、郭小橹、陈平、周勤丽、叶小明、俞力功、张执任、林冬漪、孙一琪、王展鸿、赵燕、孙逸勤……还可以长长列下去。而这名单又是流动的。如果我们将他们的“故乡—旅欧”路径一一梳理,会呈现出从中原、齐鲁、燕赵、吴越、关东等地域到西欧、北欧、东欧、南欧等的丰富路径,从而给华文文学带来崭新面貌。
“出土文物”呈现了早期欧华文学在21世纪的当下活力,“大隐于西”是战后欧华文学长期积累在21世纪结出硕果,而上世纪80年代后的欧华文学则在新世纪展现了丰富的“地域路径”,都预示出欧华文学的兴盛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