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星辰回响 格非、林白:当年的语言游戏源自对浅俗和世故的抵抗
1981年4月,《文学报》正式创刊,近四十年文学历程,犹如一条宽阔河流,源远流长。顺着水流的方向,是崇峻向坦荡宏阔,是湍急向幽深丰厚。这也是一片辽远星空,今天的文坛名家们,曾经是与现在“90后”新人一般的年龄,如一颗颗初升的新星,以新锐身姿,并入星轨,璀璨交辉,许许多多的第一篇访谈、第一篇创作谈、第一篇评论之声留在了《文学报》。

创刊号
明年4月,创刊四十周年,我们从此刻回望并聆听文学与作家们初升时的声音,那里有经典性背后隐藏的质地、品格和精神成长。正是这些声音相互激荡、回响,不断阐释和生发,从而形塑文学当下。
我们将陆续为大家带来这组专题文章“40年·星辰回响”,和年轻时的作家们相遇对话。
10月4日带来作家格非和林白谈论自己的成名作。

追忆《乌攸先生》 刊于1995年12月7日文学报

格非
格非:追忆《乌攸先生》
乌攸先生,本属乌有,又何来追忆?单从这个标题来看,亦不难发现这篇小说的游戏性质。据说“游戏”一词在德里达的笔下似有独特含义,而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界,“游戏”这一概念正遭受到正人君子的大张挞伐,无论何人何事,一与游戏沾边,便是自甘堕落。但是没有办法,当初我在写这篇小说时,的确抱有某种“游戏”态度。何况直到现在,对游戏的兴致并未削减。姚阿幸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说过这样的话:自由然而寂寞。后来,勃拉姆斯将它改成了:寂寞然而自由。语序颠倒了一下,意思大不一样。我觉得纯正的游戏必定是自由的,然而也是寂寞的。或者,也许可以这样为自己的这种游戏行径进行辩护:在“崇高”这一概念被大肆炒卖的今天,当个人被浅俗、世故甚至无耻的时尚弄得晕头转向,偶尔游戏一下,亦属正当、自然,没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张旭东先生在他的一篇长文中对《追忆乌攸先生》这篇小说有过详细的评价,并认为它包含了作者写作上的许多秘密。最近葛浩文先生又将它译成了英文,法国伽里玛出版社亦将它译成法文出版。可我在写作这个短篇时,的确没有想到过将它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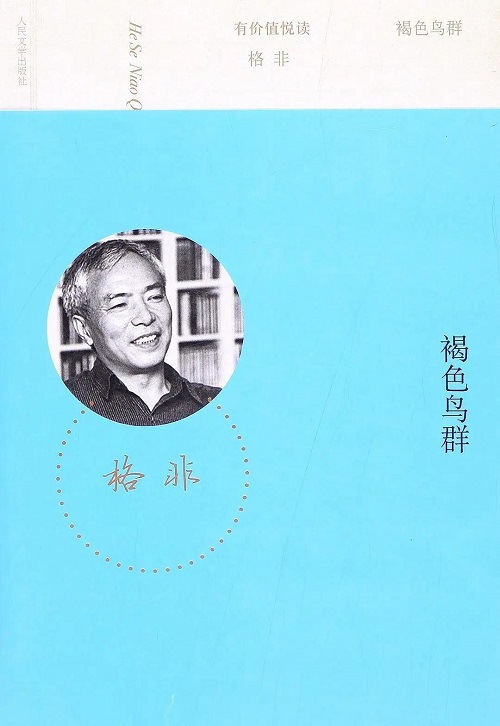
收录于《褐色鸟群》,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那是在一九八五年的初春,我们语言学小组在著名语言学家颜逸明教授的带领下,去浙江的桐庐、建德一带进行方言调查。应当说我对语言学历来没有什么兴趣,对方言调查的重要性至今不甚了解,我之所以混入这个小组去浙江,实在是想借机出去游玩一通。由于我对方言音标一窍不通,连自己的发音都混浊不清,更谈不上对那些地区的方言加以有效甄别和记录了。好在我们几个对当地盛产的五加皮酒有着不错的味觉,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偶尔也能陪着颜教授小酌几杯,因而颜教授对我们特别“宽大”,既然我们发音不准,便承担起了包括打前站在内的一应杂务。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接触到了当地有关“九姓渔户”的传说。因为好奇,我们还去有些村落装模作样地“考查”了一番。这段经历直接涉及到了《追忆乌攸先生》和日后《青黄》的写作。
方言考察的最后一站是梅城,我们安排好了一行人的饮食起居之后,颜教授或许认为我们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了,便打发我们早早踏上返校的归程。
我与一个女教师同行。我已记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记得她坐在我的对面,告诉我这班列车开到上海约需十二个小时,随后便一言不发。在这十二个小时里,我坐在拥挤嘈杂的车厢里,在腐烂发臭的鱼虾的气味中,为了打发寂寞,便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个故事。
回到上海后,适逢《中国》杂志社的王中忱先生来沪组稿,林伟民和徐芳老师介绍我认识了王中忱。他问我有无现成的稿子可以给他带走,我说倒是有一篇写着玩的东西,尚未誊写。王中忱就让我抄出来给他看看,后来,这篇小说就刊登在《中国》杂志1986年的四月号上。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正因为想写着玩玩,倒也无拘无束,并让我感受到了文学创作上最初的自由。它对我日后的写作不无补益。因此,我自己对这篇“处女作”时常怀着美好的情感。

想起《一个人的战争》 刊于1996年6月27日文学报

林白
林白:想起《一个人的战争》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部成名作。成名这个词对我有一种压迫感,它像一套不合身的衣服使我不知所措,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提醒我,我也许并不适合站在那样一个位置。事实的确就是这样。
当我回想自己的作品,想要找出一部知道的人多一些的,我首先想到的总是《一个人的战争》,我最后想到的也是它,于是我权且把它作为成名作来回忆一番。
回忆这个词使我感到它的写作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站在一九九六年的夏天眺望一九九三年,眺望和回忆都让人感到做作,就像离家不过十里就称之为流浪一样。但在我的感觉中,它的遭遇太多,满满地充塞在这几年中,它的遭遇拉长了时间,使我无端地感到沧桑和隐痛。回忆这个姿势使我把它所经历的事情推到远处,而对远处的凝视会使我安静下来。
相对于这部小说发表后的经历,它的写作过程简单之极。事先没有酝酿,在动笔写作的前一天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写这样一部作品,在这之前我刚刚写了《瓶中之水》和《回廊之椅》,我感到自己重新找回了对小说的语言感觉,由于新闻写作的规范,有一段时间我差不多丢失了文学的语感。语感的到位使我觉得自己正坐在滑梯口上,有一种往下滑的冲动。于是在九三年四月的一天,我觉得自己很想写一部长一些的作品,于是我提起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女孩多米犹如一只青涩坚硬的番石榴,结缀在B镇岁月的枝头上,穿过我的记忆闪闪发光。这是当时的开头。这个开头使我感到小说将会十分顺利地一气呵成。后来确是如此,手稿干净整洁,除了章节的前后顺序作了一点调整,所有的语句几乎很少改动。我当时觉得它们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水滴,圆润而天然。
当时我的现实处境十分糟糕,高度的精神压力和超常的工作忙乱,但它们没有侵入我的作品。写作使我在瞬间飞离现实,它是我免受致命伤害的飞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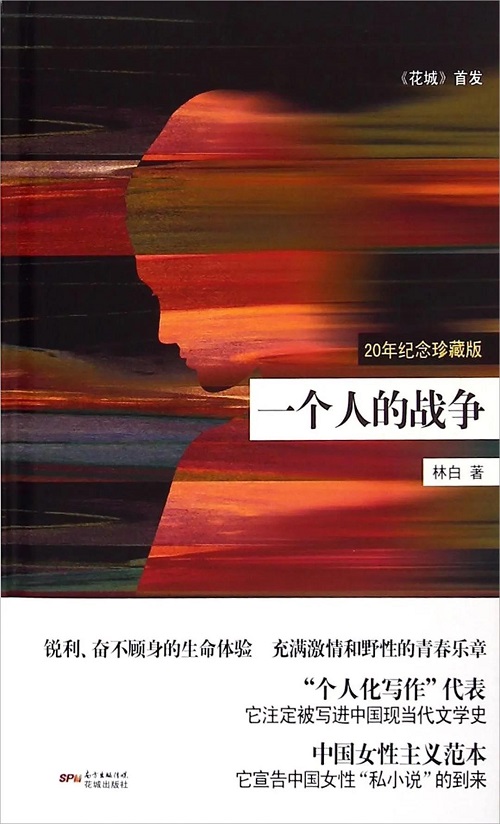
20周年纪念版,花城出版社2015年
《一个人的战争》发表在九四年第二期的《花城》杂志上,同年由朋友介绍到西北的一家出版社,我担心西北地处偏远,设计不了我满意的封面,特意在北京请青年封面设计家旺忘望设计了封面,并用特快专递寄去。没想到他们轻易就否定了这个设计,代之以一幅看起来使人产生色情联想的类似春宫图的摄影作封面。关于春宫图一说,并不是我一己的夸大和偏见,而是报刊上评论家和读者的原话。面对我的诘问,责编强调说这是一幅由著名摄影家拍摄的著名的摄影作品。这还不算,这本书内文校对粗疏,最严重的一页差错竟达十五处,这种种谬误使我十分气愤,出版社通过责编作了一些道歉和解释,并保证马上换一个,出一个订正版,我接受了。但我一直没有等到这个版本。在我的一再催促下,才在一九九五年十月份收到一份同意我撤回专有使用权的函件。这之后曾有河北的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此书并已签订了合同,但几天之后又因故解除了,我至今也没拿到合同上规定的赔偿。
这部长篇自一九九四年发表以来,一直经受着毁誉参半的命运,前不久我还看到对它责难的文章,言过其实,极不负责。但使我更难过的还是它在出版上的不顺利,到现在(一九九六年六月),我还不能知道《一个人的战争》的单行本是否能顺利出来。这种心情就像自己的孩子长大了还没有找到赖以生存的职业一样。这是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孩子,但它总是四处碰壁,遭人误解。它本是好端端的一个孩子,五官端正,不脏不臭,但却被无端穿上了一件恶劣的衣服,使人看一眼就产生误解,这种误解使它平白无故地遭受污辱。这样的结果使我心怀疼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