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作雷:《三体》中的“朴素主义社会”与“最初的人”

闫作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发表论文多篇。
《三体》中的人类未来社会,其实是当下某些人宣称的终结了历史的社会的延伸,然而在宇宙文明之战中,这个“美丽新世界”的文明法则成为人类生存 延续的障碍。《三体》通过设置地球与三体世界的生死战,直达人类“最后的社会”。在自然状态的宇宙中,“最后的社会”中的“最后的人”如何应对这场生存危机?基于此,《三体》从宇宙视角审视人类文明,揭示现代性弊病的同时,试图超克“最后的社会”“最后的人”。
“地球往事”三部曲设想的“最后的社会”,具有宫崎市定所谓的“文明主义社会”的特征,它导致了一种烂熟的文明病。在与三体世界的对比中,在对人类“最后之觉悟”的描绘中,《三体》勾勒了一个“朴素主义社会”的轮廓,以及“睁眼看宇宙”、具有强烈斗争意志的“最初的人”的形象。引入“朴素主义”,不是使其与“文明主义”截然对立,而是带来反思“现代社会”的契机。
一、科技与道德
《三体》要上演这出社会实验的戏剧,必须跳出人类文明自身的经验。只有将人类的“文明主义社会”置于自然状态的宇宙中,才能在危机时刻暴露人类文明的弱点,让“最后的社会”“最后的人”的局限一览无余。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先破除普遍主义的宇宙道德观,因为一个可以结束自然状态的人道主义宇宙,仍不过是人类文明自我想象的延伸。
《三体》是从叶文洁的故事开始的,但若仅从她的遭遇来看,类似故事在新时期初期的科幻中已有不少。比如《三体》后记中提到的《月光岛》。读过《月光岛》会发现,两部小说女主人公的经历几乎完全一样。《月光岛》的故事同样发生在1960年代末。主人公孟薇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女儿,父亲被诬为间谍隔离审查,母亲因此心脏病发作去世,她本人也被考上的大学拒收,无奈之下跳海轻生;后被梅生救活并与之相恋,但却因家庭背景连累了梅生。小说最后,绝望的女主人公跟着月光岛上的外星人,“自由的天狼星人”,离开地球飞往天狼星。与叶文洁一样,与外星人的接触使孟薇获得了从地球之外审视人类、人性的视角,她深深同意天狼星人对地球人的评价:“在我们看来,地球人还未最终脱离动物的状态,野蛮!自私!褊狭!虚伪!怯懦!残暴!粗野!”在离别之际,孟薇已认同天狼星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并在精神上将自己作为天狼星的一员,在给梅生的永别信中写道:我将永远“离开你们的地球,到那个遥远的星球上去”。

《月光岛》
发表于1980年的《月光岛》[1]提供的通过对外星人的想象和向往来摆脱人类危机、治愈同类人施予的伤痛的尝试,在当时其他科幻中也能找到。比如一篇小说写地球不再适宜居住,人类的太空飞船在茫茫宇宙中找到一颗存在智慧文明的玛雅星,这颗星球科技发达,没有压迫、剥削和不幸,“到处是繁荣昌盛的景象”。当地球使者向玛雅王表达移民的想法时,得到的回答居然是:“没问题,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2]另一篇小说写遥远的SZ1350星球人极富同情心,专门派UFO来地球搭救那些陷入绝境之人。SZ1350星球人仿佛救世主、正义之神[3]。确实,如刘慈欣所说,新时期初期的科幻小说,“外星人都以慈眉善目的形象出现,以天父般的仁慈和宽容,指引着人类这群迷途的羔羊。金涛的《月光岛》中,外星人抚慰着人类受伤的心灵” [4]。
今天已很容易发现这些科幻中的文化政治寓言。外星人通常以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形象出现,“飞离地球”无不是离开中国、移民到更“先进”文明的隐喻。在冷战松动的背景下,新时期初期的人道主义思潮、人性论从地球扩展到了全宇宙。而当充斥丛林法则的市场经济到来时,这一美好想象只能土崩瓦解,1980年代言情小说中的“白莲花”纷纷让位给新世纪之后的“黑莲花” [5]。《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也正是这个新时代现实的折射。
叶文洁的故事在《月光岛》中已初露端倪,孟薇再向前走一步就是叶文洁。然而,刘慈欣并不是要重复书写“伤痕科幻”的故事,相反,正是要与《月光岛》等科幻小说对话。《三体》通过反思叶文洁的思想和选择,打破宇宙人道主义的幻想,发出“刘慈欣之问”:“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往小处说,这是科幻迷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往大处说,它可能关乎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 [6] 进而重审科技与道德的关系。事实上,支撑新时期宇宙共同道德观念的另一个重要想法,是一个文明的道德水平与其科技发展程度成正比。
刘慈欣打碎普遍主义宇宙道德观的起点,即是展现叶文洁思想行为的可怕后果。叶文洁对人类彻底绝望的原因是“文革”伤痛、黑暗人性及生态灾难。值得注意的是,叶文洁回复三体人并邀请其占领地球的时间是1979年,此时叶哲泰已获平反,她本人也即将回清华大学教书,但她“拒绝忘却”,继续用“理性的目光”审视“那些伤害了她的疯狂和偏执”[7](1,200),她要三个已沦落到社会底层的前红卫兵忏悔道歉,不接受她们借用的电影《枫》的解释。恰恰在这个“人性复归”时刻,她精心策划谋杀了“红岸”政委雷志成,而且不惜让她无辜的丈夫一起陪葬,这与她母亲背叛叶哲泰没多大区别;她关于人类文明需外力介入的执念,与她妹妹叶文雪对理想主义的坚守也大同小异。说到底,叶文洁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8],她的精神结构是那个时代形塑的,“需要将自己的才华贡献给一个伟大的目标”(1,201)。意志顽强、科技发达的三体世界的出现,对于她,仿佛意义失落的“潘晓”一下子找到了替代性的价值目标。“冷静、毫不动感情地做了(指杀害雷志成与杨卫宁)。我找到了能够为之献身的事业,付出的代价,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不在乎。”(1,216)那些“别人”中也包括让她感受到温暖的人们,如她生杨冬时照料她的齐家屯的朴实百姓。这同样也是一种“疯狂和偏执”。受到失去“人性”伤害的叶文洁,变本加厉地照搬了曾伤害过她的那些行为方式。叶文洁对三体人幻想的自然延伸即是人权高于主权。“三体”游戏玩家聚会,讨论的重要话题就是人类社会的主权与人权问题,如果赞同西班牙殖民者介入“黑暗的”阿兹特克帝国,就会被地球三体组织(ETO)接纳为同志。这是ETO成员的基本共识。但反讽的是,作为精神领袖的叶文洁根本无法管控组织的分裂,拯救派和降临派复制了“文革”时期红卫兵组织的发展逻辑,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斗争。降临派对拯救派一些成员进行肉体消灭,为了迎接三体人主持的最后审判,其下设的“环境分支”专门制造“环境灾难”,“生物和医疗分支”专门制造“滥用抗菌素灾难”(1,184~185),至此已完全背离环保主义和“物种共产主义”的初衷。即使温和一些的叶文洁,也同样相信宇宙正义和普遍的宇宙道德,相信三体世界的人道主义光辉将照亮地球的黑暗,拯救人类于水火。在她那里,科学意味着德行,科技并非中立的“事实”,而是一套价值观念:
审问者:你为什么对其(三体人)抱有那样的期望,认为它们能够改造和完善人类社会呢?
叶文洁:如果他们能够跨越星际来到我们的世界,说明他们的科学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一个科学如此昌明的社会,必然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
审问者:你认为这个结论本身科学吗? 叶文洁:......(1,260~261)
作为“事实”的科学同时也是“价值”之源,这个观念并不新鲜,它在近代科学诞生时期的思想家和现代落后国家的人们那里非常常见。培根(1561—1626)设想的科学乌托邦“本色列”的终极目的是在全世界收集、传播科学之“光”,其科学庙“所罗门之宫”的规章仪式类似于宗教,在这里,发明家享有圣徒的荣誉,科学促进繁荣,也是德行之基[9]。圣西门(1760—1825)主张未来社会应建立以万有引力为基础的科学宗教[10],以牛顿代替耶稣行使上帝的精神权力,让牛顿“教导和命令一切行星上的居民”,同时以“牛顿协会”代替罗马教廷[11]。192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科玄之争”中的科学派,比如吴稚晖、唐钺等,皆认为科学可提升人类公德[12],产生“大我”,导向“人类大公”[13],这些看法都或隐或显将科学昌明程度与 社会道德水平相联系。
与继承了上述观念的新时期科幻相比,“地球往事”三部曲展现了一个零道德的宇宙,科技与文明体的道德不存在正比例关系。叶文洁最终对宇宙中科技与道德的关系有了全新领悟,并在女儿墓前把宇宙社会学公理告诉了罗辑。叶文洁的很多观念来自新时期,但在最后一刻,叶文洁超越了孟薇,超越了自我,甚至超越了1980年代。另外,《三体》对ETO成员的年龄有过一次说明,ETO成员主要是中老年社会精英,年轻人非常少(1,168)。或许,在丛林社会中野蛮生长起来的年轻人,有着拒斥童话般宇宙人道主义的潜意识[14]。出生于1980年前后的罗辑,这个公元世纪的年轻人,一个学术混混,即将开启其“明心见性”(吴飞的用语)的未来之旅。
二、朴素与文明
三体世界对地球的入侵,终结了普遍主义的宇宙道德观。地球被置于宇宙的黑暗森林中,一个不可能摆脱自然状态的丛林。人类“最后的社会”中的“最后的人”被迫迎接末日之战,与三体世界对决。
面对整个文明的生死存亡,人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以整体应对危机,个人应葆有怎样的精神状态,以及怎样处理个人与集体、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应该是首要议题,毕竟地球处于紧急状态。《三体》第一、二部也曾涉及对人类未来社会形态的想象。比如ET0成员潘寒基于环保理念和“温和技术”,设想并付诸实践的“新农业社会”——“中华田园”。但随着ETO被剿灭,该社团不复存在。再如雷迪亚兹为对抗资本主义,并吸取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训,在委内瑞拉建立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南美洲各个国家纷纷仿效,一时间,社会主义在南美已呈燎原之势”(2,84)。“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从《三体》对未来社会的设定看,应消失于“大低谷”之后。同时,小说悬置了中国的社会形态在未来几百年中的潜在可能。而危机初期的“技术公有化运动”惨遭失败,“它使人们认识到,即使在毁灭性的三体危机面前,人类大同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2,31)。“战时经济大转型”产生了带有军事色彩的社会,导致了“大低谷”。这样,刘慈欣便堵死了人类未来社会形态多元化的可能,只保留了唯一一种社会形态。此社会形态即“高度民主文明的高福利社会”(3,217)。自“大低谷”结束到掩体纪元300多年,人类生活在这样一个“文明主义社会”中,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提倡的人文主义原则得到彻底实行。这个历史终结处的人类社会,崛起于危机纪元后期,鼎盛于威慑纪元,衰落于掩体纪元。危机纪元后期的信条是“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2,309)。这个基于私有制的“美丽新世界”曾一度让罗辑“泪流满面”,但在末日战役中证明不过是不堪一击的花瓶。“威慑纪元弥漫着自由和懒散的享乐主义”(3,238),“文明主义社会” 发展到极致,“爱”是这个社会最可贵品质。文艺的美学风格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温馨的宁静和乐观”,批判性、革命性艺术消失得无影无踪(3,102~103)。《三体》以公元男人的视角,称其为没有“男人”的女性化时代。
作为人类社会的对比,小说也写到与地球文明接触后,三体世界发生的变化。总体来说,三体世界更具历史连续性。以地球时间算,三体世界从收到地球信息的1975年到被光子摧毁的2275年(广播纪元5年),300年间经历了两个阶段:威慑纪元之前的“高科技+专制社会+本土文化”阶段,之后的因与地球和平交往而产生的“高科技+不明社会形态+混合文化”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思想透明的三体人学会了地球人的欺骗和计谋。人类社会面对危机制订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计划,而学会了地球人谋略的三体人的计划,小说并未正面描写。《三体》的基本设定是:地球人惧怕三体世界的高科技,三体人则惧怕人类文化。人类一直有一种文化优越感,三体世界对地球“人文主义”这个最可怕的武器,一直是防范的。三体人认识到,“文明主义”可以瓦解三体,但同样可以摧毁人类自身,依据这个认识,三体世界实际上也制订了针对地球“文明主义社会”的计划。于是,“朴素主义”与“文明主义”的竞争在两大文明间展开。
最明显的莫过于三体世界的“反射文化”计划。1379号监听员对地球文明的向往,让三体的“宣传执政官”意识到,“地球文明在三体世界是很有杀伤力的,对我们的人民来说,那是来自天堂的圣乐。地球人的人文思想会使很多三体人走上精神歧途”(1,282),所以三体元首制定了严格限制地球信息流入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地球文明对于三体高层和曾经的三体人来说并无新意,因为自由民主的文明主义社会在三体世界也曾存在过:“你向往的那种文明在三体世界也存在过,它们有过民主自由的社会,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你能看到的只是极小一部分,大部分都被封存禁阅了。”(1,268)因这种文明在宇宙中的脆弱性,三体世界摒弃了这一社会形态。所以对三体人来说,如果想要这种社会,无须自外输入,只需将自身封存的遗产敞开就可以了。
因此可以肯定,威慑纪元时代,三体世界接受地球文化有一定的欺骗性;反向输入到地球的“反射文化”(三体人依据人文主义原则创作的文艺作品)正是三体宣传部门的计谋,目的是麻痹地球人,而他们自己对这种文化一直是有保留的。三体世界确实接纳了部分人类价值观,思想自由促进了科学进步。这或许是真的,但至于说三体世界向地球通报,三体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变,半个世纪中爆发了多次革命,其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与地球越来越相似,基本可以判定是为了迷惑人类。
首先,如果三体也变成了地球上那个丧失战争意志、没有“男人”、弥漫着“爱”和人道主义的文明主义社会,就决不会在程心接任执剑人时突然攻击地球,如果两个社会已经高度相似,执剑人也没必要存在,和平就会降临(程心就是这样认为的),但事实证明,六个水滴一直随时待命,攻击—占领—灭绝三部曲,是三体人蓄谋已久的计划。其次,如果三体已高度民主,是否攻击地球,应该由三体人集体投票决定,但显然在那关键时刻,攻击命令是三体元首直接下达的。三体世界有过因“文明主义社会”毁灭的教训,不会毫无反思地接受地球文化。最后,真实的三体文化究竟什么样子,人类其实不得而知,“三体世界本身仍然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那个世界的细节被传送过来。三体人认为,自己粗陋的本土文化现在还不值得展示给人类”(3,104),而“粗陋的本土文化”对三体人来说才是重要的,才是需要隐藏的,他们清楚,输入地球的“反射文化”是致命的麻醉剂,它将会在人类“最后的社会”中塑造一个又一 个“末人”。
三体世界并没有完全人文化,而是保留了“朴素主义”传统,尽管这是一种冷酷的“朴素”,却是历经无数次毁灭和重生的三体世界的主动选择。在恐怖的威慑平衡中,三体在“朴素”基础上引入“人文”,在集中基础上引入民主,以便在威慑纪元形成对地球的竞争优势。这一变化让三体世界更有弹性。至此,三体世界有了“菊”与“刀”两副面孔。而地球人则只有一副姣好但也柔弱的文明主义面孔。相对于地球世界总是摇摆于两个极端(要么民主,要专制;要么人性,要么兽性;要么精英,要么庸众......),三体世界开始注意文明与延续、朴素与人文、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平衡。三体世界“菊”与“刀”的两面,由三体世界的大使智子完美体现出来。
智子是一日本少女形象,刘慈欣的这一设定(包括对三体世界“耻感文化”的描写),意味深长[15]。两个文明和平交往时的智子,身穿素雅和服,头插小白花,痴迷茶道,沉醉于“和敬清寂”之境界。这位少女大使可爱又礼貌,无害而美好。“这时,程心已经忘记眼前是一个外星侵略者,忘记在四光年外控制着她的那个强大的异世界,眼前只是一个美丽柔顺的女人。”(3,105)但这只是一面。当水滴疾速向地球飞来,程心扔掉引力波发射器之际,智子已与之前判若两人,“她身穿沙漠迷彩”,围着“忍者的黑巾”,“背后插着一把长长的武士刀”,“英姿飒爽”中透着“美艳的杀气”(3,144)。为了恢复保留地澳大利亚的社会秩序,智子直接诉诸暴力,用滴血的武士刀教训人类:“人类自由堕落的时代结束了,要想在这里活下去,就要重新学会集体主义,重新拾起人的尊严。”(3,158)三体人并不敬畏地球的“文明主义社会”, 相反,是深深地鄙视。

智子形象示意图
所谓“朴素”并不等同于专制(专制并不意味着朴素),也不是不要文明,而是要避免一种烂熟的文明病。正如宫崎市定对“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的观察:
文明社会的先进文化影响着周围的野蛮民族,同化着周围的野蛮民族。然而,野蛮民族在文明化的进程中并不是没有任何牺牲的,他们失去的往往是本民族最为宝贵的东西。我将这种最为宝贵的东西叫作“朴素性”。文明社会表面上繁花似锦,香气四溢,但其内部却不乏光怪陆离,诡计多端。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很难察觉到的,而尚未受到文明的毒害、尚具纯真性的野蛮民族从外部却能看得非常真切。[16]
宫崎市定对元朝蒙古人接受喇嘛教和中原文化后“野性的朴素”的消失非常遗憾,认为那些东西“伤害了政治”[17] 。相比于清王朝贪图安逸丧失了朴素性,相比于欧洲社会“也在不知不觉中向纯粹的文明主义社会变质”,其弊端已在毒害社会,宫崎市定骄傲于日本的“朴素主义精神”尚未泯灭:“我国的国民成功地将科学移植到了日本,以至于最终掌握了如何使文明生活和朴素主义相互协调的关键。”在他看来,明治维新的成功正是做到了朴素与文明的平衡,而“建立一个近乎完整的朴素主义社会”,正是“东方社会对我们的希望”[18]。宫崎市定的观点虽然可被用来论证日本入侵东亚文明主义社会的所谓正当性,但不妨碍文明与朴素辩证法的启示意义。
《三体》第三部写威慑大厅中的罗辑,目光威严,“穿的整洁的黑色中山装格外醒目”(3,131)。当罗辑决定穿“黑色中山装”践行使命,他一定悟出了朴素与文明的辩证法,这是真正“明心见性”的时刻。他或许从这件已消失了两百多年的衣服中,感受到一股刚健质朴的力量。穿“黑色中山装”的罗辑,“我将无我”,凛然不可侵犯,以剑客的目光逼视着三体世界,“这目光带着地狱的寒气和巨石的沉重,带着牺牲一切的决绝,令敌人心悸,使他们打消一切轻率的举动”(3,132)。在沉默中坚守了半个世纪的罗辑,终成不可战胜的圣斗士,“他的胜利无人能及”(3,134)。“黑色中山装”并非圣物,没必要夸大,它仅在象征意义上联系着一个遥远的朴素主义时代,但却也展示着与病态文明主义 及极端个人主义决裂的姿态,三体世界一定能深得其味。
“地球往事”三部曲让地球处于紧急状态,然后顺着“人性”向前推,投其所好,给出最好的因,结出最坏的果,以宇宙视角观察着小小地球的“最后的社会”: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也是从当下推演未来,反思“现代社会”,在历史的终结处,想象一种容纳“朴素主义社会”的可能,在“朴素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辩证中开出新路径。逃向太空的“蓝色空间”号应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章北海的决定是:既非三体世界的专制社会,也非地球的“文明主义社会”,而是尝试建立一个能平衡个人与集体、民主与集中关系的社会,“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实践和探索的过程才能为星舰地球找到合适的社会模式”(2,405)。如此,历史并不必然非此即彼,就没有终结。
三、“初人”与“末人”
福山意义上的历史终结后的社会,就是一个“文明主义社会”。宫崎市定在与“朴素人”的对比中归纳“文明人”的特征:“文明人有文明人的教养,朴素人有朴素人的训练;文明人善于思考,朴素人敏于行动;文明人是理智的,朴素人是意气的;文明人情意缠绵,朴素人直截了当;文明人具有女性的阴柔,朴素人具有男性的刚强。更进一步说,文明人崇尚个人自由主义,朴素人囿于集体统制主义,总之,在几乎所有的方面,两者都表现出了相互对立的特征。”[19]而卢梭所谓科学与艺术腐蚀尚武精神、败坏风俗,也是在说“文明主义”的负面作用,背后也联系着两种社会两种人[20]。如果说宫崎市定、卢梭的分析稍显粗陋,那么福山则试图从哲学、心理学层面对“最后的社会”中“最后的人”进行思考。
历史终结之后,“自由社会最典型的产物”是一种“布尔乔亚的新型个体”[21]。这些“最后的人”专注于身体安全与物质满足,缺乏共同体意识,自私自利。这是福山赞美历史终结的最大障碍。“最后的人”,马克思已从“左”的方面揭露其虚伪,但福山认为最难以回避也最难反驳的是尼采从右的方面的无情批判。尼采认为“现代社会”的造物是一群发明了“幸福”的“末人”,他们的道德、教养和平等意识显示的是奴隶本性:
他们有某种可以自豪的东西。那种使他们自豪的,他们把它叫做什么?他们称之为教养,这使他们显得比牧羊者优越。
因此他们不爱听对他们“轻蔑”的话。因而我要就他们的自豪来谈谈。我要对他们讲述最该轻蔑的人:末等人。[22]
没有牧人的一群羊!人人都要平等,人人都平等:没有同感的人,自动进疯人院。[23]
“末人”固守他们发现的道德价值,失去了创造新价值新道德的超越性。即使在福山那里,“最后的人”也不过是“丧失了激情的自由人”。一切都得到满足的“后历史动物”,突然置身于自然状态下的宇宙文明之战中,置身于人类文明可能毁灭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会如何应对?《三体》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展开社会实验。《三体》中,“高度民主文明的高福利社会”中生活的“最后的人”,奉行“人文原则第一,文明延续第二”(2,335),没有斗争意志,以自我保存、物质生活与道德原则为全部满足,而一旦面临灭顶之灾,又只会祈求于救世主和宗教,冷漠理性中潜藏的却是最大的非理性。抽象“爱”的背后又是牢不可破的个人主义。这些观念与自三体世界输入的“反射文化”一起,织成一张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天罗地网。这就是为什么刘慈欣认为《1984》中的社会要好于《美丽新世界》中的社会的原因,因为前者通过改变还有恢复人性的可能,而后者则以满足人性的名义失去了人性[24] 。
三体世界在威慑纪元的另一个计划可称为“末人计划”,准确地说,是要在“末人”中寻找代理人,通过干预执剑人选举确保“末人”当选。因为“最后的人”失去了行动力,更不愿承担责任,所以第二任执剑人在七个“公元人”之间展开,六个维德那样不择手段的恶徒,一个善良有爱的天使。在这一时刻,智子出来鼓动程心竞选:“我们女人在一起,世界就很美好,可是我们的世界也很脆弱,我们女人可要爱护这一切啊。”(3,106)。而六大恶人却劝程心不要参选:“在公众眼中,最理想的执剑人是这样的:他们让三体世界害怕,同时却要让人类,也就是现在这些娘儿们和假娘儿们不害怕。这样的人当然不存在,所以他们就倾向于让自己不害怕的。你让他们不害怕,因为你是女人,更因为你是一 个在她们眼中形象美好的女人。这些娘娘腔比我们那时的孩子还天真,看事情只会看表面......现在她们都认为事情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宇宙大同就要到来了,所以威慑越来越不重要,执剑的手应该稳当一些。”“难道不是吗?”程心问。(3,108)这里,刘慈欣并非要触犯女性主义的政治正确,而是以极端方式揭示“末人”的幼稚病。然而让人感到压抑的公元男人,反而激发了程心参选的决心。当然,程心当选,威慑失败。而这一切都在三体世界的预料之中:“你做出了我们预测的选择”(3,144)。“宇宙不是童话”(3,145)。最终,人类在计谋和欺骗上也输给了三体人。
在自然状态的宇宙中,放弃寻求承认的斗争,就是甘居奴隶地位,然而更可怕的是,宇宙文明博弈是零和博弈,奴隶本身会被肉体消灭,这意味着宇宙文明间不存在黑格尔阐发的那种在主奴辩证法中生成历史的机会。《三体》设置了这个生存死局,堵死了奴隶“返回自身”成为“自为存在”的可能[25]。宇宙的自然状态,就是你死我活、做奴隶而不得的状态,它无法像人类那样,在地球自然状态中经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悲剧后,达成社会契约,进而创建一个保护他们的利维坦[26]。宇宙智慧文明的差异首先是物种的差异,人类的“文明主义社会”在宇宙中可能不过是一个特殊存在。
这里顺便提及一个问题,就是对《三体》中“高科技+专制社会”这一社会形态的质疑,认为高科技不会与三体世界这样的专制社会并存,“长老的二向箔”显示了刘慈欣未来乌托邦想象的贫乏[27]。这个话题很有意思。但对它的分析不能仅局限于人类经验。要考虑到,物种的生理差异是科技发展程度的变量。《乡村教师》中的碳基联邦人,他们科技的发达与其信息传播和接收方式、记忆可遗传等有巨大关系,这意味着他们更智能,在他们眼中,人类的生理构造非常原始,即使建立了文明型社会,科技也不可能走太远。同样,三体人的信息交流方式也有其优越性,而且记忆可部分遗传。歌者所在的大神级文明,“长老+二向箔”,但歌者有自我意识,只不过他的生理结构使其可以删掉危害生存的思想,他们的文明词典中可能根本没有“专制”、“民主”这样的词汇,但这不妨碍他们科技发达。置身于自然状态的宇宙,人类自身经验是需要超越的,这应该是“地球往事”三部曲的主题之一。即使在人类文明中,辨析此问题也需要政治经济学视野。“中东石油帝国”那样的社会才是专制,还是说一切与欧美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都是专制?按照这个逻辑,印度的科技水平应该远远高于中国才是。刘慈欣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确实混乱不堪。思想自由可以促进科技进步,但思想自由必须辅以利益诉求,在近代世界,是无“思想”的“奴隶”发明了技术,再经科学的资本化,这才促进了科技进步[28]。市场社会欲望驱动的竞争机制确实可以刺激满足人性的创新,尤其在民用领域,但当今时代重大科技突破越来越取决于资金投入及其背后的科研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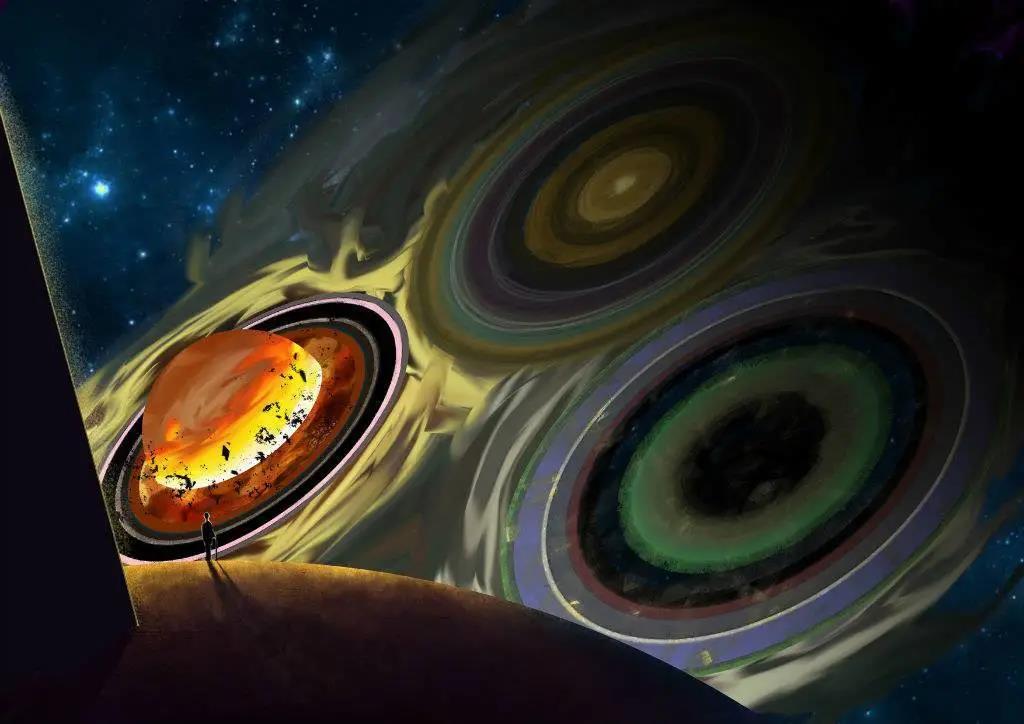
二向箔示意
那么,如何超克“最后的人”?对于这些幸福的“末人”,尼采大呼“我教你们做超人”,“创造新事物和一种新的道德”[29],“人是应该被超越的某种东西”,“一切生物都创造过超越自身的某种东西:难道你们要做大潮的退潮,情愿倒退为动物而不愿超越人本身吗”[30]?但这种疯狂的权力意志与现代社会的平等诉求背道而驰。福山为了拯救“最后的人”,将尼采的超人转化为类似贵族精英的“优越意识”,以平衡布尔乔亚的“平等意识”,但其所谓的“优越意识”不过集中于艺术、体育竞技等去政治化方面。为了提升“最后的人”的共同体意识,福山又诉诸黑格尔的“最初的人”。
“最初的人”为寻求他人承认而斗争,斗争结果是主奴关系的确立。在黑格尔那里,主人是独立的自为存在,而奴隶则为对方而存在[31],主人为捍卫名誉冒死而战,奴隶则屈服示弱,因而主人更有自我意识更有人性,奴隶则未摆脱动物状态,所以导致这个承认也是不完满的:主人获得的不过是奴隶的承认,而奴隶则处于不平等状态。但其后,奴隶通过劳动“返回自身”,有了平等诉求和自由意识,通过斗争建立的自由国家,主人和奴隶都得到了承认,所以自由国家保留了主人的高贵和奴隶的劳动。历史因此终结。而历史终结处,正是马克思、尼采批判的起点。福山对黑格尔的这番科耶夫解释,是为了借助“最初的人”唤起布尔乔亚丧失了的斗争激情,一种“战争唤起的德性和雄心”[32],因为“最初的人”超越动物本能,超越自私自利,可以让布尔乔亚具有共同体意识。但“最初的人”的斗争也可能带来破坏性,所以福山小心翼翼将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三体》中的“最初的人”不同于黑格尔的“最初的人”,因为他不寻求主奴关系;也不同于宫崎市定的“朴素人”,因为他也有“文明人”的一面;更不等同于尼采的“超人”,因为他不蔑视大众。只是在最低限度上,与他们共享着某些相似的精神品格。《三体》中“最初的人”,是在自然状态的宇宙中,在危机时刻为挽救地球文明,以非道德的方式开创一条生路,在星辰大海中延续人类文明的人;是“睁眼看宇宙”,超越人类文明经验,认识到宇宙残酷真相,为寻求其他文明的承认而斗争并不惜付出生命的人;是具有顽强意志,在文明冲突的紧急状态下触犯布尔乔亚的道德信条,创造新道德新价值的人。“最初的人”的斗争意志与超越意识不是指向同类,而是针对外星入侵者,与其说他是救世主,毋宁说是面对宇宙神秘黑色方碑的好奇古猿。“最初的人”是英雄与恶魔的混合体,野蛮凶猛,疯狂有力。
执剑人交接时刻,罗辑如“孤独的铁锚”般,端坐于“像坟墓一样简洁”的威慑大厅。十分钟后,程心走进大厅。程心看到时间仿佛在这“死寂”的大厅中停滞,她决定首先要让这个“坟墓”“恢复生活的气息”,这里将是她的全部世界,“她不想像罗辑那样,她不是战士和决斗者,她是女人”(3,134)。在这样的对比中,作者将两人斗争意志的差异不动声色地刻画了出来。简洁朴素的大厅,带着地狱寒气的决斗者的目光,以及它们的对立面,构成了一幅“最初的人”与“最后的人”辩论的画面。
在《三体》中,刘慈欣将“最初的人”具象化为一群公元人。维德的出场是从冒犯“文明人”的道德伦理开始的。他问新入职的程心:“你会把你妈卖给妓院吗?”(3,42)这个不择手段前进的人,“就像一块核燃料,即使静静地封闭在铅容器中,都能让人感觉到力量和威胁”(3,343~344),他的威慑度爆表,但他参选执剑人并不是要当独裁者,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的权力欲望,而是出于随时牺牲一切与三体世界一决雌雄的决斗意志;在掩体纪元研发光速飞船并试图让星环集团独立,也是为了他所说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为自由而战,“为成为宇宙中的自由人而战”(3,381)。苦心经营逃亡,在太空中创建星舰地球的章北海亦复如是。罗辑于危机纪元的最后时刻终于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并在半个世纪的执剑生涯中道成肉身。公元世纪还是学术混混的罗辑最终“明心见性”,体会到“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斗争意志,用“最初的人”的威严目光警告三体世界:“地球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说到底,开创历史的“最初的人”,是终结历史的“最后的人”的镜像。
结 语
确实,想象未来的社会形态是最难的,一个超克了历史终结的总体性社会[33],一个令人期待的乌托邦,超出了刘慈欣的想象能力[34]。但顺势而为,在历史终结处演出一场人类生存危机的戏剧,给“现代社会”以警示和痛击,仍有其现实意义。《三体》显示,那个假定的“文明主义社会”,仍然存在政治不平等和经济鸿沟,且充满了布尔乔亚的虚假意识。未来的社会形态不就是在对宣称“最后的社会”“最后的人”的反思批判中创生的吗?
“地球往事”三部曲为了让人类意识到黑暗是生存和文明之母,首先破除了普遍主义的宇宙道德观,然后在宇宙自然状态下布下零和博弈的战场。“睁眼看宇宙”,面对宇宙文明之战,人类文明也是自身的敌人。在此危急时刻,《三体》展开了对“朴素主义社会”与“文明主义社会”、“最初的人”与“最后的人”的辩证思考,一种在“文明主义社会”中容纳“朴素主义”,将“最后的人”转化为“最初的人”的努力。
星辰大海中,开创历史可能性的斗争,生生不息。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6期
注 释
[1]金涛:《月光岛》,《科学时代》1980年第1~2期。
[2]吴狄:《飞向玛雅星》,《科学文艺》1982年第2期。
[3] 潘洪君、张会群:《归来兮》,《科学时代》1981年第3期。
[4][6] 刘慈欣:《后记》,《三体》,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00、300页。
[5] 王玉玊:《从〈渴望〉到〈甄嬛传〉:走出“白莲花”时代》,《南方文坛》2015年 第5期。
[7]刘慈欣:《三体》,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页。第二部、第三部采用的版本为: 《三体2·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三体3·死神永生》,重庆出版社 2010年版。以下引文,页码在括号中注明,不再一一标注。
[8]吴飞:《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版,第40页。
[9] [英]弗·培根:《新大西岛》,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5~37页。
[10] [法]圣西门:《论万有引力》,《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11] [法]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
馆1962年版。
[12] 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
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 唐钺:《科学与德行》,《科学》1917年第3卷第4期。
[14] 陈颀注意到汪淼、叶文洁对待科学与文明关系的不同态度,与他们所处时代有关。作
为年青一代的科学家,汪淼没有“文革”伤痛,没有“河殇”情结,会不自觉认同、 捍卫自己的时代和文明。参见陈颀《文明冲突与文化自觉——〈三体〉的科幻与现 实》,《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
[15]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16] [17] [18] [19] [日]宫崎市定:《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6、120、127~129、26页。
[20] [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21] [32]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176、336页。
[22] [23] [29] [30] [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13、43、7页。
[24]刘慈欣:《我的科幻之路上的几本书》,《我是刘慈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 版,第32页。
[25] 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6] [英]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7] [34] 陈舒劼:《“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 社会形态想象》,《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
[28] 闫作雷:《技术发明主体之争与1970年代的科学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 第1期。
[31] [法]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4页。
[32] 李静:《制造“未来”:论历史转折中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文艺理论与批 评》201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