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俄罗斯文学20年:如何在失重的自由中重启文学的活力
编者按
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
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
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
(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文章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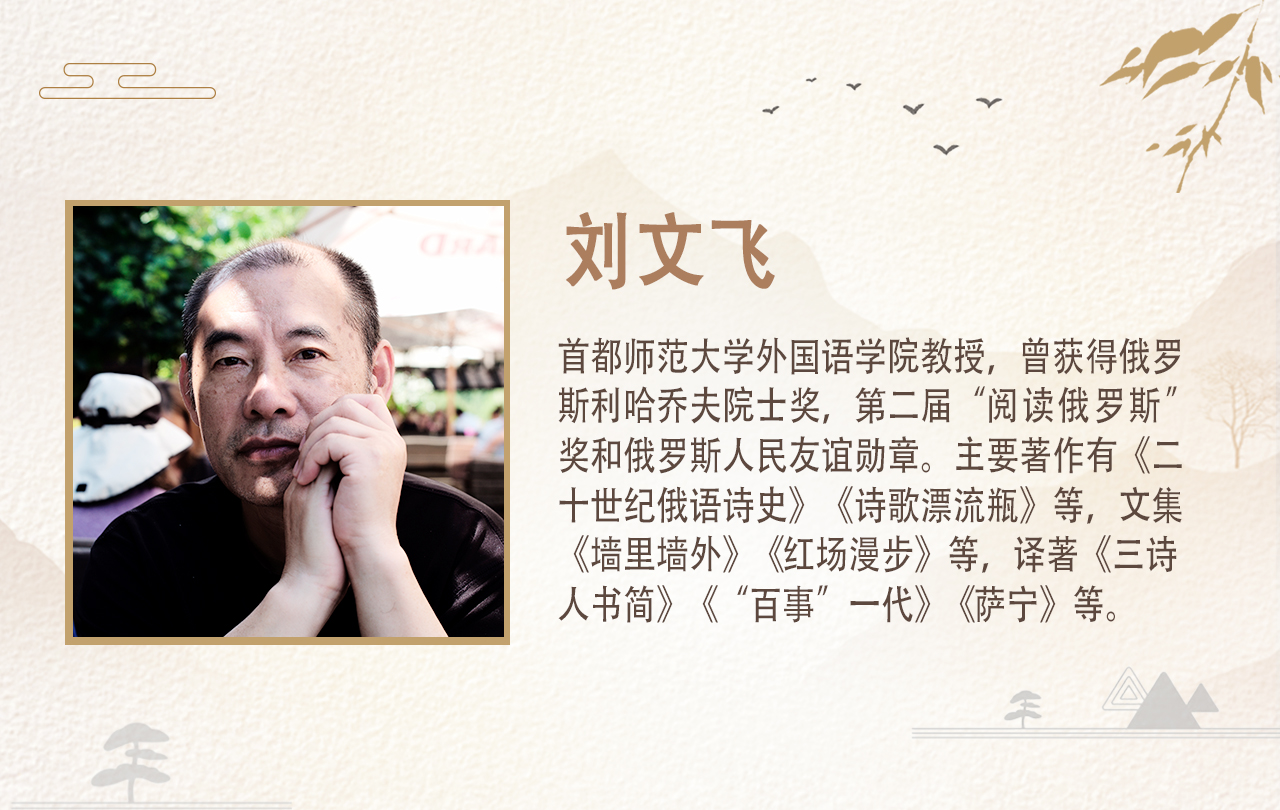
一个新的世纪又过去了五分之一,相对于俄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乃至苏联时期的革命时代和解冻时代,这20年间的俄罗斯文学似乎波澜不惊。但是,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文学传统悠久丰厚的国家,文学生活自然仍在正常持续,在这不长不短的20年里,当代俄罗斯文学也悄然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与苏联文学渐行渐远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官方文学和在野文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置,地下文学浮出水面,境外文学回归故土,20世纪俄语文学的诸多板块终于合而为一,成为“统一的”文学。但这种所谓“后苏联文学”,就整体而言仍建立在与苏联文学的比对关系之上,无论是反乌托邦文学对乌托邦文学的戏仿和解构,还是后现代主义潮流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颠覆,无论是对苏联历史的文学反思,还是对苏联时期文学的历史重估,其实都是以苏联文学为参照系而展开的。进入21世纪后,情况有所不同,当代俄罗斯文学似与苏联文学渐行渐远。
首先,在苏联时期成名的大作家纷纷离世,当代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的直接关联基本告一段落。苏联乡村散文代表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在2001年的去世构成一个信号,标志苏联解冻时期涌现的那一代作家开始退出历史舞台;2008年,作为苏联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最突出代表的艾特马托夫与颇具争议的索尔仁尼琴几乎同时离世;次年,同时被视为苏联时期青春文学和境外俄语文学第三浪潮之代表的阿克肖诺夫去世;2015年,同时被视为乡村散文、战争文学和道德题材文学之代表拉斯普京去世。就这样,20世纪下半期俄语文学中主要几种文学流派的领军人物都先后离去。作家伊斯康德尔2016年去世时,笔者在俄罗斯的报纸上看到诗人叶夫图申科拄着拐杖出席葬礼,便在给诗人的邮件中写道:“如今您已成为苏联时期俄语文学的最后一根拐杖。”诗人回复道:“你称我为文学的拐杖,这个形象很出色,尽管也很悲哀。”第二年,这位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苏联诗人也在美国离世,同年去世的还有年近百岁的彼得堡老作家格拉宁。今年,苏联时期战壕真实派文学的代表邦达列夫也告别人世,这位享年95岁的老作家的去世表明,作为一个群体的苏联作家已不复存在。
其次,关于苏联和苏联文学的争论已不再是当下俄罗斯文学中的时尚内容,之前激烈交锋的双方都渐趋“中立”。苏联解体前后,关于苏联及其历史和功过的评说是整个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关于苏联文学及其历史和优劣的讨论也是一个社会性话题。然而,二三十年过后,随着被讨论对象逐渐隐入历史深处,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被俄罗斯的寡头政治、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环境和气候变化等现实问题所吸引,在解体后步入成年的新一代俄罗斯人,更是把苏联时代及其文学视为遥远的、陌生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即便写到苏联时期的历史,其立场也不再是单一的维护或声讨,而开始采取更为“客观”的立场。比如,生于1977年的女作家雅辛娜在其长篇处女作《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2015)中,就以某种超然的态度写出了历史的悖论。小说描写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去富农化”运动,它虽展示了富农阶层被残酷镇压的悲惨历史,却也让被流放的富农婆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作者在为这部小说的中译本所作序言中写道:“我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时,准备描写的正在于此——关于一个人命运的转变,即一个赴死之人突然喜获第二次生命,而且与第一次生命迥然不同。”失去丈夫、遭到流放的祖列依哈,反而因此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在封闭的囚车,在与世隔绝的林中劳改营,她反而赢得了不止一个男人的爱慕。在一个普遍扼杀个性的时代,祖列依哈的个性反而得以觉醒和释放;在那些非人的生活空间里,祖列依哈反而逐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女人。不去简单地怀念或控诉逝去的时代,而是艺术地再现那个时代生活中的悖论,这是以雅辛娜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作家所体现出的新的创作取向。
最后,作为“苏联文学”基本特征的元素也在逐渐消融。高尔基1934年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报告中,曾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界定“苏联文学”:第一,苏联文学应该是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西方文学和俄罗斯旧文学的新文学;第二,它“不仅是俄罗斯语言的文学,它乃是全苏联的文学”。高尔基所言的苏联文学的第一个特质,显然已被当代俄语作家有意识地消解了,当代俄罗斯文学追求的不是与西方文学的对峙,而恰恰是对接,不是与俄罗斯旧文学的决裂,而恰恰是承续。至于苏联文学的第二个特质,即多民族文学,也在逐渐淡化。苏联解体后,原先的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苏联解体后成立的独联体,在2008年的俄格冲突、2014年的俄乌冲突和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其凝聚力每况愈下。当代俄罗斯文学对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文学的关注度在持续下降,一些少数民族文学的杰出代表、后来用俄语写作的著名作家,如吉尔吉斯族的艾特马托夫、阿布哈兹族的伊斯坎德尔、白俄罗斯族的贝科夫等相继去世后,联系俄罗斯文学和那些民族文学的纽带松弛了,当代俄罗斯文学似乎也在主动放弃作为一种超民族文学的使命和责任。比如,一直用俄语写作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201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俄罗斯文学界就表现得相当克制,既无肖洛霍夫获奖时的欢庆,亦无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获奖后的喧闹,更无当年已开始用英语写作的美籍犹太诗人布罗茨基获奖时所引发的热潮。换句话说,俄罗斯文学界似乎没太把俄语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当成自家人。
当下俄罗斯文学的多元构成
近年俄罗斯文学的最突出特征或许就是其多元化,这既指其多样的题材和风格,也指其更为丰富的文学观念和作者构成。
苏联解体后,广大俄语作家或主动、或被动地与政治拉开距离,作家的“社会代言人”和“灵魂工程师”身份不再得到普遍认同。这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多元化的基础。但在进入21世纪后,作为俄罗斯官方意识形态的东正教信仰开始渗透进俄罗斯文学,其具体表现为:首先,是对俄罗斯文学史的宗教阐释,包括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在内的俄国经典作家都被塑造成虔诚的基督徒,许多经典名著也被置于宗教信仰的语境展开重新解读。其次,当下俄罗斯作家大多承认自己的东正教信仰,并自觉地将其对世界和生活的宗教感受和意识带入其创作,描写宗教史掌故、修道院生活和个人心路历程的作品大量涌现。最后,俄罗斯教会也很重视文学这一“思想武器”:2001—2004年间,杜纳耶夫编写的六卷本文学史著《东正教与俄国文学》陆续出版,完成了从东正教视角对俄罗斯文学的全面梳理和概括;东正教会成立牧首文化委员会,创建专门的文学出版社和图书馆;牧首基里尔和都主教吉洪还亲自写作“文学性”作品。
当下俄罗斯文学的风格如此多元,竟无一种流派能占据首要位置。苏联解体前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曾是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它成为一种文学时尚,迅速填补了苏联文学突然死亡后留下的巨大空白。但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似已显出疲态,老一代后现代作家如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比托夫等相继离世,苏联解体后开始写作的后现代作家如佩列文和索罗金等,其作品中的后现代成分似有所减弱,这两位当下俄罗斯著名小说家的作品,有许多已被译成中文,如佩列文的《“百事”一代》《黄色箭头》《恰巴耶夫与虚空》,索罗金的《暴风雪》《碲钉国》等。与后现代文学形成对峙的,是在两个世纪之交出现的“新现实主义”潮流。新现实主义是一个庞杂的构成,总体而言,新现实主义作家们关注并反映迅速变化的现实,但并不带有预设的立场;他们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作品的情节、形象等往往都是碎片化的、印象式的;他们的笔法是写实的,却并不排斥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段;他们的现实主义同时也具有自传性、主观化、折中性、非崇高化等调性。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有瓦尔拉莫夫、普里列宾、谢钦和沙尔古诺夫等。
新现实主义的兴起同时派生出一个文学现象,即非虚构文学的繁荣。传统的回忆录、旅行记、特写、政论等原本就是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体裁,也曾涌现出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等名作,只不过在当下俄罗斯文学中,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瓦尔拉莫夫在2008—2015年间一口气为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写出七八部传记,如《格林传》《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传》《普里什文传》《普拉东诺夫传》《布尔加科夫传》《格里高利·拉斯普京传》《舒克申传》等,他一直强调,他写的虽然是真人真事,却都是“文学作品”。在一些纯文学奖项中,获奖作品也常常是人物传记,如德米特里·贝科夫的《帕斯捷尔纳克传》、萨拉斯金娜的《索尔仁尼琴传》等。
女性文学的崛起也是新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道景观。一贯由男性作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俄语文学在近20年里发生了某种“性别变化”,一大批女性走上文坛,成为主流作家,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乌利茨卡娅和斯拉夫尼科娃并称为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四杰”。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将戏剧、寓言等体裁因素糅合进小说,扩大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生物学专业出身的乌利茨卡娅善于细腻地解读俄罗斯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她的多部中长篇小说,如《美狄亚和她的儿女》《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忠实于您的舒里克》和《雅科夫的梯子》等,在俄罗斯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并也均陆续被译成汉语。前文提及的雅辛娜,在处女作之后又于前年推出长篇《我的孩子们》,该书中译本也即将由北京十月文学出版社出版。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界还经常爆发关于“女性文学”的争议,如今这样的议论已很少听到,究其原因,或许因为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群体的身份和实力已得到普遍认同,或许由于众多女性作家步入主流,从而消解了俄罗斯文学中传统的性别界线。
大众文学的泛滥曾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文化生活中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一方面,这是苏联解体后文化的一种自然选择,是对官方文化的反拨,是精神解放的象征;另一方面,这也是商业化的结果,是对大众的低俗趣味的迎合。一时间,向来以道德感、社会责任感见长的俄国文学,被以侦探小说、武侠小说、幻想小说、言情小说甚至色情小说为代表的大众文学所取代;曾号称“世界上最喜爱阅读的民族”的俄罗斯人,竞相捧读各类通俗小说。进入21世纪之后,大众文学与严肃文学间的关系出现了某种微妙变化:一方面,大众文学自身的文学水准似有提升,一些靠写通俗文学起家的作家,如阿库宁、鲁宾娜等,已被列入大中学校的文学课教学大纲,成为“新经典”;另一方面,面对严峻的生存压力,一些严肃作家们也开始把“通俗化”当成一种创作追求,把许多大众文学元素掺入自己的作品。严肃文学的大众化和大众文学的经典化,这两个相向而行的潮流构成了当下俄罗斯文学的一道新景观。
既狂欢又寂寥的文学生活
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传统似乎得到延续,每逢大作家的整数生卒年,俄罗斯都要举行全国性纪念活动,普希金的诞辰6月6日,更是被定为俄罗斯语言文学节,是法定假日。当下俄罗斯的作家崇拜现象和文学造神运动似乎并不亚于苏联时期,笔者近20年间多次造访莫斯科,每一次都能看到新树立的作家纪念碑,如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纪念碑(斗争广场,2000年)、肖洛霍夫纪念碑(果戈理林荫道,2007年)、茨维塔耶娃纪念碑(鲍里斯格列勃胡同,2007年)、布罗茨基纪念碑(诺维斯基林荫道,2011年)、特瓦尔多夫斯基纪念碑(激情林荫道,2013年)、奥库扎瓦纪念碑(阿尔巴特街,2014年)、米哈尔科夫纪念碑(厨师街,2014年)等。2018年,莫斯科一下就落成好几座作家纪念碑,如位于索尔仁尼琴大街的索尔仁尼琴纪念碑、位于巴甫洛夫大街的艾特马托夫纪念碑和位于完善街心花园的布尔加科夫纪念碑。在这20年间,还为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经典作家新立了纪念碑。莫斯科如今究竟有多少座文学家纪念碑,恐怕很少有人能数清。莫斯科的纪念碑原本就很多,而其中十之七八都是为作家和诗人树立的。莫斯科人似乎铁了心,要让俄罗斯文学史上的每一位大作家都在莫斯科获得一方立足之地,直到作家们的身影占据莫斯科市内的每一处空地。这样的文学偶像崇拜现象,在其他国家是比较罕见的。
2014年6月12日,普京总统签署《关于在俄罗斯联邦举办文学年》的第426号总统令,将2015年确定为“文学年”,总统令中写明,这一举措之目的,即“在俄联邦范围内激发起全社会对文学和阅读的兴趣”。由国家出面举办为期长达一年的“文学年”,这在人类文学史上可能尚无先例。在一年时间里,由政府和官方机构举办的活动就有千余项,如国际作家论坛、俄罗斯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图书推介活动、国际书展、图书馆之夜、阅读夏令营等,还有众多的作家创作研讨会、作品签售会、文学创作竞赛、诗歌朗诵会等,而各种计划外的民间活动和临时项目更是数不胜数。文学年不仅有充裕的政府拨款、专门的组委会和执委会,还有专门的网站和定期出版物。2015年的俄国文学年成了一个绵延360天的文学读书会,一个高潮迭起的文学狂欢节。
各种文学奖的设立和颁发,当然也是俄罗斯文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节目。苏联解体后,俄联邦政府很快设立了国家级文学艺术奖项,各地政府也有相应的官方奖。但与苏联时期不同,当下俄罗斯出现了许多由基金会、企业或个人出资设立的文学奖项,经过最近二十余年的大浪淘沙,如今已有几种文学奖确立了其威望,如英国布克奖基金会1991年设立的“俄语布克奖”、俄罗斯畅销书基金会2001年设立的“国家畅销书奖”、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2003年设立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奖”、多家银行和企业2005年设立的“大书奖”等,这些奖项的评选和颁发活跃了当今俄罗斯的文学生活,为一些作家提供了雪中送炭的支持,也推出了许多文学新星。
与这些热热闹闹的文学活动形成对比的,是当下俄罗斯作家并不乐观的生存现状。谈起俄罗斯文学当前所享有的空前的创作自由,一位俄罗斯作家曾感慨:“原来过多的氧气也会憋死人的。”这句话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作家之前的光环或桂冠,与他们当时的时代身份是相辅相成的,而变成真正的文学个体户,在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可能性,其影响力和号召力有所下降,甚至有可能“失业”;其次,在俄罗斯作家获得自由的同时,俄罗斯读者也获得了自由,即选择的自由,文学不再是他们获得精神教益、思想快感和审美乐趣的主要来源;最后,曾以“批判”作为限定语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长期以来业已形成包括“伊索式语言”等在内的一套独特的话语方式和表现手段,但到了21世纪,这一套看家本领一时似难以派上用场。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俄罗斯文学在鲜亮外套下的日渐消瘦。在如今的俄罗斯,靠写作为生的严肃作家为数甚少,作家们大多拥有教师、记者、编辑甚至导游、司机、守院人等“第一职业”,他们的作品在报刊上发表,通常是没有稿费的;除少数畅销的严肃作家外,绝大多数作家的作品印数都很少,只有数千册,甚至数百册。创刊于1924年的俄罗斯大型文学杂志《十月》,曾发表过包括法捷耶夫的《毁灭》、马雅可夫斯基的《放声歌唱》、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等在内的大批名著,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发行量曾逾百万,如今却难以为继,该刊主编巴尔梅托娃女士需要为每一期杂志的出版呕心沥血,寻找资助。从2020年起,这份杂志的纸质版已暂停出刊。《十月》这家俄国百年文学名刊的遭遇,折射出了当下俄罗斯文学的生存困境。
如何在俄罗斯文学的辉煌传统下继续创新,如何在近乎失重的自由状态中保持写作定力,如何在市场化条件下坚守个性化的创作追求,这些都是俄罗斯作家在当下所面临的棘手问题。步入21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任重而又道远。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