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松&朱琺:当我们谈妖说怪时,我们在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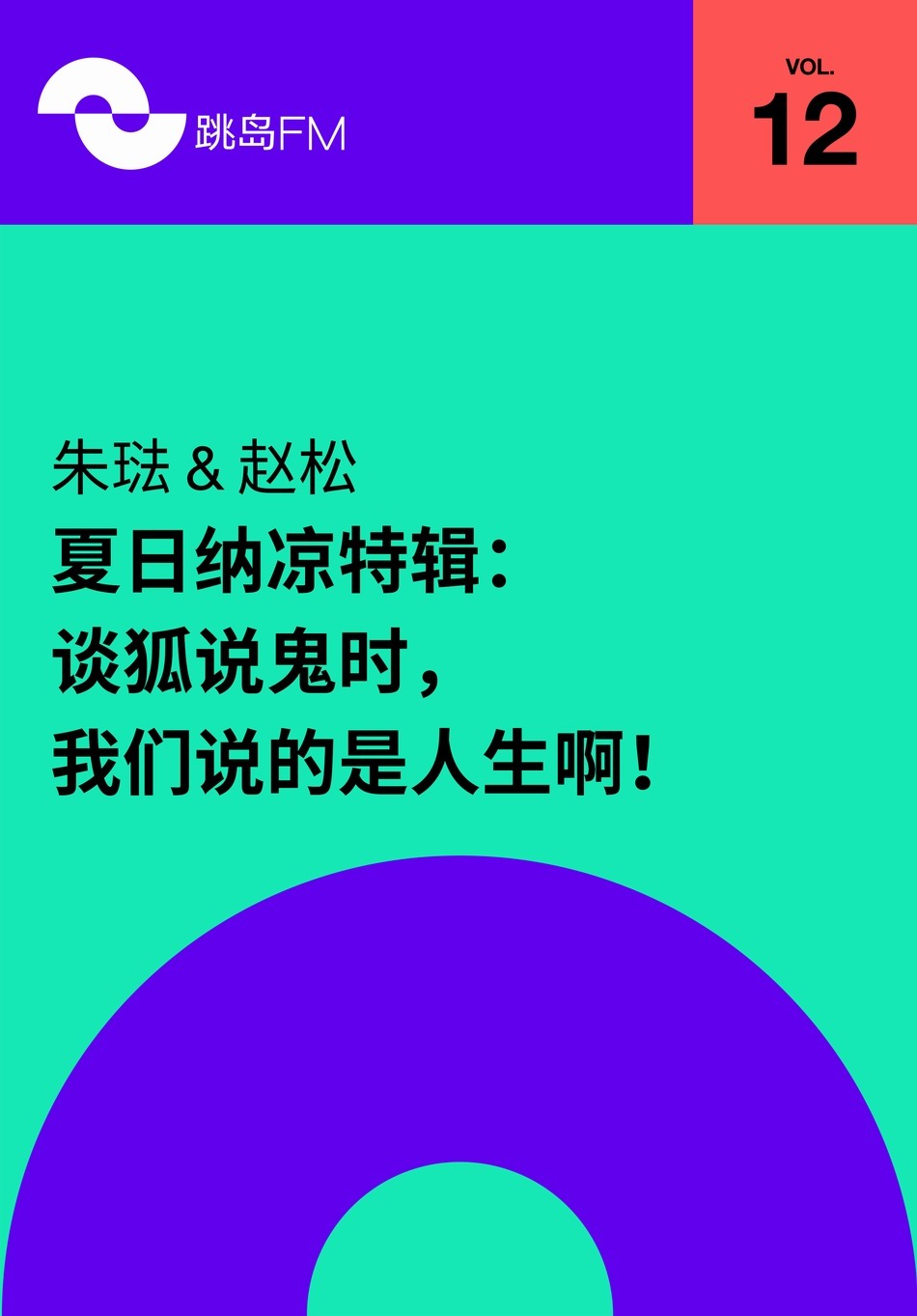
活动海报
6月17日,作家赵松和朱琺做客“跳岛FM”第十二期,与听众们聊起志怪小说。赵松曾编选《细听鬼唱诗 : 志异小品赏读》,而朱琺的新作《安南怪谭》在上个月刚刚出版。
在《安南怪谭》中,朱琺重新整理了越南汉文小说中的志怪故事,用更加合乎中国读者对汉语文学的感知习惯转译、翻写了那些荒诞怪异的情节。他说:“小说原文是用汉文写的,但这种汉文的语感跟我们的汉文有区别,本身就具有了一种怪诞的意味。”
中国的志怪传统
“在中国,志怪有很丰富的传统。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晚清,一直都没断过,它可以说是文言小说非常长的源流脉络。”
赵松对中国志怪的兴趣在于两点,一是处理题材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变化和延续性跟传统叙事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二是中国人隐匿于“神仙妖怪”背后的世界观与生死观。“中国是一个儒家社会,不像西方那样跟宗教有密切关系。 尽管中国有道教,也有佛教,但总体来讲还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那么妖魔鬼怪的东西是带有强烈补充性的,它可以让人在无关宗教的层面上去思考人和非人的世界,生死之外的世界,人死后的世界。这里有非常微妙的变化空间,涉及到中国人究竟怎么看待世界,看待生死。”
在朱琺看来,越南汉文小说中的志怪故事与中国志怪故事看上去有地理差异,但整体还是在同样的文化母体中。“都使用汉字书写,都受儒家文化影响。与儒家文化并行的,还有民间鬼神信仰、万物有灵的思想,它们对整个东亚地区都产生了影响。”
朱琺还提及,日本近代学者认为中国的神话逐渐枯萎了,捐弃了上古时候充满想象力的追求和怪诞的传统,越来越经验主义。“日本可能会看重中国更早的像《山海经》这样的东西,他们会给《山海经》重新配图,觉得妖怪在中国大陆被排斥了,而日本的妖怪学就很发达。实际上我们谈所谓妖怪学的概念是日本人在近代提出的。而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传统当中,它确实被逐渐边缘化。”
“因为它会动摇秩序,动摇一个价值观的核心。”赵松表示,事实上怪力乱神的东西在民间是有基础的,乡土恰恰是最能容纳鬼神故事的地方。“乡以上的部分是秩序化的。民间的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信仰,尤其在中国大一统之后,这些东西慢慢地消解掉了。”

赵松
人为什么要写志怪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生和死之间有一个决然的区分,但在鬼怪故事中不是这样。朱琺说,一个失去了生命的人物依然存在,被称为“鬼”,有的还变成了“精”。“鬼怪故事构成了非常复杂的生死关系,跟我们的日常经验是有区别的,它突破了生死的二元。”
他说起南方“飞头蛮”的传说——这一种群的脖子到了晚上可以自动分离开来,等早上太阳快升起时再回来。“如此这般对身体更自由的想象,不受我们日常经验的束缚。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永恒的向往,可能是这些鬼怪故事背后的一种比较坚实的意识基础。”
“对于生死,人理解的载体就是肉身。肉身会死,所以死亡比较可怕。但如果你可以摆脱肉身,那死亡本身就不那么可怕了。”在赵松看来,破除对生死的恐惧,也是志怪小说发散想象的重要源头。“另外,这种想象的前提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有限,确实会有一些非常特殊的体验是人类文明解释不了的。”
他谈及古人写志怪,还隐含着一种“人是万物灵长”的价值观在里面。“树曾经也是人,鲤鱼曾经也是人,人是进化的终点。但是进化成人之后,又超越了人的能力。我们能从这里看出来,还是有人的价值观在这里。”
“我们还会从历代志怪看到人对于秩序的悖论。人希望有秩序,因为秩序带来安全感。我们喜欢在一种安全感里谈论妖魔鬼怪,但一旦秩序性的安全感没了,人对于自身安全的需求就会大过对于不可知事物的需求,人的好奇心就会减弱。”基于此,赵松认为人对于妖魔鬼怪的兴趣起伏与其生活的稳定性有很大关系,“生活越稳定,谈妖说怪的需求就越高,因为他需要有变化。而在乱世的情况下,或者还有人借助这种故事表达善恶因果的关系,做出道德性的警示,这也是为了制造某种安全感。”

朱琺
谈论志怪的最大意义在于好奇心和想象力
在今天,读者能通过各种书籍了解志怪——比如栾保群的《扪虱谈鬼录》是偏文献整理的,锦翼的《纸上寻仙记》是通俗好看的,也有新创作的当代怪谈如赵志明的“中国怪谭”系列。
“栾保群老师所摘录的那些故事,灾难性的叙事,都有可能变成所谓的都市传说。志怪的母题不断被讲述,这个讲述本身其实就是文学了。文学把它记录下来,把它告诉别人,这个可能是我们面对这些怪异之事应该有的一种态度,也是文学的内在动力。 ”朱琺认为,文学背后的隐秘动力就在于我们去探索那些不可知的、超出日常经验的处理,处理在生命的延长线上的、介乎于生死之间的种种题材。
不同作家的文学处理各不相同。赵松举例蒲松龄和纪晓岚,一个写《聊斋志异》,一个写《阅微草堂笔记》,但两人的书写完全是不同的方式。“纪晓岚就是一个志怪小说的原教旨主义者,他觉得你不要加工。换句话说,他比蒲松龄更相信这个事情的真实度,而蒲松龄只是借题发挥。一般分析会认为蒲松龄应该比纪晓岚更相信这些神奇的东西,但恰恰并不是。蒲松龄作品的文学性更强,情节更曲折,人格更鲜活,他的了不起在于他的想象力。”
“毕竟,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如何超越这种有限性,最好的方式就是打破想象的界限,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条条框框。我觉得这是让有限的人生变得丰富起来的唯一办法。”从这意义上讲,赵松认为人们谈论志怪的最大意义在于保留对这个世界不可知一面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朱琺深以为然:“志怪是通向不可知的一个窗口。我们要打破日常生活中的心灵束缚,看志怪是一种方式,写志怪也是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