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天起,关心花草和树木 ——读《植物让人如此动情——枝言草语》和《植物让人如此动情——植物哲学》有感
平日里接触的多是专业论文,习惯了冰冷的文字,那些幼年甚至青年的淡然恬适的氛围都遥远得不能想象了。然而,手边的这两本书依旧唤起了这样的温馨。每篇文章都不长,散文的形式很是平易近人,像是有人在娓娓叙说,但她也不刻意,只是在说故事,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故事不是那种结局未知的悬疑案件或者带着血泪教训的历史叙事。有趣的是在《植物哲学》里,每篇短文的结尾总要按惯例出现两三句人生感悟。这些感悟有时候转折得不免突然,似乎只是作者自己的遐想,但从总体基调上看,这般由草木到人间的慨叹是积极昂扬的,像盖在文末的小红花,点出欢快的句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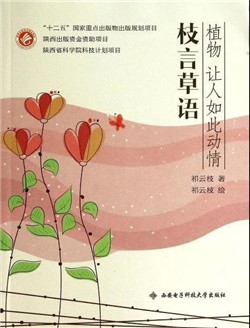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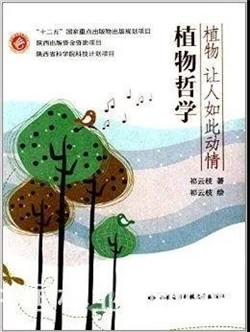
更让人赞叹的是科学知识原来还能打散成这样零碎的只言片语,镶嵌在古今中外的轶事和对植物拟人化的描写中。我眼中的科学是威严的,成体系的,由一整套公式理论组合而成,没有天地的灵气,没有五彩斑斓的四季,只有所谓永恒不变的真理。但若这么说,我便是时常遗忘两件事,一件是人类最初对自然的好奇,另一件则是当我自己也还是个小孩时,对自然抱有的那种一无所知的好奇。小孩子往往对数字有天然的敏感,当作者在书里惊呼“一个小小的南瓜,竟然能够承受五千磅(约2268公斤)的压力”时,可以想象小小的脑瓜一定会绞尽脑汁思考五千磅究竟有多重。如此这般思考,就无需人引领,悄然进入比较度量的领域。库萨的尼古拉在《有学识的无知》里引人注目地谈度量,隐隐然有科学先驱的影子。万万不敢说科学起源于度量,但比较与标准化却是智力活动的一种形式。从这一层面上看,这两本书不愧为优秀的科普读物。精心打磨的不仅仅是文字,还有彩色的插画,作者知晓图文的巧妙结合,不是生硬的植入,而是互动生趣,相得益彰。
然而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这样的书几乎“不忍卒读”。它似乎太“轻飘”了,无论是文字还是插画,带着一种与世无争的样貌,勾勒美好的一方小花园,与现在忙碌的工作学习格格不入。这让我不禁开始反思,如果说现代人忙碌到不忍心翻开一本轻盈的带画的书,那生活是不是也显得太过凄惨?主要纠结的是,翻开之后,让思绪随着轻快的文字起伏飘荡一会儿,又得重重地落回地面,更加悲凉。
博物学的认知在如今这个时代显得颇为老旧,仿佛昨日之事。现如今每逢春暖花开之际,在室外遇上一两株新奇或不知名的植物,欲要探根究底,只需掏出手机拍照识别,便能有所收获。而这种收获,在计算机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似乎很是微不足道。人们常常质疑,人工智能能够替代人的是哪些功能?抛去这些能用电脑机器完成的任务,我们人在世间还能剩些什么?我们习惯将自己看成一个个孤零零的个体,如同微信的经典封面,面对一个孤零零的地球。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广远的宇宙时,就不再把地球看成唯一的家园,更别提其间的花草树木。万物有灵的童年早已离成年的现代远去,在机械化的世界图景里,不单是自然草木,就连人的心灵都要被分隔出来,加以充分地研究。这种追求客观的实验性质的研究,总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
或许并不是少了什么,只是因为被遗忘太久而生疏了。当自然哲学开始用数学的语言书写之后,现代社会便开始将人解构。人可以在生物学的界门纲目科属种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在医学解剖的实验中认识自身的构造,可以借助物理化学等具体科学手段对自己开展各式各样的研究,但是我们仍然在怀疑困惑。人早已将自己放逐出自然界,万物变成了不可通约的研究对象。在科学研究的条条框框里,原始的情感与爱的关怀无处安放。书里作者对植物拟人化的渲染,唤起的正是那种陌生而温暖的感觉——对情感的认可和爱的接纳。20世纪以来,C.P.斯诺以“两种文化”的定义将科学与人文二分,爱这种包含人文因素的字眼在很多地方都要受到科学的嘲讽,甚或是人们的刻意忽视。而忽视爱的教育,无非是科学主义所能导致的最恶劣的后果之一。或许在新的世纪,科学与人文要实现的是新的弥合,在这种弥合中,对自然的爱的体验将填补现有认知的空白。
谈到遗忘,我们会忘记的不止是原始的天真,还有我们独特的文化。书里熟练地使用数字来说明事物的状态与概念,对我们古典的文化知识同样信手拈来。《黄帝内经》《晏子春秋》《本草纲目》等等,这些汉语体系里的文化知识奠定了我们认知的最初颜色。而在对自然的追问和探索中,它们能引发和数字科学一样的好奇与喜悦。对于小孩子而言,最为重要的或许不是真正记住的那些知识,而是探索过程的愉悦体验。在狂妄自封为万灵之长后,人终归还是要回到大地,在发明制造生产无数先进设备与工具后,人还是会面对自己,不停地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到那时候,我们永远也不会有关于这些问题的统一回答,而根植于大地的爱的哲学,或将长远流传。
本文为“2019科普文创——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创作评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