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测海:文学是无休无止的期待
来源:潇湘晨报 | 刘建勇 2020年03月16日08: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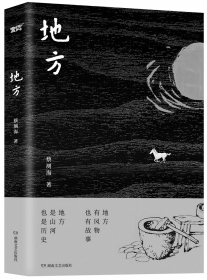
蔡测海最新的长篇小说《地方》。

蔡测海。
三川半,地名,是湘西作家蔡测海的理想故土。《地方》是作者第三部以三川半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是三川半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最厚重、扎实的一部。作者笔下,三川半的人、事、景、物、情等一一自由生长的同时,又共同完成了一部展现泛三峡地区独特地域里自然生命与人物命运交织的地方志。
这部史诗般的地方志,气息既古朴又鬼魅。三川半的历史与传说、现实与幻想、梦境和非梦,以及她的生死无界的时空,人神共享的世界,在《地方》中,融汇叠合,难分难解。
山的篱笆桩,围出了三川半一片天地
“你一定会守在那里。”这是蔡测海最新的长篇小说《地方》开篇的第一句。
他的上一部长篇小说《家园万岁》的开篇第一句,是“有一种游戏,叫作回来”。
这两部长篇和更前面的,《非常良民陈次包》,组成了蔡测海的“三川半”三部曲。
三川半是地名。
“有个地方叫三川半。三川半就是这个地方。”20多年前,蔡测海在三部曲的第一部《非常良民陈次包》中就介绍了三川半。
蔡测海介绍,三川半没有河流,只一条小溪,小溪是称不上川的,那川,多指别的事物——“人为一川,泥土为一川,牲畜为一川”,剩下的那半是什么,蔡测海说“不好说”。
在这个被蔡测海叫作三川半的地方,“山的篱笆桩一根一根地楔着,围出三川半一片天地”。这个地方离长江有些距离,但应该又不太远,因为,在三川半的高山上看到,“长江很细,三峡短促,三川半这片天地弥漫得很大”。
在三部曲的第二部,蔡测海介绍,为了水和粮食,还有草药,三川半的先人从远处走了很多路到的三川半。到了后,他们“在下雪最冷的时候也不离开,在干旱缺水断粮的时候也不离开”,他们“不是候鸟,是留鸟”“热爱这里的森林和流水”。
以上关于三川半的介绍,都出自蔡测海的小说。这个半真半假的地方,蔡测海后来在他的一组笔记小说《三川半万念灵》的创作谈中有了落地——“三川半,借指湘鄂川三省也,武陵山陵地,泛三峡地区。”
这个地方,也即蔡测海的故里。半个多世纪之前,在这个山的篱笆桩一根一根地楔着的地方,童年时候的蔡测海曾在山垭口眺望远处,他看到,远处是大山,再远处还是大山。
三川半,土地往高处伸展,接住月亮
“孩子们的秘密是关于食物的秘密。山里河里,是秘密食物的地方。野山菌、竹笋、山药,他们在树林和草丛里藏好,等孩子们去找。鱼藏在深潭,虾藏在菖蒲草中,螃蟹在石头下面,约好季节,把那些秘密打开。”这肯定是童年蔡测海就有的发现。这些发生在三川半的秘密,他在《地方》里毫无保留地抖露了出来。
在他的三川半,他看到青蛙逃到远处,爬上荷叶,望着洗菜的女人们,听她们的私房话;看到一种一千年也长不大的小鱼游过去,争吃散落的菜叶子;看到蝉在枫香树上鸣唱,它用声音把日子拉长,他注意到蝉不大,声音却不小,几只蝉的和声就能把一座山抬起来。
他看到有人摘石为桥,展地为路,取木为屋,搭火为伴;看到写满农事和季节的斗笠;看到山溪的鱼,躲进石头屋,把水作窗户,把寒冷关在水外,他觉得石头屋里的鱼很暖和,像山里人围住火塘;看到蛇为了长大,一年一度蜕皮;竹为长高,七天掉一个笋衣。
随着年岁增大,他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看到老鼠有两种快乐,偷粮的快乐和偷生的快乐;看到子弹和尸骨埋在深处,它们用蟋蟀和蚯蚓的语言讲悄悄话,孤独让它们靠近,用地下练成的鼠眼,打量对方生锈的年龄;看到明亮的刀子生锈,聪明的人在阴谋中长出坏牙齿;看到土地变得局促,往高处伸展,长高到土地菩萨管不到的地方,长成云朵里的高楼,高过山头,接住月亮。
即便如此,他的伤感或者说痛苦好像并不强烈,他的记忆里仍有焚音领雪,那雪先是一朵一朵地下,再是一团一团地下,路遮了,地盖了,树上挂满了雪,像一幢一幢的雪帐,老虎、野猪、豺狼,一经染白,便与百鸟争颜色。
蔡测海让三川半的所有美好和伤痛,在《地方》里全生长了一遍。
如果写作没有意义,不如去栽几棵树
十二岁或者十三岁,少年蔡测海第一次走出大山,出武陵山腹地,再翻越雪峰山,过湘中盆地,到长沙,到长江中下游平原,见识大都市的万家灯火。后来,这个小时候常眺望远处的山里人在有着万家灯火的都市安下家了,却又经常地离开城市,翻越一重又一重山,回到武陵山腹地的他的老家,回到三川半,回到有着草木生灵家族的部落,他喜欢那里和颜悦色的山水,喜欢那里的生死无界、善恶相生相济。
“蔡测海这个人实在难找。偶尔一露面,又忽然间消失,好像是一个外星人。”有朋友这么说他。他的“忽然间消失”,多半是回了他的三川半。即使没在三川半,在城里,他也难找。他不接电话,不用电脑,不在电视上露脸。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因为《远处的伐木声》等作品,他不断获奖。据说,他获完奖后,便沉默,像没获过奖一样。
“我是草莽。”大概10年前,蔡测海在香港大学讲座时说。他很有些草莽气质,他喜欢打麻将,不喜欢与人谈论文学。“做朋友讲义气,发财讲运气,打牌讲手气。”他讲。他的朋友很多,遍布商界政界民间。在朋友中间,虽然也有朋友称他为蔡文豪,但更多的,是称他为蔡哥。
因为面善心慈,幽默睿智,且时不时会因为某句话或某件事咧嘴哈哈一笑,呈一派天真烂漫,他的朋友大多喜欢他。他的一个朋友曾说,常有朋友看他好像沉迷麻将桌,替他叹息:如果他把打麻将的那些业余时间都用在小说创作上,成就将是何等了得。就在大家以为他在麻将桌上不可自拔时,他忽然就拿出了一部刚完稿的长篇小说。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十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三寸厚的一沓手稿,数百张叠加在一起的方格纸,最后一页的墨迹尚且新鲜,而最前边的几页,纸张已经泛黄,俨然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文物。”三川半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家园万岁》完稿后,最早看到该小说手稿的蔡测海的一个朋友撰文说。这个朋友认为《家园万岁》是一部具有时间厚度的小说,“时间不仅参与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而且成为这部小说的一部分”。
《家园万岁》出版了七年之后,同样具有时间厚度的《地方》在2019年下半年完稿,手稿同样是最后一页墨迹未干,而第一页已经泛黄。
“我写作三川半系列小说,时间跨度二十余年,也不过只写了六十多万字。在这二十多年里,我有时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字?长年累月地,而且一直笔写。如果这样的劳动没有意义,还不如去栽几棵树,去养一池鱼。”蔡测海说。
幸好,蔡测海并没有真的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栽树和养鱼上。
对话
“鲁迅有赵庄,沈从文有边城,我是三川半”
潇湘晨报:您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医生、记者、老师,您曾说过,这些都只是您的人生经历,和您成为作家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些跨界都比较大的经历中,您的选择应该是比较多的,是什么促使或者说推动了您选择了最终以写作安身立命?
蔡测海:过往的经历,都不是任意的。个人的生命不会无处不在。常识告诉我们,生活的选择,就是不可选择。文学于我,也不是选择,是生活中的发现。我发现使用语言的快乐。
潇湘晨报: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使用语言的快乐的?这种快乐和打牌什么的快乐相比,有什么不同?
蔡测海:从读唐诗开始吧,更早应是民歌和乡村妙言。和麻将相比,写作是精神愉悦,高级的快乐吧,与日常生活的快乐不同。
潇湘晨报:您怎样看待作家这种身份?特别是在生产和传播海量信息的当下。
蔡测海:作家不是身份,只是一种状态。他接收信息,也发生信息。我大部分时间与写作呈游离状态,长时间与写作中的小说失联。前一页稿纸已经发黄,然后再接着写。我让我的长篇小说呈一种断章式状态。让小说留下大的空白。这个空间,容得下想,也容得下悟。
潇湘晨报:我在一篇写您的文章中看到,您在某个各色名流汇聚的地方被视为“新保守主义者”和“爱国人士”。您怎样看待这两个标签?
蔡测海:爱国,是爱一种古往今来的文化。这个文化可靠,植入人性。所以,朋友说我新保守主义。
潇湘晨报:您的写作,大多数是以湘西为背景。在您早期作品《远处的伐木声》中,阳春随着木排去了远方,阳春后来有没有回古木山,您没有给出答案;在您的新作《地方》,最后一节,三川半的山川、树木、屋、牛、男人和女人的名字都被盗走又都追了回来。两个作品的不同结局,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反应了您对湘西的情感和认知上的一些变化?
蔡测海:我不在意湘西是一个地理名词、历史名词,或文化名词。它只是借代和隐喻。归去来,是精神上的因果关系。
潇湘晨报:您说的湘西只是借代和隐喻,它借代和隐喻的是?
蔡测海:如《地方》所指吧。某处。鲁迅不是有赵庄吗?湘西呢?各人的精神版图是不同的。沈从文是边城,我是三川半。
潇湘晨报:湘西的风情对你的文字风格的形成有没有影响?《地方》给我的感觉,既像是巫傩大神在某个仪式上的念词;又像是神到处撒种,每个文字读过去都发出芽、开出花来。
蔡测海:关于《地方》,是西南方言对我的恩赐,我把他作为一个语种。它激活了我的想象力,给我提供了一个表达方式。
我原本有中原人的血统,也有大西南的基因。孔孟的庄严,楚骚之风,巫傩之气,成就了我的文化人格。我的灵魂拘谨而又渴望自由。怀古思己,悠悠而郁忧,常有思想的病痛。
潇湘晨报:《地方》中,历史的伤和痛,您也用诗一样的文字呈现了出来。感觉您给这些伤和痛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
蔡测海:历史的伤痛,与个人生命的伤痛,往往是重叠的。博尔赫斯的伤痛和鲁迅的伤痛,我能感知。我的文字,来自我的痛感,万千尘埃中的我。
文学,不是绝望的路径,它是无休无止的期待。
潇湘晨报:“留住乡愁”“回不去的故乡”“乡村振兴”这是近些年经常会遇见的一些短语,关于故乡,您远远地打量她或是偶尔走近她,有没有想过她的将来会是怎样?
蔡测海:说乡愁,有点文人情态。我的故乡是喀斯特干旱缺水地区。历年的生态破坏正在恢复。现在是满目青山,干涸的山泉复活。我和老家人,将一块小地方变成湿地。费钱费力,值得。这将是我最后的努力。
潇湘晨报:继续说说前面说到过的盗名者。您觉得当下有可能成为盗名者的,将会是什么?是新的技术吗?
蔡测海:真正的盗名者,是时间和遗忘,还有怀疑。我们会忘记人名和地名,会忘记出生地和生活过的地方。然而,我们有在某地认真生活过吗?盗名者,应是哲学名词,尽管我不怎么哲学。
(蔡测海简介:1952年出生于湘西龙山,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著有小说集《母船》《今天的太阳》等,长篇小说《三世界》《套狼》及三川半三部曲《非常良民陈次包》《家园万岁》《地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