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旅行中写诗,走得再远都是为了走向内心
“有一次,我在圣马可大教堂前喝咖啡。在闲坐的三个半小时里,我面前走过了八个中国旅行团。导游也不让游客们进教堂的,他们大声一喊:‘各位请看,这就是著名的圣马可大教堂’!”在1月18日下午的思南读书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说起了自己在威尼斯旅行时的趣闻,不断引来读者有关“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会心一笑。
十年来,汪涌豪的足迹遍布欧洲,以他者的目光打量这片土地上的遗址、宫殿、墓地、古堡、故居,领略众多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文明遗存,并以诗歌的语言,编织出一幅曼妙的灵魂画卷。
今年1月,汪涌豪的第一部现代诗诗集《云谁之思》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的140首诗歌皆作于他的旅途中。尽管从事写作三十多年,尽管早以专长中国古典文学为学界所熟知,第一部诗集的出版依然带给他极其幸福的体验。
他笑言:“虽然我58岁了,但请允许我开始这段青涩的诗歌之旅。”

在1月18日下午的思南读书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说起了自己在威尼斯旅行时的趣闻。
以他者的目光,回归自己
在汪涌豪看来,旅行和旅游是不一样的。旅游一般是说从自己住腻的城市跑到别人住腻的城市,旅行走的则是心路,“我觉得一个人走向内心的路,要比走向外部世界的路遥远得多。”
他举了美国登月宇航员戈登的例子。“戈登第一次登月归来,记者问他在月球上最想看到的是什么,戈登说最想看的是地球,说走得再远都只是为了看到地球。我觉得这话很迷人,佐证了‘旅行都是为了返回自己的内心’。”汪涌豪说,走得再远,每一次旅行的归属点都是自己身在的始发之乡。
至于旅途,其中有许多迷人的风景,有自然风光,亦有人文风景。汪涌豪更喜欢后者,无论是帕特农神庙的历史荣耀、佛罗伦萨的艺术殿堂、如调色盘一般浓烈的巴黎大街,还是荒原古墓的灰色一角,都引起他无尽的内心震撼,以及强烈的写诗冲动。
“不作诗真不知如何消解。”
他有时就靠在博物馆外的柱子上写,有时写完已是零点之后,虽然疲惫却也十分开心。“我觉得真正的旅行是在时间和文化之中,时间和文化其实是一个东西。当一个人没有文化,时间只是时间。当一个人亲近文化,并且有一定的文化,时间绝不仅仅是时间。”
诗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家新感慨,汪涌豪最终把外在的风景变成了自己灵魂的风景,“有批评家这样评价过庞德的翻译,说庞德的翻译掌握了翻译艺术最高的奥秘,就是‘潜入他者’的能力。汪老师正有‘潜入他者’的能力,但他最终回归自己,赎回自己,成为一个更新的自己。所以我想这本诗集不同于一般的旅行诗,它有他者与自我的意义。”

葡萄牙阿部菲拉海岸
诗才是人心最大的真实
在常人眼中,诗让真实变得不真实,或者因为在生活中无法找到真实,所以人们才会寄情诗歌。
但在写诗和读诗的人看来,诗才是人心最大的真实,当生活无法让人如愿以偿,人们尚能在诗中安顿心灵。正如布罗茨基曾说:“诗是抗拒不完美现实的一种方式,亦为创造替代现实的一种尝试”。
汪涌豪提及,现在很流行说“诗与远方”,好像诗只存在于远方,眼前的生活都很苟且,“其实诗就在你身边,它提供了一种精神生活。只要你能够停下来,减去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欲望,诗就会来到你身边。”
“诗可以把你认识的世界变得更复杂一点。这句话,需要有知识的人去体会。但是诗也可以把很复杂的世界变得简单一点。这句话,需要有更高修为的人才能体会。”汪涌豪笑言,不管是想把生活变得更复杂一点还是想把生活变得更简单一点,诗都是很好的助力。
“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我力求笔下的诗不要破碎。如果情感是缠绵的,在章法上我就想用回环的章法。如果这个诗所表现的东西是垂直的,我的句式就从长句到短句往下掉。我非常注意有这样一种节奏。”
君主们的大起大落,艺术家们作品的永恒,某个想象瞬间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在写诗时,汪涌豪并不只是一味地回到历史现场,书写地球另一半人类的故事与思想,他也想把它们引到当下。比如灵感源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故事的《爱上阳台》,其中有这么一段:
时光穿越到今天,
我和你频频聚首又道别。
我时常分不清何谓坟冢与婚床,
正如守不住秘密的你
却什么也没法向我公开。
彼此取暖是鼠辈,
独来独往是雄狮。
谁愿将一刻的莫名感动,
换一生的无法沟通?
虽说没有过爱就不知道孤单,
但谁又担荷得起
花一生投入的爱情,一天
就被扔进了记忆的黑洞?
汪涌豪坦言,就诗歌内蕴的营造而言,他最在意的是写出自己直接感知到的心底的真实,并赋予这种真实以更广大的指向。而在形式上,他希望能打通古今与中西的界域,更充分地开显创作背后所隐蓄的中国文化的底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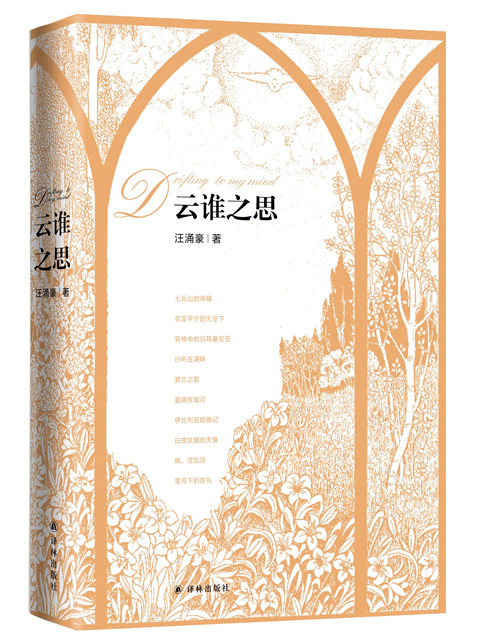
延续了被中断很久的浪漫主义传统
翻开《云谁之思》,诗中涉及的人物和典故多来自十九世纪。诗人、评论家张定浩说:“我们会发现,十九世纪的西方文艺深刻影响了我们,至少是汪老师前后几代人的精神生活。而一个受过十九世纪文明影响的人,回到欧洲后他的感受是什么?这本诗集也可以视为一种反哺。”
“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告诉我们,百年汉语新诗是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再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么一个跃进的过程,仿佛我们用数十年的时间就大跨步进入后现代了,与西方同步了。但其实我们每个阶段都没有完成,浪漫主义没有完成,现代主义也没有完成。西方人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慢慢形成了各种各样彼此激荡的浪漫主义传统,我们大概只有一二十年的时间。随着徐志摩的去世,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整个浪漫主义传统在中国一下子就断掉了,并成为一种很奇怪的被年轻一代写诗者轻视的对象。”
在张定浩看来,汪涌豪的这批诗难能可贵地延续了我们被中断很久的浪漫主义传统。首先在音调上,它们明朗,悠扬,有一种让听众与读者舒服的语感,又有吟游诗人那种历经世故的体谅。“这种语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浪漫主义的一大要素在于诗是用来与别人交流的,是需要用耳朵倾听的。”
他提及,中国过去也有咏怀的传统,也是在游历中用诗歌述事怀古并与朋友交流,汪涌豪在吸纳延续西方浪漫主义传统的同时,似乎也吸纳了这个古典传统,这两个传统都强调与他人、与天地万物、与过去的交流。
“而与此相对立的,是当代诗人慢慢变成了一个个所谓的创造者,他们只是用力在创造发明一个个自己的诗学世界,并不太考虑交流,这就带来与公众的割裂感。所以我们读当代诗往往会觉得读不下去,很多诗坛中人写的诗,可能都只能观看,无法读和听,因为他诗歌中没有一个乐意和你交流的声音。”
张定浩说,浪漫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但简单来讲它是对意志、行动乃至于对人的一种尊重。“它的每一首诗背后都有一个人。但是浪漫主义的自我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自恋或者是狭小的个人,往往真正浪漫主义的自我是把自己投射到宇宙这个无限中去,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成为宇宙无限的一部分。从汪涌豪的诗中,我们看得到这种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