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叶嘉莹先生

“弱德之美”是叶嘉莹先生对词体的美感特质提出的一种本质性说法,其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凡被传统词评家所称述为“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之品质原来都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弱德之美:谈词的美感特质》是以词人、词史为线索,从文学体式、性别文化、历史世变等多方面探讨词体的美感特质,是作者关于“弱德之美”之专论、讲演、访谈的首次结集。
本文从“弱德之美”这一审美出发,体现了叶嘉莹先生平生之天性与不渝之持守,读者也可以亲切地感受到学术与人生相融合而闪现出来的幽美与光华。
我想,认识作为一个教师的叶嘉莹先生,或者作为一个诗人的迦陵先生,都不妨以一个转语开始:她本质上是一个在桃花源前那道清溪上的摆渡人。春雨桃花,她在;雪满清溪,她也在。唐朝张旭有《桃花溪》诗: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洞在何方?桃花源有吗?在的,叶嘉莹如是说。但其实,从绿鬓芳华到今日银发满头,七十年风雨清溪,依然在摇她的船桨这件事本身,即是桃花源;个中人由垂髫而黄发,怡然自乐,昭示了当代一段美的历程。
壹
叶先生的人生,或者,由我半带猜测地说吧,她在“日常生活”中尽了作为一个女儿(长女)、妻子、母亲所有能尽和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担负多于享受,苦多甜少。但是,诗人的气质、师长的教诲和期待、离乱所催生的志意、西方的学术文化熏陶,更重要的是中国开放时代的到来,让她凭之、也得以在这个千古机遇中做出了一场淋漓鲜活的美的演出,铸造成功了一个为历代诗人墨客所罕见的“叶嘉莹现象”——着实地说,叶嘉莹独特之生命美学由此而生。这种美学不徒然是一种构想,而是由她重新品味、亲践生活所成就,也由其以精彩文字所呈现(创作诗词或论说诗词),非寻常老儒的青灯黄卷可比。在一个一切皆时尚,出生便夭亡的“液态时代”(齐格蒙·鲍曼语),有叶嘉莹这样一个人,活出一个罕有的、既与历史文化血肉相连,又对将来殷殷期盼的典雅的生命方式,称之为“精神贵族”或不为叶先生所首肯,但有那意味则显然不为过。这种存在方式,不必说是稀少的,但一切现在或未来的“有所思”的人不能不认真反思这个“叶嘉莹现象”存在和形成的根由。

齐格蒙·鲍曼
贰
人的生活本身变幻难测;人与镜中影对望的每一刹那都一去不复返。所有这一切,与如水入器、不可定型的艺术正同。接触先生十数年,我觉得她之不与坐而论道者同的特色是:她素志不移,但同时又不断“整顿”自己的人生,遂若彩虹随现;她既以文字、语言尽染层林,而复以血肉生命亲践之,由此汇成的感发之力便最能启导人们进入诗之世界。人所共知叶先生是教师,但人少知她尤其严苛于教育自己:她对词之特质由不可言的要眇幽微之思的撷取到最后提出“弱德之美”新说,那与其说是叶嘉莹词学的演进,毋宁说是叶嘉莹以绵延的反思之力重新释读古人、释读自己,最终把缚在人们身上百数千年的“忍辱负重”之类名缰解脱,让古人、今人蒙尘枯竭的心泉汩汩涌流。人生苦难,千古无同。每个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本质上无从比较。即以女词人而论,李清照、徐灿、贺双卿以及近代的丁宁,也都同样经历了某种或国仇、或家恨的深重苦难。略为不同的是,叶先生曾经接受过西方文明的直接洗礼并亲践其中。在细味种种苦难之后,她显然以巨大的勇气采取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儒家传统的“威武不能屈”当然是根本的精神资源,苏东坡于天风海涛中所蕴含的咽断之音更为她津津乐道,但人所少知道的是她非常喜欢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的《绝食的艺术家》一篇,内中蕴含有一种不与世俗同尘的自我持守。如果弱者总用强势者制定的各种“规范”来为自己辩护,最终必归于无效。叶先生因之在晚年提炼出一种她自己的生存美学:“弱德之美”——你有你的外在强力,但我总守住我心灵的自由和对美与善的持守,相信“云端定有晴晖在,望断遥空一抹蓝”。这种久被压抑的新鲜生命能量一旦被挖掘出来,其喷薄之力便冲刷洗清了今人的耳目——我们因是而看懂了新的苏东坡、辛弃疾,也看懂了叶嘉莹由域外踽踽独行之旅延伸纵放于中华大地的美的播种历程。这种不断整顿自己思想的“活法”必然是开放的,必然是一个有历史性的、文化的维度的开拓和现实的践行的鲜活历程。人亦由是而将个体有限的生存扩大至最大的可能领域。“弱德之美”说是叶嘉莹人生经验和学养的归结和再出发,亦是其多彩生存美学的光谱的原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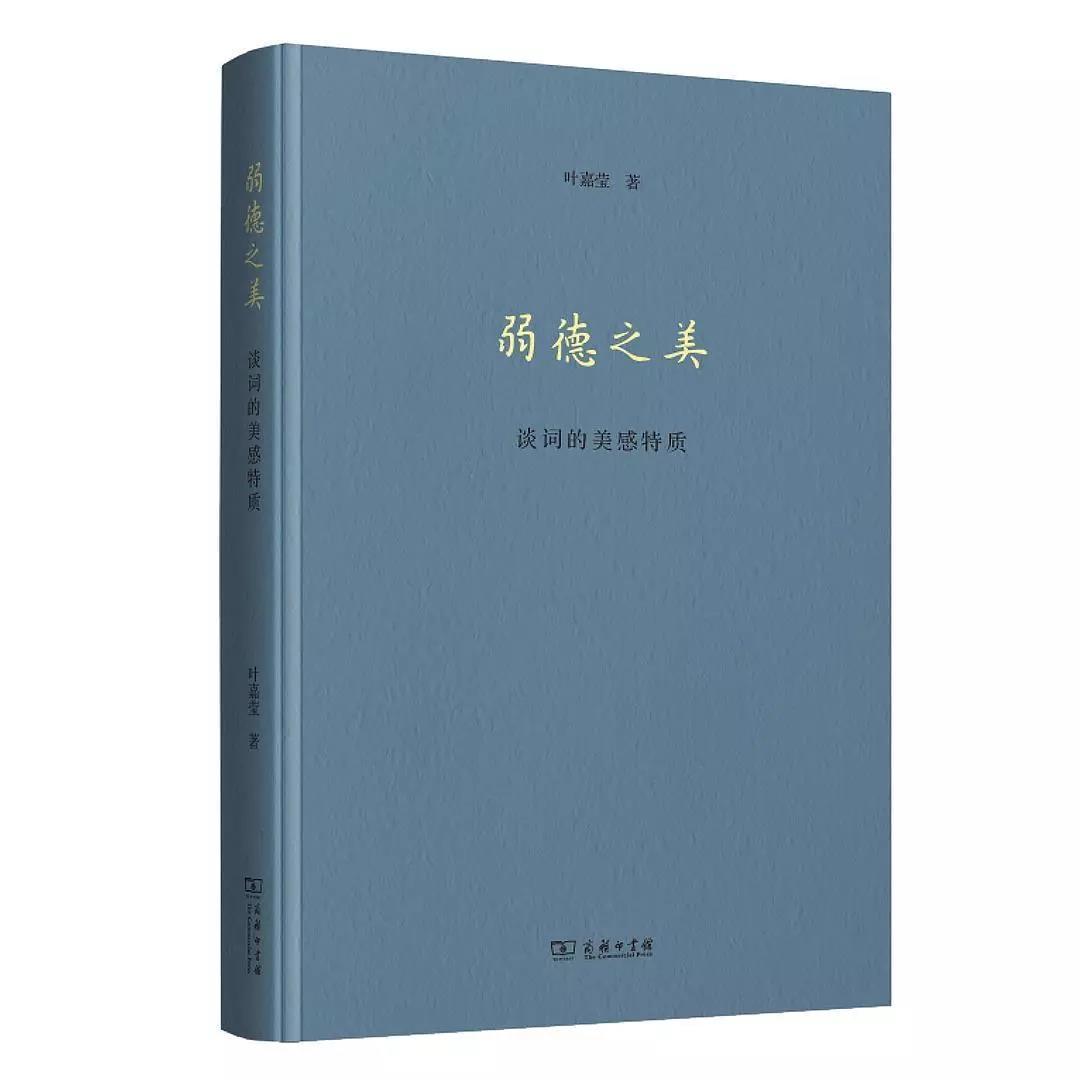
《弱德之美》
(加拿大)叶嘉莹 著
商务印书馆
2019年6月
叁
词人,一般常有自己最喜好、擅长的词牌。稼轩词六百多首,长调“贺新郎”有二十三首;小令“鹧鸪天”有六十三首之多。无独有偶,叶先生的小令亦多“鹧鸪天”。里尔克说,诗人的根本任务就是“新鲜地指称世界”,叶嘉莹果然在“鹧鸪天”中把她发现的“弱德之美”的境界用老油灯和蓝鲸这两个意象“说”出来了。老油灯,和历史、文化、自身遭遇环环相扣而出;蓝鲸,这个她晚年诗词中屡现的沉郁但壮丽的意象,亘古所无。或许是碰巧,我和叶先生这两首词的创作有过交会。
2000年,她来澳门参加词学研究会议,我因施议对教授之介认识了叶先生。叶先生选诗、读诗、教诗极严谨,这是她门下弟子都知道的,但我只是一个门外的读者,却反而亲炙得先生平和亲切的一面:她从不以我之不懂学问为嫌,我在十数年间不停地向叶先生通信请教,今达几百封之多,无所不谈不问。偶尔,亦将自己看到觉得有点儿意思的书寄呈先生一看。《老油灯》和《鲸背月色》即是其中的两种。本意以为如鲁迅先生所谓“聊借画图怡倦眼”而已,但不想这一如我等平常人视为当然的偶然就引发出叶先生创作了两首可称绝唱的“鹧鸪天”好词。现在录写在下面:
其.一
友人寄赠《老油灯》图影集一册,其中一盏与儿时旧家所点燃者极为相似。因忆昔年诵读李商隐《灯》诗,有“皎洁终无倦,煎熬亦自求”及“花时随酒远,雨后背窗休”之句,感赋此词。
皎洁煎熬枉自痴,当年爱诵义山诗。酒边花外曾无分,雨冷窗寒有梦知。人老去,愿都迟,蓦看图影起相思。心头一焰凭谁识,的历长明永夜时。
其.二
偶阅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n )女士所写《鲸背月色》(The Moon by Whale Light )一书,谓远古之世,海洋未被污染以前,蓝鲸可以隔洋传语,因思诗中感发力可以穿越时空之作用,盖亦有类乎是,昔杜甫曾有“摇落深知宋玉悲”之言,清人亦有以“沧海遗音”题写词集者,因赋此阕。
广乐钧天世莫知。伶伦吹竹自成痴。郢中白雪无人和,域外蓝鲸有梦思。明月下,夜潮迟。微波迢递送微辞。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

叶嘉莹3岁时与小舅李棪(左)及大弟叶嘉谋(右)合影
这里专说第二首。蓝鲸这一新颖意象,既有传统的影子,但又可以生发出全新的意味。宋·苏轼《和陶郭主簿》有句云:“愿因骑鲸李,追此御风列。”宋·陆游《八十四吟》之二亦有“饮敌骑鲸客,行追缩地仙”之句,都有雄伟的意味,但似乎只是外在的叙写。而叶先生使用蓝鲸这一意象,则一是和通俗文化中对巨大蓝鲸的神秘的美结合,又巧妙地注入了传统诗歌中的“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的意涵。在蓝鲸这一意象中,巨大与纤微,遥远而心即,低沉而绵延,单一而丰富……种种张力被牵引入诗,而又不时使人重回到《诗·泉水》“毖彼泉水,亦流于淇”的感发原点,生动地展现了作者时刻在历史和现在、在场和不在场的活跃状态。时间于此不再是一个箭头的方向,而是多维的发散状态,多层次的精神结构。蓝鲸独语这个古朴、壮美的形象被她人化了,它不仅寄寓了叶嘉莹这个独特的存在——她固然“在场”,深沉地独语、苦语,但她实际上又在邀请、等待无数不“在场”、缺席的古今知音(大洋另一端的蓝鲸)成就一场“千秋共此时”的壮丽演出。这一意象她此后屡屡用之,直至最近,当荷月初吉前夕,我写了两首诗给她,叶先生覆言:
贱辰远劳牵念,岁岁惠赐佳章,衷心感激无已。大作是两首好诗,写出了对人生深刻的体悟。我未敢奉和,只是用你的诗韵口占了一首只有四句的小诗。如下:
来日难知更几多,剩将余力付吟哦。遥天定有蓝鲸在,好送清音入远波。
“遥天定有蓝鲸在”,超越时空的交会,是迦陵先生以为人世间千灾万劫,万水千山,但诗心总有相通的一日;与素心人(古若陶潜、辛老子,今则是待启蒙的未知诗者)相期,若阮步兵之得人岭上回啸,则是她读诗、写诗八十多年的衷心之思和期盼。意象的新鲜本身即是诗人不断在和现实碰击交汇的表现。诗,不是为了只和学者交谈,而是要和所有的人交谈。是的,即如她的所谓“弱德之美”,提倡即使在外力的强压下跌倒了,也要保持着自己灵魂的高洁。“弱德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那不是弱德。弱德是一种坚持,是一种持守,是在重大的不幸遭遇之下,负担承受并且要完成自己的一种力量。”她以为这种美才是人之为人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人的生存美学。弱,确为现今这个一切视“强”为唯一真理的时代所看不起的,我相信,叶先生也知道这一答案是有限的或不完善的。但是,人不就永远在有限性中活着吗?叶先生为自己的标准和判断承担责任,她勇敢地去爱,去思考,去创造,把自己创造性的良心和层累而成的历史智能有机地联系起来、整合起来,成就为一种成熟的生存美学。弱德之美是她由被动的“能在”转化为“此在”的主动选择、有作为的自由方式,即诗性地栖居的具体展现,是一种不甘浊流的“超越”。它恰如思想家阿多诺的一个比喻:有这样一个讯息适合被记录下来,并且值得花工夫把它放在瓶子里扔进海里漂浮;是的,未来什么时候、什么人会读到这个讯息都不确定,但这个讯息的潜能因着这首诗的存在而度过它现在被忽视的时段。她相信这种弱德之美的价值有不灭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她以为唯有这种脚踏实地、依靠自身、不诉诸其他任何事物的行动才可以使自身的精神保持主动的状态,从而积极地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利和自主权;某种价值暂时不能实现这件事本身终究是脆弱的,而且一定会过去,她坚信这一点(“心头一焰”)。大家不都是称颂叶先生浑身渗透着文雅吗?但请注意,她的文雅有无尽的勇气和力量支撑。一个人不以外力自华,能不文雅吗?从这个角度看,叶先生的美学是在这个文化成为用于消费的产品仓库的一个例外,她坚守严格的品味区隔标准、让人变得高贵的原则,和美化一切不稳定性与不一致性的“流动性现代”对立,和“买到手即过时”的消费主义对立。她坚持精神的守望,而不是“回去购物”(“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即时说的一句话,以为购物是治疗一切苦恼的方式)。

年轻时的叶嘉莹
肆
叶先生本质是诗人,不是学究。她的创作也好,论文也好,归结到最后,就是重回诗的原点、目击道存的“感发”。上引《诗·泉水》:“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泉水可越万山至目的地,但我此去却不能复返故里,这种摇动人心的“感”就是诗的原点,赋比兴都是余事,恰如孔夫子说的“绘事后素”。没有感发之力的诗是虚伪的,不足以言诗,我想这是叶先生的心里话。
叶先生长期生活在书斋中,但她平静的书桌是走过千山万水和艰辛苦难后才到达的。坐进书斋,但她还是用心来继续她万水千山的旅程。生活本身,例如在台湾早年睡在人家家中的过道上,那是艰难的实在,但不是诗。诗是整顿过的生活。她所以如此重视吟诵,是因为诗的音韵是某种形式的构想成形,失去它即失去诗,至关紧要。她讲诗,写诗,都是在以某种她以为理应如此的“形式”重新整顿她曾经过的生活。叶先生现在都要坐轮椅外出了,但她讲诗则坚持一定要站着讲,也不管讲多久,她也很注重自己的演讲仪容,原则上决不使恶俗加之于身,即使讲最脍炙人口的诗也都隔晚备课。为什么?这是对自己生存风格的爱护和锤炼。风格,是具有排他性的,不是不许你学,而是你学不来,因为这是她以整个的生命历程铸造而成的。“客子斗身强”,她常引用这句杜诗以自勉。她一生都在旅途中,也一直以默默的斗心走自己的路;“身强”是以内在的韧劲逼出来的。可以说,她的遭遇“点亮了”她的存在。她常说将“遗憾”还诸天地,事实上是以一颗被重新擦亮的明珠还诸天地,彼此照亮。由此可知,叶先生对诗词的观照并不纯然是一种对美的客观的、主客二分的观照,而是以审美自身的生存为第一元素展开的不断更新的、无限的、超越的美的旅程。她不是学究,她是一个美的追寻者;因此她不能容忍虚伪的、外观表象的“崇美”。有一次,我陪她出席一个学校为行将毕业的以“主持人”为专业的学生举办的吟诵表演的活动,她在现场评论,就尖锐地批评个别同学:“你表演的超过了你内心感受到的,因此是虚伪的!”她不接受把诗词吟诵异化为潮流演技表演的朗诵。这件事本身实际上揭示了她对诗歌的评说能力不徒然是指涉某一具体作品的能力,而是实实在在地展现了在二十一世纪这个人类对于前途、人与非人(机器人)、人与动物等问题之尖锐涌现时的响亮回答。审美或品味能力本身是人异于一切的特点,是人对各种人性能力的综合性的复杂的判断活动,人的本体或最终的归宿在此。人的生存本体论在此。

1948年叶嘉莹结婚照
或者,我们都是花,而叶先生是辛勤工作的蜜蜂,把百花酿成不同的蜜,即是以诗性的语言(评说和创作都是)重新“说出”各个花儿们心向往之而未能、未及说出的理想的世界。叶先生的工作是“制造可见的来为不可见的服务”,向我们“敞开”了一个原来见不到的世界。她夙夜不懈的辛勤,至今如是。这后边的动力,或者可借佛教的“死随念”喻之。她夙有佛心,《瑶华》一作下片云:“因思叶叶生时,有多少田田,绰约临水。犹存翠盖,剩贮得,月夜一盘清泪。西风几度,已换了微尘人世。忽闻道,九品莲开,顿觉痴魂惊起。”她平时少讲佛,而身践之。常常想到自己真的是与死同在,随时都会死、都有可能死,与死为邻,与死亡只有一线之隔,我们由是重新检讨、审视、挖掘自己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这就是经常在生存和死亡之间穿梭,“犹存翠盖”和“九品莲开”都是照面间事,死亡因而绝不是单向道,而是可以纵横穿越的。“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我们得以以此和他人、神、世界、历史对话,此即审美之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