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上龙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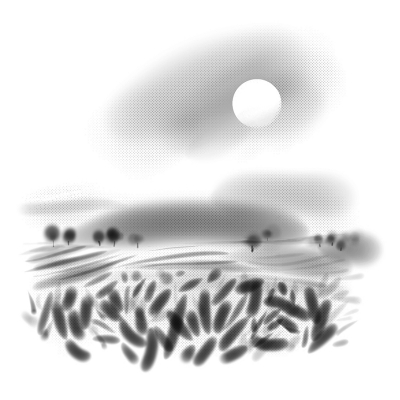
郭红松绘
一
圆月从后山升起,中间是耀眼的白光,周围是粉色的云,向晚的夜空仿佛一张微醺的脸。我们就着月色喝最后一口杨梅酒的时候,听见月色里亮起一声“老黄——”
这是初春的龙坞,西湖之西,钱塘江之北,一个离杭州只有十五公里的世外桃源,千亩茶园连绵起伏,散落着一户户茶农人家。离清明节还有五天,对于以西湖龙井茶为生的村民们来说,这是金子般的五天。
茶农黄建春的炒茶坊里,蒸腾着这个春天最浓郁的香气。自从祖先与一片叶子在森林相遇,茶就在波澜起伏的人类进程里扮演着各种风雅角色,而对于黄建春一家,茶就是茶,是土地的馈赠,安身立命的根本。
踏月而来的,是一位茶人——与黄建春家一墙之隔的求是茶园园主王如苗,跟在他身后的,是即将来杭攻读茶文化博士的美国小伙戴伦。
十年来,农历二月二过后的每个清晨,王如苗都会一个人沿着求是茶园旁蜿蜒的小路走一段,先经过比邻的黄建春的茶垄,慢慢下坡,走向开阔处,展眼便是黛色的远山和一垄垄碧绿的茶园,低低萦绕着白色的云雾,一声声鸟鸣从沉静了一夜的空气中穿行而过,叫声比露珠更为清冽,而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芽尖,也像一张张雀嘴在鸣叫。他常常想,一定不止他一个人知道,一杯茶里,藏着多么美好的清晨。
古时,将采茶时节上门来寻茶、留宿或相帮的朋友,叫作“茶亲”,此时,王如苗是,我是,戴伦也是。一见如故的三个人像古人一样,坐在黄建春炒茶坊前的空地上喝茶。普通的玻璃杯,几张顺手拉过来的骨牌凳和矮竹椅。用最舒服的姿势坐下,感觉一左一右都是我多年的兄弟。围着我们的,还有十几个竹篮竹篓竹筛竹簸箕,还有老茶树们,以及一只脚受了伤的猫。
皓月当空,人在草木间,空气里有三种茶香——一种是炒茶的干香,一种是明前茶茶汤的润香,还有一种是茶树呼出的气息,香气在月光里暗暗浮动。我恍若觉得,此时月下喝茶的,不止三人,而是对影成六人、九人、无数人……是第一次与茶相遇的猎人或者神农,是留下划时代茶学专著《茶经》的茶圣陆羽,是首创“佛茶一家”的茶祖吴理真,是写下“茶人”二字的唐代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是手书“茶禅一味”的宋代圆悟克勤禅师,是吟出“从来佳茗似佳人”等千古绝句的苏轼,还有宋徽宗赵佶,还有将狮峰山下十八棵茶树封为“御茶”的乾隆……一片树叶,在与人类的第一次结盟后,用它小小的身躯占领了地球上300万公顷的土地,一杯弱水,由实物蜕变为灵物,在历史时空里腾云驾雾,既左右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又让无数素昧平生的平凡人像家人一样坐在同一轮圆月下寻得清净自在,就像此刻的我、王如苗、戴伦,还有仍在炒茶的黄建春。
王如苗说,半个月前,下午三点,早春头一批西湖龙井刚炒好出锅,门外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新茶好喝了吗?”进来的是一位山东大汉——他在济南开茶庄的茶友。茶友从王如苗的朋友圈得知新茶今日开采,于是独自一人开了八小时的车来到求是茶园,只为品鉴早春第一泡西湖龙井。两人在茶桌前一一坐定。那个下午的第一口西湖龙井,王如苗尝出了与往年不同的滋味,和胃一起慢慢热起来的,还有眼眶,还有心。
二
月上柳梢时,她们已经睡下了。
惊蛰过后,春分之前,油菜花铺满江南大地时,采茶女们浩浩荡荡地从江西或安徽等地出发,坐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抵达杭州,抵达一个个正在萌芽吐翠的茶园。
她们大多五六十岁,做了祖母或外祖母,大多不愁温饱,但一年一度二十天的采茶工收入可以补贴家用、零花,或攒足一根金项链、一对金耳环。
一斤茶需要一双手采摘56000次,按照采摘嫩度的不同,分为莲心、旗枪、雀舌,构成龙井茶的品质基础。采茶工是否用心,直接关系东家一家人一整年的生计。短短的二十天是一场“战斗”,凭的仅仅是口头约定,还有良心。
午后寂静的时光里,滑过一声声鸟鸣,一朵朵云在天空默默无语。采茶女们双手戴着半截棉纱手套,每一个指甲都被茶汁浸染成黑色,拇指和中指食指指肚的皮很厚,指纹已经被一道道纵横交错的裂纹代替。这些手指上仿佛长着眼睛,左手落在一片叶芽上时,余光已经瞟到右手要落到的那片叶芽,右手落下时,左手又有了着落。用的是食指和大拇指指尖的巧劲,抬升拔起,只轻捻,不紧捏,不用指甲掐,太嫩了不行,太老了也不行。
每年清明前后,戴着斗笠、穿得花花绿绿的采茶女们静静散落在云雾绕缭的龙坞茶园,成为江南初春最美的景色,被摄入人们的镜头。镜头年年记录着这种美,却无法记录斗笠下通红的脸、湿透的头发,还有酸痛的腿脚。
此时,月光照见她们已经熄灯的窗口,让我想起一张照片——是她们中的一位发在朋友圈里的合影,背景是一垄一垄绵延不尽的茶树和寂静的群山,她们大多笑得很腼腆,其中一位叫王中玉的笑得最开心,皱着鼻子,露着豁牙。
照片下写着:“七仙女下凡。”
三
月亮升到顶空时,落到龙坞茶农黄建春身上的月光仿佛多了些重量,使得他的手势和脚步都渐渐沉重,像独自一人拖着一整个夜的黑。
“沙——沙沙”,筛子旋转,茶叶飞起来,在月光下悬停一秒,或十分之一秒,落下,瀑布般闪亮,沙沙沙地落回筛子,分量轻一些的碎叶,便经他手腕的巧劲,飞离了筛子,落到了地上。
村里人都睡了,采茶工都睡了,他的家人也都睡了,他还在炒茶。除了吃饭,抽几口烟,他没有过片刻的休息。他的手,是天生炒茶的手:五指合并,严丝合缝,从指根到指尖,有微微弯曲的弧度,与炒茶锅紧紧贴合,手工炒茶的“抖、带、挤、甩、挺、拓、扣、抓、压、磨”十大手法一一精通。黄建春是村里炒茶炒得最好的人,他炒出来的茶叶,色绿、香郁、味甘、形美,尤其是色泽乌润,手感如同摸在丝绸上,无比光滑,拿到茶叶市场卖,一般比别人价格高一两百元。
第一锅新茶出来,叶底细嫩,如同花朵一般,他从来舍不得自己喝,喝的都是清明后采的老茶,卖相差的那种。不是喝不起,不是死要赚钱,是太辛苦了,只有他自己知道,在每一片茶叶上,他从未吝惜过自己的体力。
巨大的老香樟树像一双大手覆盖着炒茶坊,让他常想起父亲的大手。睡在山上的父亲说,这是老天的恩赐,传了1200多年,不能白白扔了。是啊,祖上传下来的茶园怎么能放弃呢?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怎么能放弃呢?他不太懂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好好做茶,心无杂念,随遇而安,是最心安理得的谋生方式。
月光下,一丛丛老茶树站成了一块块沉默的石头。老茶树是祖上传下来的,年岁久了,乏力了,产量太低,味道较之新品种更为苦涩、浓烈,有人特别喜欢,但卖不出价格,几乎被茶农们放弃了,便任其自由生长,也不修剪,越长越高,越长越瘦,无人问津,野猫随意出入。
月光下,茶农黄建春微微弯着腰,用畚箕畚着茶,那么瘦,像一棵老茶树。
四
我睡在月光下的龙坞,做了一个关于茶的梦。我梦见我在梦境里外飘浮,如同立体的圆月亮在海平面上下浮沉。我在梦里捕捉着“它”——有时,它是一枚嫩叶;有时,它是一粒葵花籽大小的绿光;有时,它是玻璃杯里千万个跳舞的精灵;它是解毒的良药,亦是喂给敌人的毒;它是刀剑,亦是丝绸之路上的生命之饮;它是禅院里的一缕青烟,亦是殿堂上的最高礼仪;它是僧侣行囊中无上的佛法,亦是凡间最美的烟火;它是诗人的酒,是酒的友,是他乡明月,是游子的根,路的尽头……
它在几近沸腾的温度里一次次涅槃,让万千生命在永恒的不完美中感受短暂的完美;比心脏更柔软的舌尖,为漫长的生命苦旅完成了一次次短暂的释放,哪怕只有一盏茶的时光。
而那些制茶的人们,手掌上带着泥土的温度,在我的梦里转身,面目清晰,他们从未想过要释放自己的艰辛和坚忍,累到极点时,也只是轻轻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梦被一声鸟鸣啄破,隔壁房间采茶工们洗漱和聊天的声音鱼贯而入。打开房门,黎明前最后的月光四处逃散,月亮放弃挣扎,向着山坳渐渐沉沦。
路灯尚未熄灭,采茶女们又出发去山上采茶了。不知谁说了个笑话,她们嘻嘻哈哈的笑声瞬间占领了被晨雾和露珠管制着的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