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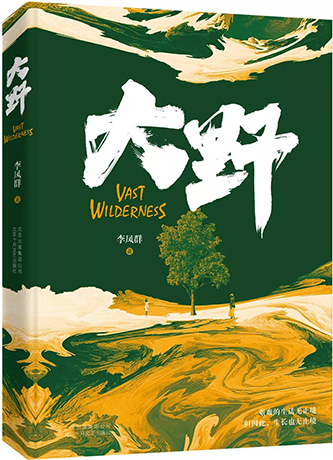
《大野》
作者:李凤群 著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编辑推荐
◇七〇实力作家李凤群最新力作 斩获2018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
◇两颗为爱焦灼的赤诚之心 一场包容否定和挣脱的殊途同归
于卑微处起身,她们必将走向生活所馈赠的开阔
◇艰难的生活无止境,但因此,生长也无止境。
◇繁华世界就此别过/我曾爱之弥深/即使我无所获/我仍感不虚此行 ——赫尔曼•黑塞
内容简介
《大野》是70后实力作家李凤群的长篇新作。小说由“世界之间”和“遇见”两部分组成,前者双线书写,穿插并行,推动情节;后者补插倒叙,完整曾被隐去的节点,是两位主人公人生中宿命般的高光时刻。
作者将笔触集中于两个城镇出身、出生于“改革开放”起始时代的年轻女性——今宝和在桃,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她们辗转并行的人生际遇。性格两极,却同样敏感,对生活充满体察,她们循着不同轨迹,以迥然的方式对抗既定生活,缺少爱但又渴望爱、追求爱以及更高的自我实现。“自己是谁,将过怎样的一生”,从一种生活到另一种生活,事关逃离和回归的“成长”,或许将伴随她们以及一代女性的终生。
如果说《大风》更多关注的是大的时代以及置身于其中的小人物的命运,那么在《大野》中作者的思想深度更多体现在对人物更高层次精神追求的剖析。物质生活逐渐充盈,但精神的提升并非一定能与物质的改善相同步。作者对社会现象和世情有着丝丝入扣的体察,饱含理解和同情心来书写,下笔精炼而不失细腻,读来令人共情。
作者简介
李凤群,女,安徽无为人。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大风》《大江边》《颤抖》《活着的理由》《背道而驰》等多部。曾获第三、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安徽省首届鲁彦周文学奖长篇小说奖,2003年度青年作家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提名奖,《人民文学》2018年度长篇小说奖等。
名家推荐
坎坷的遭遇,汹涌的欲想,传奇的缘会:两个女子以生命演义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自在?“凶猛退后,诗意涌现。”风流云转,传奇不奇。李凤群的最新小说,诚挚有情。——哈佛大学东亚系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 王德威
《大野》用鲜活的感觉连通个人与时代,以充沛的元气谱写生命的热烈与坚韧。——复旦大学教授严锋
2018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授奖词
“李凤群的长篇小说《大野》,以双生花式的精巧结构叙写当代女性的成长,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性别、财富流转等诸多命题叠合在人物个体命运的遭际之内,如盐入水,融合无迹,语言精练有力,情节映花照水,冷静疏离的表象之下饱蘸磅礴的同情共感,显示出熟练的小说技艺和人性认知的深度。”
附录1
暗自欢喜胜过锣鼓喧天
李凤群
我脑子里时有这样的印象:一个姑娘坐在门口织毛衣,见到有生人走近,迅速抬眼一瞧,又把眼垂下,继续干活。你以为她什么都不想知道,事实上她什么都看在了眼里。
还有一些姑娘,咋咋呼呼到处赶集,哪里有热闹就往哪里钻,不在乎什么眼光异样,她们笑得火热,好奇和欲望都写在脸上。你只要惹到她,她横眉竖目,脏话如瀑布倾泻。
这两种姑娘有时各自独处,有时又依偎在一起。我总会看见形象和性格都迥异的姑娘并肩走在街上,如此不同,又如此合拍。
你们的记忆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姑娘——或者木讷内向,静静地站在人群之外,或者活泼强悍,充满活力?
时光流逝,我的青春随之消逝了,这些姑娘们也消失了。她们散落在人间的各个地方。我常常想起她们的面容,常常追问:经过这么纷繁的时代,她们的人生,有怎样的经过,后来又到达了哪里?
念念不忘,终有回响。二〇一六年伊始,有那么两位姑娘向我走来。
今宝生于一九七八年,父亲突然辞世,从那场葬礼开始,人们刻意把她往一个模具里面塞。彼时,改革开放,机会数次绕过她的家门,母亲被迫下岗,弟弟们去偷窃。一个小县城的姑娘,没有父亲,没有任何获得成功的机会。她像大多数人一样,个人的生活和庞大的历史之间无限接近,却又无法汇合。二〇一七年,我对她以后的人生大致预计如下:在不幸的事件中,她不会被落下。炒股,肯定亏;丈夫,肯定会背叛;孩子,肯定不太好管教。如此这般,恐慌一直跟随她,她像别人一样,逐渐老去。
但我不能这么写,我要她坚持下来。因为,我想结识一个沉默但却带有力量的、健康的女英雄。
过完年,我继续在寒冷的城市东北郊区和她相处。随着她的成年,她开始拥有自己稳定的性格,并且学会了思考。春天,后院几十种鲜花竞相开放的时候,今宝的形象渐渐变得清晰:她做服务员,端着几千块一斤的“江刀”往客人的桌上送。她看不惯这些粗鄙的食客,但也只能默默顺从。今宝被嵌在这块土地上,无助、沉默、被动,没有奇迹,没有奋力一击的能力,没有从天而降的机遇。她伪装起自己的不适,努力去理解日日新的故事和事故。
二十出头,她结婚,目的明确,找到自己及家庭的依靠,但是喧嚣热烈的时代仍然没有把她容纳进来。譬如丈夫身上的光环褪掉之后,他曾经的形象,他后来真实的性格,他性格里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方,还有他思想的贫瘠,最后落实到今宝身上,远远超过了同情。她将如何取舍?
活着变得无足轻重,好像身体被抽空,价值被磨蚀,存在感被消解,她的处境是我和我的许多乡邻、友人的写照。她无措地盯着镜子的时候,那种艰难、困惑和无奈深深打动着我。
她无力,却并非无能。一种力量生发出来,要带她走。
这时,在桃出现了。
在桃——这个从七岁开始就到世间寻找火柴的小女孩,出生即被母亲遗弃,血液里藏着一团燃烧的火焰,世界于她,是一团灰色的云团。捕捉云团、捅破它,仿佛是她的天职——她嘲弄一切,农场、学校、街道,她用在桃式的咒语诅咒幸福的父亲、年轻的老师、河边钓鱼的老人,她以古怪的姿态横行于世。谁也读不懂,这是她索取爱的信号。
十一岁,在桃便接受男孩子的搭讪,坐在挎斗摩托车上,轰隆隆地穿街过巷,所到之处,恨不得锣鼓喧天。她粗鄙而胆大妄为,浪迹于农场和周边小镇,没有受过任何歌唱训练却屡屡登台演出,跟着草台班子在乡野混饭吃。她想搞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关于母亲,关于爱,关于歌声,关于活在世上的意义。她被欺骗了一次又一次。
出走的今宝遇见了疲倦至极意欲回归的在桃。在桃展现她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生活,今宝却从中看到了苍凉,她最终放弃了出走;而意欲回归的在桃无法理解今宝的沉静:苍白寂寞,生有何益?她掉头继续踏上陌生的旅程。
人世间的爱欲盼望,如日月星辰,千百遍地循环上演。很难说谁对谁的影响更大,今宝一生几乎没离开过这个县城,仅去过一次上海。站上东方明珠塔顶,除了看见更仓皇的伴侣,什么收获也没有。彼时,正值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激情年代,没有人能对飞速变化的生存环境视而不见,人们追逐财富,到处弥漫着物质的香甜。今宝成了底层的精神探索者,她逆潮流,与世无争,用心体察生活,在细微和静默处寻找依存。
在桃呢,继续莽撞探寻,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她想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她要把自己唱出来,她想要有温度的亲吻,她还想要谜底和公道。父亲搬离了家,骑挎斗摩托的男人消失了,她过度崇拜的南之翔离开了她,钟爱她的公务员放弃了她。所有幻想都因为对“爱”扭曲的、不妥协不将就的、缺少节奏的索取而破灭。伤口上挂着长矛,她依然一路狂奔,简直停不下来。她像一个战士,她就是一个战士。她张牙舞爪。搏斗,搏斗,搏斗。看样子,她要死在路上。
许多年过去。
今宝越来越没有英雄的样子,心里装着整个世界地理,却只身在瓦砾间。瞧瞧她的现实处境:到处是垃圾场,没有子女,家庭冷漠,婚姻寡淡,与娘家兄弟决裂,朋友们早就各奔东西,美妙幸福的生活与她无缘。以至于到后来,她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好失去,因而变得更柔软更沉静。表面上,她漠然而自闭,没有态度也没有抵抗,她放弃了一个又一个完成“自我”和走向茫茫世界的机会,没有人捆绑,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挽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选择,就像绳套悬在头顶,她想了一想,把头伸了进去。就像在荒漠深处开放的小花,因为看不见,以为它没有开放,以为它从来没有香过。
她没有变得无耻,她不虚荣,也不索取,明知命运不公,却是满腹悲悯,心系神秘世界,却又审慎克制,既不是无望,也不是充满渴望。她厚德载物,心如明镜。她以沉默保住自己的体面,保住对生活的敬意。她这样的人,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似乎又是复制出来、无处不在的,她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要什么高潮和意外,只要生活本身,并且捍卫“成为自己”的权利。静默的生命获得了强度,她终究脱离了我,成为她自己。
此时的在桃呢?
这个决意跟世界死磕到底的姑娘,她快活成传说中的无脚鸟了,没有办法停下来。她不原谅抛弃她的母亲,她不接受谎言,也不接受虚假的爱情。为了不重蹈母亲的覆辙,她打掉了自己的孩子,并且宣判这个世界人人有罪。在桃绕着地球飞翔,用她的“翅膀”,丈量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个人在与这个世界搏斗的过程中,并不能创造出更多的东西,但是,爱可以。得知那个被自己恨了一辈子的女人并不欠她的时候,在桃百感交集。她的心结,在千百次疾呼之后有了回响——那个“发育迟缓”的弟弟在静静地等着她归来。凶猛退后,诗意涌现,她的奔跑戛然而止。里里外外都是黑暗,爱过的刹那,光照进来,一个时代的画卷铺开,她得以看清人世间的苦痛煎熬:卖花的妇女,在车间里不见天日的女工,拖着残腿写字的乞丐……从愤怒起身,到执念放下,到达慈悲处——也是起身处。
人间的悲喜剧,静静地上演,轻轻地摇摆,默默地反转。
今宝和在桃,或停留在原地,或奔跑在迷途,她们都是赫尔曼•黑塞的“朝圣者”——
我常颠扑于途,
寻庙烧香,
我一无所获,
苦乐皆同过场。
我曾懵然于流浪的意义和归宿,
千百次,
我跌倒,
又把余勇鼓起
我寻找的,
正是爱之星,
…………
如今我认得了我的星,
却为时已晚,
他已背我驰去,
遗我晨雨弥漫。
繁华世界就此别过,
我曾爱之弥深,
即使我无所获,
我仍感不虚此行。
每一个狂放不羁的在桃的心里都有一个今宝,每一个今宝的心里依偎着一个在桃。像一对立在镜子正反两面的姊妹花,相互映照,相互取暖,却永不重合。
现在,我问自己:我是否挽留住了记忆深处那些与我一同长大的少女们?
我不知道。
她们有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
我不知道。
我是否拉扯着她们一起走得更加光明?
我不知道。
创造者从不比其人物高明。最后时刻,我顺从了在桃的意愿,开始与随波逐流的生活和解,和平庸的自己和解,和接踵而至的失望和解,有所屈服,有所承担。
告别锣鼓喧天,方能生出真心欢喜。
附录2
成长的路径——评李凤群《大野》
戴瑶琴
李凤群的小说不是以故事性见长,她的叙事节奏很慢,不制造大起大落与大悲大喜,作品的感伤质素会伴随读者思考的深入程度,显现弥漫。与《大风》大跨度的家族叙事相比,新作《大野》更加聚焦,作家调动人物心理的不断取舍以追随社会的各种浮动,而并非强化或者营造种种人物命运与历史事件的汇合,从这一点看,它跳脱开了“中国故事”常见的叙事套路。需要重视的是,“70”后女性的成长是《大野》所关注的核心论题,在桃出生于1978年,作品一方面表达着写作主体与写作对象的相似情感体验,另一方面呈现“70后”身份共同体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过程中的共同经历,而解开小说的密钥是“比较”与“依存”。
《大风》和《大野》都以人物心理建构,李凤群运用了绵密的叙述针脚,因此它们不适合跳跃式快读的方式,往往会因错过细节而混乱了故事的发展节奏,只有诚恳地从头至尾静心阅读才能理清头绪。我一度以为《大野》会是一部《桑青与桃红》式的作品,实际根本不存在两个人,而只是同一女孩的两重性格。谜底直到小说最后一章《相遇》才完全解开,确实存在一个共同时空,今宝和在桃得以相识相知。她们处于两种生长世界,野蛮恣意与按部就班,但动、静行动的边界模糊。小说里引用《无地自容》的歌词:“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大野》定位于关怀普通家庭的农村少女,跟踪她们屡次“从一种生活走向另一种生活”,就在不断的追索与压抑里踩踏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夯实了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的互相迁就、互相撕扯、互相压制。大众化的故事和人物构思,先期排除了极端情境和特殊人群,以纯粹素朴牵引读者的情绪呼应。
今宝和在桃互为镜像,男女两性互为他者,所有细节互相作用,如同中国建筑的卯榫结构,没有施加戏剧性描写的外力或重力,却将故事与人物严丝合缝地聚合在一起。在桃选择的路向是出走,我大胆地猜测这个名字是与“在逃”谐音,李凤群有意识地赋予她特殊使命,一切离经叛道的行为都被用以肯定自己认可的选择。“我就确定了什么叫不爱,可是我还是一直在找爱,就像一堵墙,你站在墙的反面,你更想看到它的正面。”那么,在桃如何找到爱?她发现的有效途径是通过痛,“痛苦!不管这个痛苦大不大,这终究是痛苦。这痛苦就是粘合剂,贴紧了我和他。”在桃和南之翔的情感际遇,诠释了爱与痛的互相转化。因为痛(温饱)渴望爱(尊重),因为痛(尊重)追求爱(爱情),因为爱(爱情)再次产生痛(尊严)。今宝选择的路向是留下,为了照顾每位家人的感受,必须收藏并压抑自我,混沌度日。“她自己就始终处于无法分清的状态:什么时候做什么,应该爱还是恨,什么时候是哭的最佳时机。”“最糟糕的生活就是这样缓慢的无声的耗损。她想象过不幸,像疾病、火灾、山洪爆发,或像鬼子进城这样不可控的极端事件,但是眼皮底下,生活中最大的磨难却是如此缓慢无声的磨损。这种磨损酝酿出眼下这种模糊的不可比拟不可言说的甚至说不上是痛苦的东西,带着温柔的暗黑的嘲弄意味,让人想哭。”这种“磨损的磨难”,与“70后”作家张惠雯界定的“现代病”是同质的,它是“无法治愈的、现代的烦闷,那种挥之不去也无所寄托的欠缺与失落。”今宝渴望被尊重(家庭与社会)、被爱(丈夫),但父亲临终的叮嘱“替我照顾好弟弟们”时时刻刻警示她将一切个人规划偃旗息鼓。“她突然对着镜子发出一连串的诘问:你是谁,这是哪里,这是在干什么?一惊之下,她猛地咳了一声。声音消失了。因为,她凭着自己的声音,感到自己心如死灰般的绝望。”由此可推断,在对比的视阈下,细化温饱、安全、爱、尊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其实是小说人物设计的一个重要基点。
小说耐心地刻画具有共性的成长诉求:在桃和今宝各自需求对方的生活。两人之间的通信,搭建起一条密道,构成了生命意义的互动。“在桃那大大咧咧的坐姿,随随便便的腔调,甚至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谈话内容,让今宝看到了一种生活的轻盈,在桃身上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自由气息。这种自由她似乎从来没有体会过,在父亲死之前,她隐隐约约有过、品味过,但现在,似乎已经消散,辨认不出它的模样了。现在,她认出了它,在一个陌生的姑娘的脸庞上。”在桃和今宝展示着闯荡社会与相夫教子两种相反的生活模式,而其中却交织着激进与保守两股相同力道的成长冲动,互为“他者”的多义性被阐发。互相检视、体认与思考后,她们发现最通达的方案是回归,化繁为简,先前由个体构筑的理想自我的幻境被完全戳破。
《大野》呈现的是生于“70年代”的农村女孩的自我“成长”,其动因是“你更向往自由,你渴望经历一些故事,遇到爱你的人,看重你的人,看看外面的世界,也看看别人怎么活。”李凤群对它的价值既进行了分析,又给出了结论:人都会在心理向度内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的反复过程中,理解自己、宽宥他人。在桃最终甘于平凡,享受安定,她不断“逃”的动因是“爱”,为了年少的那场“青春梦”,但重遇南之翔后的生活,是她主动推翻了以前一切的“自我肯定”,而选择无尊严地画地为牢。她对“家”的回归,实际又否定了她卑微的爱。今宝在循规蹈矩中抵抗顺从,从起先对婆婆权威的挑战,到一次任性出走,最为极端的是以跑步的方法与孕期较量, 我们从中可以梳理出今宝在被规范化中不断制造出“否定”的拐点。当遭遇丈夫破产、弟弟背叛,今宝对杏红说:“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早上起来就知道一天要做些什么,要发生的事全在脑子里,一桩桩,心里有底。我以前总是在等着什么,一直认为等下去有些人有些事就能变,现在呢,我不是在等什么,就是在过生活。想到这一天全都是为自己过,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我是真的觉得忍耐比自由更重要,因为忍耐向内,要是自己不折磨自己,旁人也折磨不了。”成长中否定和肯定的攻守,制造着成长的过程与代价。
《大野》与《大风》分别围绕着“成长”与“寻找”不同母题,但它们却殊途同归到一个点:爱。无论闯荡还是固守,归宿为家,“我能记住的却是我的亲人,我爱过的、恨过的人,以及迷过路的地方,摔倒过的地方。”埋设在两个女孩之间的感情伏线并非欲望、梦想、自由等宏大主题,而是相遇的那刻,在桃令今宝“闻到了一种特别的味道,这种味道不让人疼痛,却让人产生幻想,这个味道让人想起了远方,想起了爱,想起了忧伤,同时又想起了——家,我的眼泪快要掉下来了。”“爱是个好东西,爱也是个坏东西。爱产生一种力量。”大风和大野,都昭示着释放、追寻和坚强。大风,倏忽间起,导致张家四代飘忽不定的人生,爱却是《大风》里无形的风,在《大野》里依然指引着成长的方向。
沈从文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里说“我老不安定,因为我常常要记起那些过去事情……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时,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李凤群在创作谈中写道:“我总会看见形象和性格都迥异的姑娘并肩走在街上,如此不同,又如此合拍。……时间流逝,我的青春随之消逝了,这些姑娘们也消失了。她们散落在人间的各个地方。我常常想起她们的面容,常常追问:经过这么纷繁的时代,她们的人生,有怎样的经过,后来又达到了哪里?”台港暨海外“70后”华文作家,无论是写“中国故事”还是“他国故事”,他们会主动思索“70后”一代人的独特体验。周洁茹剖析“70后”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孤独,张惠雯揭示美国“70后”华人新移民的烦闷,李凤群反思改革开放时态域中“70后”的成长路径。“我是否挽留住了记忆深处那些与我一同长大的少女们?她们有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我是否拉扯着她们一起走得更加光明?”李凤群在《暗自欢喜胜过锣鼓喧天》里提出了三个问题,答案都是“我不知道”。我认为《大野》是她用文学在挽留与她一同长大的那些少女,但她们以后会怎么样?用句通俗的话说:走一步看一步。这其实也正是写现时态生活的魅力。
戴瑶琴,文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
附录3:
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获奖感言
李凤群
说一说我自己吧。我生在一个鸭蛋大的小岛上,这个岛独立存在于长江主干道和支流之间,俗称江心洲,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去,我们都得先坐船。岛的四周是堤坝,内围种庄稼。夏天发大水的时候,我真的可以坐在门槛上洗衣服。天地白茫茫连成一片,但是,就是生在江边的这个家族——我的爷爷不会游泳,我的父亲不会游泳,我的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全都不会游泳。成年以后,人家听说我来自小岛,第一句话就是,那你游泳一定很厉害吧!事实上,我们不允许游泳。我们家族成员都有这个禁忌,就是不准把脚伸进江水里。兄妹之间若想坑害对方,只要向父母告状说他今天把脚伸进水里,那肯定要挨揍,没有例外。有一次,我实在忍受不了禁忌的诱惑,在父母的注视下,跑到江边。我爸爸就那么看着我,看着我把脚举在江面上,他说,你试一试,你试呀!他的表情凝重,声音低沉,好像那只脚一放下来,天地会为之色变。我退回来了。
为什么?后来我知道,我的二伯父溺水身亡,我的大表兄溺水身亡,每年,我们村上都有大人或孩子掉进长江里。有的会游泳,有的不会,有的被捞起,有的从此不见。我的家族对抗意外的方式就是——躲避它,远离它。
有一次,我终究那样干了,我也真的溺水了,我被拖上来的时候尚有意识。我的父亲奔跑过来。他看到我转动的眼珠子之后,站起身来开始在河岸上奔跑,不是呼救,他知道我没有死。他在喊,快来看哪,快看哪。他让我待在侥幸生还的现场,让邻居小孩子来参观,杀鸡儆猴一样。我难堪极了。但是,语言和真相之间隔着另一条江,需要许多年,我才听懂他声音里隐含的劫后余生的狂喜,他的叫喊——像放了一根双响炮——他想轰走所有的后怕和余忧。
我十三岁初中毕业,到十八岁,一直在做农民。一切农民做过的活我都做过。种玉米,割麦子,施肥,杀虫,我都会。到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人人都在锄草施肥,我也在锄草,天近正午,酷热难耐,突然,我扔下锄头就向江边走,我翻过堤坝,到达江滩,我的鞋子已经沾上了水,一位邻居从身后扑倒了我。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我要去自杀了。
当天晚上我父母、姑姑、婶婶,轮番过来开导我。他们的意思是,不止你一个人干活,你的小学同学,你的邻居,你的表姐表妹,每个人都要干活呀。意思是我们没亏待你,大家都是公平的,也有人从更高的境界做工作。他们说:劳动光荣,懒惰可耻。
怎么跟他们说呢,我不是怕劳动,我也不是死于不公正,我是死于厌倦。水隔开了外部世界,没有路,没有电,没有书,什么都没有,我的少年时光就这么没完没了、翻来覆去地整理几亩地,草锄干净了,一场雨,草又长出来了。永远没有止境。我死于对这种没有止境的生活的厌倦。可是,他们破译不了我的肢体语言,我们的世界没有通向他人心灵的路,他人即天书。
二十八岁到三十七岁,这个九年,我是在病床上度过的,有一种病让人浑身疼痛,不能站不能坐,只能躺着。以前,我也很喜欢讲这一段故事来励志,我的第一本小说是用铅笔写出来的。有人问呀,为什么是铅笔呢。“因为圆珠笔躺着用不出油啊。”我会急急忙忙地补充。但这九年,我真正的癖好,就是买被子。最多的时候,我有四十床被子,各种漂亮的花色,只要天气变坏,要刮风下雨的时候,疼痛会加剧,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就会换洗被子。我母亲总是会纠正我。
你应该天晴时换洗被子。
可是天晴时我不疼啊!
你这是不讲道理。换了被子就不疼了?
可是对于我,新被子就是新的世界。新鲜的花色就是病榻上的空气。
这几件事真是很普通,这样的事我还可以说上三件、三十件,也正因为如此,我也常常想,那些从来平凡的、未曾被听见的、永远不会被注视的生命从开始到结束就真的没有意义,不值得挽留了吗?
契诃夫曾经说过,真正好的作家应该是生活在黑暗中的。我想我就是生活在黑暗里的人,并且我认识许多在黑暗里的人,然而就算是黑暗里长出来的生命,他也是生命,而不是黑暗。我觉得文学,可以把黑暗带到光里来,让亮带到黑暗里去。
事实上,无论是对水的恐惧,无论对做一个农民的厌恶,无论是九年卧床的痛苦,其实都给过我报偿。我父亲在河岸上大声疾呼的时候,已经把大江大河置于我脑海,注定我要完成《大江边》。因为疾病和疼痛,我完成了《良霞》和《颤抖》,两个主人公一个身体不好一个精神有恙。病好后我去了美国,离乡背井之下,我完成了《大风》,波士顿是个极寒的地方,每年有六个月的冬天,我见识了世界上最多的雪,人在自然面前渺小如尘埃。又因为对平庸生活的无力反抗,我完成了《大野》。
这些经历和体验,既是惩罚,也是恩赐,就像今日此刻,既是对写作时光的鼓励纵容,也可能是庄严的误读和误导。
光荣或者挫败,欢迎继续光临!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