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与贺年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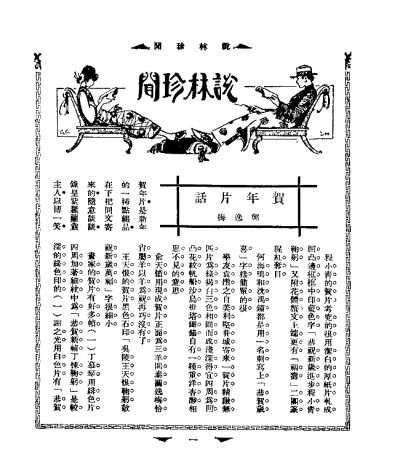
郑逸梅有收藏贺年片的癖好,他在1926年1月28日出版的《紫罗兰》第1卷第4期写有《贺年片话》,历数了程小青、何海鸣、王天恨、丁慕琴、谢之光、胡亚光、周瘦鹃、程瞻庐、范烟桥、徐卓呆等作家、画家各式各样的贺年片,既有来自海外的,又有中式古朴的,既有“在笺纸上寥寥画上几笔,然后再在上面写字”类的,也有“供自己专用的花笺,写上几句贺词”类的,让人目不暇接,“周瘦鹃富审美观念,所以他的贺片也是美丽绝伦,那文字为‘天地易纪日月更始起动安宁所至利喜周瘦鹃恭贺新禧’,用仿宋字,红色印的,左角为紫罗兰图,花娇叶亸,真觉纸上生香呢”。
戏剧家赵景深也有集藏的癖好,作家的书信、结婚帖、名片以及贺年片等都在他的收藏之列,单是贺年片一项,就有一打。他1947年1月1日写有《现代作家的贺年片》,生动介绍了他所珍藏的徐志摩、刘梦苇、吴芳吉、孙席珍、郑振铎、李健吾、徐调孚、焦菊隐、施蛰存、黎锦晖等作家、艺术家五彩缤纷、各具特色的贺年片,“最好的一张是徐志摩的‘海滩上种花’,这是用宣纸印的一幅线条画,还是徐志摩自己画来制锌版的,画的是一个女孩在海滩种花,旁边署著‘徐志摩拜年’五字。徐志摩自己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就叫做《海滩上种花》,大约收在《自剖》文集里,后来又曾被收入中华书局的初中《国语与国文》。倘若这拜年片被当年的徐蔚南看见,他准会收进他那部插图本的《创造国文读本》里去”,“黎锦晖的最为别致,是用注音字母写的红字凸出,边线也凸缓,极为美观”。
《钱玄同贺年柬跋》,是刘半农“仿照罗振玉研究金石甲骨文字的笔法,为钱玄同的贺年片戏作的考古文字”(张耀杰),颇为好玩,不妨全文照录,“此片新从直隶鬼门关出土,原本已为法人夏君樊纳携去。余从厂肆中得西法摄景本一枚,察其文字雅秀,柬式诙诡,知为钱氏真本无疑。考诸家笔记,均谓钱精通小学,壬子以后变节维新,主以注音字母救文字之暂,以爱世语济汉字之穷,其言怪诞,足滋疑骇,而时人如刘复、唐俟、周作等颇信之。……柬中有八年字样,论者每谓是奉宣统正朔,余考钱氏行状,定为民国纪元,惟钱氏向用景教纪元,而书以天方文字,此用民国,盖创例也。又考民国史新党列传,钱尝谓刘复:‘我是急进,实古今中外派耳。’此片纵汉尺三寸,横四寸许,字除注音字母外仅一十有三,而古今中外之神情毕现,可宝也。”
老舍1931年在《小说月报》连载的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中为我们描述了小坡送给全世界小朋友们的贺年片,“全世界的小朋友们!你们可曾接到小坡的贺年片?也许还没有收到,可是小坡确是没忘了你们呀。小坡的父亲在新年未到、旧岁将残的时候,发了许多红纸金字的贺年片。小坡托妹妹给他要了一张和一个红信封。一只小白鸟噘噘着小黄嘴巴儿,印在信封的左角上。片子上的金字是‘恭贺新年’和小坡父亲的姓名。小坡把父亲的名字抹了一条黑道,在一旁写上‘小坡’两个字;笔上的墨太足了,在‘小坡’二字的左右落了两个不小的黑点儿;就着墨点的形象,他画成一个小兔和一个小王八,他托哥哥大坡在带着小白鸟的信封上写:给全世界的小朋友”,“小坡的贺年片是在年前发的,可是你们不一定能在元旦接到。你看,他的红片儿也许先送到太阳上去,也许先送到月亮上去,也许先在地球上转一个圈儿,那全看邮差怎么走着顺脚。就是先在咱们的地球上转吧,不是也许先送到爱尔兰,也许先送到墨西哥吗?简直的没有准儿!可是,你们只要忍耐着点儿,早晚一定能接到的。假如你们看见天上有飞机的时候,请你们大家一齐喊,叫它下来,因为也许那只飞机就是带着小坡的贺年片往月亮上或是星星上送的。还有一层:小坡的信封上,印着个黄嘴的小白鸟,并没有贴邮票,他只在信封的右角上粘了半张香烟画片,万一邮局的人们不给他往外送呢!但是,据我想,这倒不大要紧。邮局的人们不至于那么狠心,把小坡的信扣住不发。他的信是给全世界的小孩儿的,那么,邮局的人们不是也有小孩儿吗?他们能把自己小孩儿的信留起来不送?不能吧。”
朱自清1933年回忆他逛伦敦的加尔东尼市场时,“快散了,却瞥见地下大大的厚厚的一本册子,拿起来翻着,原来是书纸店里私家贺年片的样本。这些旧贺年片虽是废物,却印得很好看,又各不相同;问价钱才四便士,合两毛多,便马上买了……我口袋里那册贺年片样本,回国来让太太小姐孩子们瞧,都爱不释手;让她们猜价儿,至少说四元钱。我忍不住要想,逛那么一趟加尔东尼,也算值得了”。
丰子恺在1936年1月10日《新少年》创刊号上写有《贺年》。范用在《我爱穆源》中回忆,“自己做贺年片,是丰子恺先生教的。……丰先生给《新少年》半月刊写了一系列《少年美术故事》,头一篇的题目叫《贺年》,讲了个做贺年片的故事……看了丰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受到启发,自己动手做贺年片”。
贺年片一般是用来新年祝福的,想不到它有时候还具有别样的宣传效果。陈望道回忆,“1921年新年,陈独秀建议我们到外面去拜年。贺年片上一面写‘恭贺新禧’,另一面写共产主义口号。我们一共七八个人,全都去,分两路,我这一路去‘大世界’和南市。两路都是沿途每家送一张贺年片。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都参加了。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作家们的贺年片也理应成为我们文学研究的学术课题之一,借助于贺年片,我们可以梳理现代作家之间的交游史。“短柬片札,亲手自书,或言国政,或言交情,或言家常,琐屑极细极微之事,大抵皆仓卒濡毫,不假修饰。寥寥数语,流落人间,而其人品之醇驳,性情之邪正,往往于无意中流露而出。则以言观人,莫尺牍若也”(黄虎痴),现代作家们的贺年片也当如是观。
(作者:宫立,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