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视域下的科幻地形图
《给孩子的科幻》有一个颇为冷酷的开篇。想要提早见到哥哥的美丽女孩偷乘了要执行救援任务的急遣船,却不知道这类飞船没有任何富余燃料,等待她的命运是被抛出船外,在距离哥哥工作星球咫尺之遥的地方变形为一具丑陋的尸体。
让汤姆·葛德温这篇极富争议的代表作率先出场,可能有编排上的偶然,但《冷酷的等式》一文在中国科幻视域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却已然标识了刘慈欣和韩松编选全书的思想坐标和深层逻辑。按照研究者王瑶的分析,《冷酷的等式》(又译《冷酷的方程式》)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核心意象“理性铁笼”的原初文本,几乎所有当代中国科幻作者都尝试过对它进行模仿、变奏、颠覆或突围。也就是说,在这样一本“给孩子系列”的开头,编者就以超越日常的残酷,给出了中国科幻的关键问题与焦虑核心。

▲《冷酷的方程式》早期出版时的封面
以这样的方式向孩子打开科幻,联系着编者对“孩子”和“科幻”不同寻常的理解。在韩松看来,孩子和科幻本身就是一种同义反复,“科幻本身就等同于年轻和梦想,代表了人类这个物种目前正在经历的童年时代。我们接受它,就是肯定我们自己,从而树立起对当下和未来的信心”。也就是说,这本选集并不意在为刻板印象里无辜无知的孩子提供某种定制低幼的“洁本”,而是希望经由科幻来召唤和牵引一批属于(代表)人类未来的孩子。
《太阳风》中意外不断发生却仍要驾着光帆驶向远方的豪情,《霜与火》里对严酷生存环境和仅有八天的生命周期的超脱,《追赶太阳》中遭遇意外的幸存者以绕月球表面一周的脚印写下的生命意志的颂歌,都是科幻文类以最具体可感的方式对人类精神的想象和再现。而这些仿佛《地心引力》《火星救援》前身的故事,也应和着我们通过好莱坞科幻大片习得的对于科幻的日常想象。但编入这几篇小说和阿瑟·克拉克、雷·布拉德伯里等英美科幻大师的名字,并不意味着韩松和刘慈欣在搬运复制英美世界中某种“天然的”、抽象的、无国别的人类,他们的选择是坐落在中国科幻视域之中的。这是一份中国科幻共同体的核心索引,当我们顺着《给孩子的科幻》进入一个科幻议题时,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份地形图的导引下,体认着(叠加起)不同时期中国科幻人对同一主题差异性的阅读和思考。
最为有趣的一组例子是围绕“进化/演化”的三篇小说(《雪山魔笛》《熊发现了火》和《水星播种》)。童恩正的《雪山魔笛》用一种报告文学的笔触,讲述考古调查队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古刹旁意外发现了神秘生物的痕迹,在科学集体的缜密设计下,揭示和发现了一支存留至今的猿人,以“活化石”见证(填补)了从猿到人的人类进化链条的中间环节。小说满怀社会主义式的对自然没有恐惧的好奇和激情,宗教和传说在故事里只是佐料和调味剂,真正的满足与欢喜来自印证(或补完)达尔文进化论、赫胥黎人类起源说,科学轨道仿佛更加完整的那个时刻。
这份因科学“完成”而欢欣的情绪并不为《熊发现了火》分享,特里·比森描绘的是一个怪诞得多的情境。这一情境就是小说的标题——熊发现了火,这个在日常语境中荒诞不经、在幻想语境下又好像平淡无奇的事件之所以诡异,用刘慈欣的概括就是“地球的智慧文明本来有各种可能性,这一种似乎早就该发生了”。也就是说,特里·比森正好逆转了童恩正的思维实验,展示了如果进化论/科学假定的可能性(准确地说必然性)在当下被印证,当学会了使用工具、使用火的熊“入侵”现实人类世界,面对这种奇特景象普通人的生活将怎样被改变(或不被改变)。换言之,科学不再是一种有待印证的必然性,而是召唤奇特状态、创造新关系和新连接的可能。而这正是自认“新左派”的特里·比森通过“后新浪潮”式的写作对另类可能性的想象与再现。
颇有意思的是,这两篇小说对科学自身的必然性和带来的可能性的对位呈现,也在无意识中打动了设计者,选集的封面图画就是“举着火把的熊隐身在巍巍雪山之后”——可能性高擎火炬藏身于必然性之后。当然,无论《雪山魔笛》还是《熊发现了火》都并非当代中国科幻讨论“进化”的主流范式,更多故事中人类已经取代了大自然来操弄必然性和偶然性。描绘这种“僭越”的代表作者就是王晋康,而《水星播种》正是最成功的一篇。故事并没有平铺直叙地描绘一种人造的硅锡钠生命从低级形式向智慧生命演化的过程,相反,它将相隔亿万年的两种生命视角(人类和索拉星人)穿插交互,外星人面对的神秘情境通过当下的人类故事获得诠释。更为震撼的是人类企业家的缜密计划遭遇了毁灭性的意外,故事结束在(被创造的)外星人自身的历史逻辑中。
残疾的人类想要弥补自身的缺憾,最终却导向了后人类的结局。王晋康讲述进化的方式已经在不经意中显现了现代主义发展逻辑的悖论,也把我们引回当代中国科幻的核心关切——人类该如何存续于这个资源有限的地球/宇宙(中国在资源有限的地球该如何发展的升级版本)。而这也让我们进入了该选集中最具戏剧性的场景,刘慈欣和韩松——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两位科幻作家互选对方的作品,韩松挑选了刘慈欣的《微纪元》,刘慈欣则选择了韩松的《宇宙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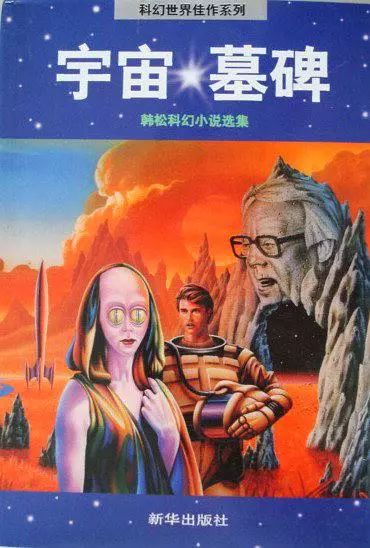
▲《宇宙墓碑》早期出版时的封面
熟悉刘慈欣的创作和言说会知道他是太空技术和“星辰大海”的虔信者,在刘慈欣的作品中困守一般绝没有好下场,《三体》系列里通过让光都无法逃逸进行自我防护最终导致自我湮灭的“光墓”就是对困守立场的形象化讽刺。然而《微纪元》却并不分享这种“开着地球去流浪”的豪情,作为刘慈欣序列中相对早期也极为特殊的一部,面对极端的灾难状态,人类社会选择了用基因技术将个体缩小 10 亿倍。由此,人类社群得以保存,而消耗资源极少的“微人”也创造出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乌托邦。这里最动人心魄的一幕是从太空中归来的唯一“宏人”在见证了微纪元的完美生活后,主动焚化了所有留存的宏人胚胎细胞。用灭亡高耗费人类的方式来完成对另类“后人类社会”的认同。这种决绝的姿态,以极高的强度显影了危机的深重,而这也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科幻作为文明预警的自我期许。
相比而言,韩松的晦暗从来都是更为彻底的。《宇宙墓碑》作为整本选集最神秘莫测的一篇,是一个来自现实也抵抗现实的隐喻——凡记忆的必将被遗忘,无论人类进行了多少建设,宇宙都将恢复它作为一座大墓的状态,然而在最后的黑暗来临之前也许还会留有一些格调迥异的存在。

▲作家刘慈欣
作为一种舶来文类,科幻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发展史,但某种科幻亚文化圈却是八九十年代以来才渐次形成的。很多著名科幻作者都是通过阅读外国科幻(主要是美国黄金时代科幻)获得了最初的灵感,开始自己的本土写作的,到 2015 年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可谓完成了一个惊人的旅行和翻转。
而更为奇特的是,促成这一翻转的译者刘宇昆也是一名华裔。当然如果仅仅将刘宇昆理解为中国科幻面向美国、面向世界的译介者和推手,则忽略了他自身写作的成就。在选集收录的《宇宙之春》中,刘宇昆以陌生化的笔调,描绘了一个宇宙春节的到来。在结尾庄严的诉说中,新生的宇宙将幻化为北京西站的模样——“太空中群星组成的一个图案——那是一座长方形桥梁,层层叠叠的塔楼为顶,道道裙檐累累下扑,他们会将其命名为‘戴高帽的矮蜘蛛’。因为他们理应知晓些先辈的事迹,知晓他们自己来自何方。”这是一份经由科幻中介的深情,身处离散状态的华人对于中国不灭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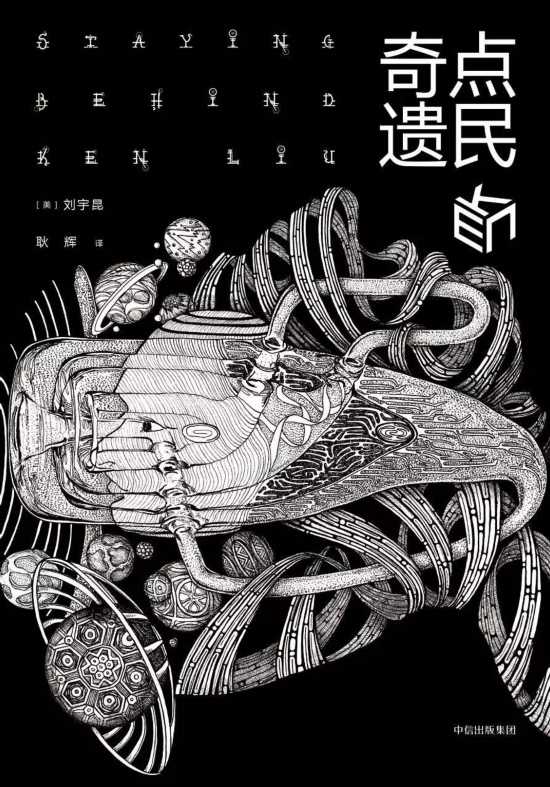
《奇点遗民》
[美] 刘宇昆 著
耿辉 译
中信出版社 出版
比刘宇昆更具知名度的华裔科幻作家是特德·姜。作为当代最优秀的短篇科幻小说家,特德·姜的每一篇小说都极为精彩,《巴比伦塔》更堪称他最完美的作品。相比被改编为电影《降临》的《你一生的故事》,《巴比伦塔》通过一砖一石构筑了一个更加完整生动的世界,惊奇感灌注于每一行和每个场景的转换中。当凿穿拱顶的时刻到来时,读者会和小说中的矿工们一样屏息以待。也是借由这样一篇违反所有科学常识、却充满工程细节的“巴比伦人的科学幻想小说”,编者重申了科幻中想象力的力量——科幻绝非现有科技的推论,而是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权力。而这可能也是编入潘海天《偃师传说》的原因,由科幻打开对中国神话的重新阐释。

▲电影《降临》剧照
选集收束于陈楸帆的《造像者》,经历了中外漫游的读者回到了中国科幻自身的脉络。作为更新代的代表作家,陈楸帆有着对于中国现实和技术现实的双重敏感,他在处理近未来题材时不是将其放置在一个有别于当下的时空。相反,《造像者》这类故事极有可能就发生在此时此刻。他所做的是捕捉这种寓于此刻的未来,以描绘在新的媒介技术形态下普通中国人将如何生活、如何思考。而这可能也是面对“未来已至”——科幻小说中最狂悖的梦想纷纷实现而手足无措的我们更需要的思想准备。
当然,仅仅十五篇小说所能形塑的也只是一个充满遗憾的轮廓,单一的性别、两三种国别都提示着这是一份理应扩展可供批判的地形图。手持这份导览的孩子或大人,理应望向更远的远方。然而可贵的可能也是这种极简和狭隘,允许我们在路程的开始一窥位于中国科幻视域中心的症结和洞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