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碎片记忆 彰显人性光芒——2017中国文学回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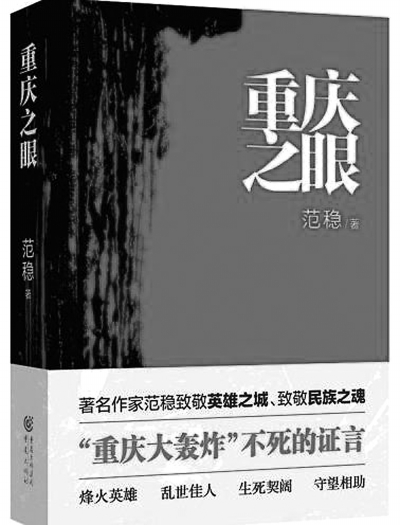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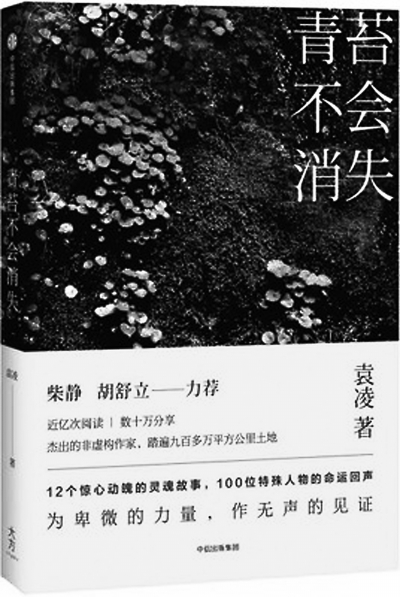
现代个体的庸常生活平淡无奇,同时又面对新媒体追新求异的信息轰炸,对于身处“迅捷、多元、多功能”现代生活中的人来说,真相和真实远比任何时代都更为扑朔迷离。我们身处真实和真相之中,同时真实和真相又往往遥不可及。文学如何去呈现和照亮超出一般个体认知能力的现实?文学和现实复杂而诡异的关系成为当下写作者焦虑的根源,写作的碎片化、焦虑感和批评的无力一起折射出文学自身尴尬的境地。批评话语试图通过“文化”、“权力”、“经济”“欲望”、“理性”之类来阐释文学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然而现实自有其发展的逻辑和节奏,作家也有着个人化的经验模式和叙事方式,由此文学阐释往往既没有站在作家的立场,也没有考虑读者的期待,而是在当代哲学和文化文学批评的各类范式中进行着第三者的自我独白。 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2017年依然是文字工匠在自我与他者、历史与现实、人物与命运纠缠中的笔墨生涯,写作像是有着无穷魅力的苦役,让作家欲罢不能。对于专业阅读者来说,一年的文学阅读是耗费心力的大工程,然而在海量的写作文本中,所有的个人化阅读依然只能是管窥蠡测、不能见全豹的一瞥。
1.从启蒙他者到现代个体——“我”的精神生长
如果说鲁迅一代知识分子在启蒙大众的层面上写出了灰色小知识分子叙事文本,而当灰色小知识分子终于在衣食无虞的环境中成长为一个现代人的时候,这种生长性更加体现在个体对自我的现代身份、人格、伦理和情感状态的独白和反省。一批作家开始探究灰色生活内核中的心灵镜像,在对内心复杂性的剖析中,试图叙述现代知识分子面对自我的忏悔与救赎。基于现代个体漂泊的宿命,“救赎”依然是个体自我走向阔大的有效途径。在传统、权威、科学和理性被解构的时代,基于个体的道德律令和人格建构的反思无疑非常值得珍视。《丹麦奶糖》(刘建东,《人民文学》2017,1)中出现了一个现代的“我”,这种第一人称叙事不同于现代文学中第三人称的“零余者”。“零余者”大多在家国之痛和个人命运多舛的维度,以个体的悲剧映射社会的不公。然而当一个现代人拥有一定的生存自由度,饱暖的世俗生活让我们感觉平庸的无趣时,又如何面对引诱灵魂和肉身的权力和欲望?文本在现代物质主义生活方式中表达了社会成功学和功利主义对人精神的腐蚀与戕害,这种精神性痼疾细微而幽深地隐藏在日常经验的各个角落,在习焉不察的情境中,让人之所以为人的“信”和“念”成为蚀骨噬心之殇。《心灵外史》(石一枫,《收获》2017,3)中也出现了现代的“我”,这是一个不仅仅以吃饱、穿暖、买车和买房为生存标高的文学人物,在对“大姨妈”的体贴、同情与理解中,“我”个人被挤压的生活则汇聚到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精神救赎中。文本以个人化的方式呈现出时代变迁中人真正的信仰、情感和伦理困境,这种对自身困境的体认、左突右冲和忏悔反思无疑体现了“后苦难时代”的现代人自身精神的生长性。《水岸云庐》(蒋韵,《长江文艺》2017,7)通过主人公中年危机中对于日常性的出走,在复仇主题中完成个体自我的精神救赎。《黄棠一家》(马原,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0月)回归现实叙事,对中国现实投去颇为独特的关注,文本中的时代和人物都带着马原一代作家的底色。《平原客》(李佩甫,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2017年8月)无疑让人遥想到战国的门客和“士”文化,同时在一个“士”式微的时代,精英和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成为工具理性和世俗功利主义的隐喻和象征。
对于中国人来说,身体解放既意味着远离物质匮乏,又意味着解构传统伦理。在浅薄的意义上,这两者都会带来解放之后欲望无边的释放和释放之后的虚无。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利他的、道德的、伦理的重负被消解于个性和利己主义的张扬,然而精致的物质主义也无法掩盖精神匮乏症的怅然若失。或许当现代人宣称“我是我自己”,以个体所谓的肉身、情感与理性为自己正名的时候,上帝、传统、历史、道德和伦理的重负轰然倒塌,这时无边的困惑和孤独就成为现代人永恒的宿命。然而人文主义的深度正是在悲观主义止步中起舞,如何在痛感叙事中起舞,艰难地叙述中国现代人的精神生长,可能是当下中国叙事重建现代世俗生活合法性和审美价值的题中之义。
2.日常性的记忆碎片与非日常性的审美观照
莫迪亚诺曾经认为小说家的使命是拾起人类命运的碎片记忆。碎片记忆是易于拾取的,而人类命运的叙事则是考验作家对于整体社会经验的文学性表达。写作即便是记忆碎片,也应是人类命运的记忆碎片。如何从日常性记忆碎片进入文本叙事层面,再进入人性和历史的纵深,体现出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故事星球》(彭杨,《人民文学》2017,4)在对当下城市生存的日常性进行叙事的同时,关注职场生存中最具有冒险精神的创业一族。小说将青春梦想和市场、资本、网络元素整合在主人公的奋斗史中。时代新人阿信在向着未来狂奔的路上,因为有着遥远的“故事”和对“星球”的向往,一代青年才有可能成为在时间维度上留下印痕的人。《生死课》(胡性能,《十月》2017,5)讲述死亡是日常的、又是溢出日常的经验。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检验我们对于死亡的姿态。叶弥《下一站是天堂》在对于神秘现象的讲述中抵达日常性的真与善。王祥夫《怀鱼记》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写人性,主人公癔症式的自我救赎被当作嘲弄和调侃的对象,文本隐喻着以对立、豪取和贪婪为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小说论证了一个古老的观点:世人愚蠢,时间盲目。我们身处日常,更深处时间和历史之中。然而,不自知、不自觉乃至无法真正“觉”和“悟”依然是人性致命的弱点。
非日常性依然是作家更具超越性的审美追求,作家在个体非日常性的叙事中,呈现出对于文学性的强烈自觉和文学创新的冲动表达。《自我、镜子与图书馆》(李浩,《作家》2017,10)中,非日常性以戏剧的方式进入日常,戏剧舞台直指人心的“自我”,“我执”是人类的宿命还是诅咒?《双生梦》(晓航,《青年文学》2017,4)依然从科幻的维度突入当下中国现实,以幻想的残酷真实来论证现实的超现实。夏商《标本师》是智性写作,小说家在轻盈的叙事中融入沉重的人性主题,在知识性叙述中保有丰沛的情感体验,在个体性生存图景中隐喻现代人的困境。《众生:迷宫》(黄孝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以自己独特的文本意识和文学观念构造了一个巨大的迷宫意象,在文本和观念两个层面实践着作家的先锋意识。《国王与抒情诗》(李宏伟,长篇小说,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5月)在幻想的叙事模式中注入对于当下现实的深度思考,文本形式上的非常态和文本内容的非日常性一起让这部小说充满着先锋气质。
3.历史与现实罅隙中的伦理表达
在烟熏火燎的当下,回溯和重构应该是慢的,是细小而真切记忆中的幽微情意。只有通过这种幽深而锐利的表达,我们才能真正抵达记忆的真实,从而趋向对于历史和人性真实的文学叙事,文本言说个体生命经验的幽微之处却指向对于时代整体性精神气质的呈现与照亮。《少年吉祥》(张之路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2月)以散文笔法营造小说意境,用凝练精粹的汉语生动地讲述了大变动时代的中国少年和中国故事。《天堂来客》(肖克凡,《山花》2017,3)在幽默风趣的平民化叙事风格中,凸显了寻常百姓在历史夹缝中的卑微生存景观,以及这种景观中所凸显的时代精神气质。《十三姨》(陈永和,《收获》2017,1)在回望的视角中,我作为一个冷眼的“小辈”目睹了自己的“长辈”十三姨落寞而衰败的生活史。那种一辈子没有走出自我的孤独突兀地呈现在文本中,显示出作者对于幽暗人性的感伤与抚摸。《祖先与小丑》(雷默,《花城》2017,3)精准地描述了死对生者的折磨,摹写了对于逝者的祭奠仪式以及这种民间类宗教仪式带来的对于生者的安慰。这种叙事无疑显示出民间风俗最原初的宗教意义和精神性。潘灵《偷声音的老人》在历史的时光中镌刻深入内心的记忆。李铁《送韩梅》在残酷的生活真相中融入一丝温情,也带着对于人性真实的淡淡揶揄。凡一平《上岭村戊戌年记》通过对乡村的记事,表达对乡土伦理的重新认知和思考。《七层宝塔》(朱辉,《钟山》2017,4)在对乡村伦理坍塌过程的摹写中,凸显了生存法则和现实世界的芜杂与混乱,人性在时代进步的物质功利中日益复杂而扭曲。《梁光正的光》(梁鸿,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1月)叙述一个面对时代和历史充满着生活热力的中国农民,他在俗世生活中执着于心中的“光亮”,孑然前行。
在过度娱乐消费的大众文化叙事中,历史无疑正以碎片的方式镶嵌到国人的精神镜像中,历史被称为“奇幻想象中的博物馆”也并不为过。文学依然是抗拒大众奇幻化历史叙事的有效方式,很多作家以悲悯情怀和救赎意识来对历史进行深度的文学叙事。《重庆之眼》(范稳,长篇小说,重庆出版社,2017年3月)锁定抗战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在历史苦难镜像的投射中,作家对于人、战争、战争对人性的戕害进行了颇具历史深度和现实性的叙写。《猎舌师》(房伟,《当代》2017,4)在传统文化中注入最惨烈的历史片段,在颇具符码象征性的时空节点上,人性被放在苟活与安逸中去考量大义、伦理和正义,文本细腻地刻画了小人物面对大历史的姿态。
4.线性进步的现代城市及其表情
线性进步的城市依然是当下文学表达最集中的区域。现代城市的表情更多呈现在对于个体、婚姻和情感的现代性表达。当下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失范,现代价值观多元混杂,物质主义生存对女性精神的侵蚀无疑是令人惊愕的,女性对于自身状况的认知和反思呈现出保守和退让趋势。曹军庆的《向影子射击》在对特权阶层的控诉中,更让人刺心于女性主动性的物质奴役。宋尾的《隐身》通过荒诞的叙事隐喻城市和城市女性的灰色命运。后刘巧珍时代的村姑们也只能开始了在异乡的漂泊,无根感是寄居城市的所有人的乡愁。王安忆《乡关处处》(《长江文艺》2017,5)中,城市对于乡土中国的月娥们来说已经变成了生存的第二故乡。《摩擦取火》(陈仓,《芒种》2017,9)是陈仓的后进城系列,人和城的关系依然发生着令人心惊的裂变。一代青年被物质功利主义所豢养,自然成了“自恋的享乐的一代”。余一鸣的《求诸野》在非常普适的层面上叙述了中国父母的伦理担当,以及这种亲情伦理在现代城市生活中遭遇的尴尬与无奈。于是在一代新人身上能够发现对于金钱和权势的膜拜,而无法看到发自内心的对于伦理的“善”的尊敬。
对于现时代中国女性来说,生存的紧迫性压倒了身体和精神的觉醒,无感或者假装无感依然是当下女性逃避精神性痛苦的无奈选择。身体叙事依然行走在众多女性叙事的文本中,但也有很多作品从简单的伦理和道德判断中抽身出来,进入现代婚姻内部去表现婚姻中平庸的恶和恶意。《你还是年轻人》(文珍,《小说界》2017,1)、《简单生活》(傅泽刚,《北京文学》2017,4)和《AL》(李静睿,《单读13·消失的作家》)都直指现代婚姻的隐疾。张天翼《春之盐》探讨了最能透视中国式婚姻内核的产后生活现场,产后的抑郁是生理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
在城市的线性进步中,人被放置在“欲望”、“功利”中煎熬,人性在善与恶中被打量,男人和女人在远离传统的不归路上寻找着、或者失落着自我。《精血》(陈希我,《小说月报》原创版2017,2)以精准的手法摹写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形象,在现代生存法则的调教下,个体跟随着内心的欲望生长着,在平庸的“恶”中败坏了自我也毁灭了他人。刘爱玲《秘密的N次方》通过代孕女孩的经历揭示了当下成人世界的扭曲变态。《无边无岸的高楼》(韩永明,《当代》2017,6)现在时地描述了快速拆迁的社会现象,进入城市化高楼生存的乡土人物是如何迅速坠入现代物质主义的暗疾中,传统亲情和伦理转瞬间被欲望瓦解,人性暴露了最不堪的软弱和自私。《好人宋没用》(任晓雯,长篇小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通过讲述中国好人来阐释对中国式传统伦理和价值的坚守。《奔月》(鲁敏,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0月)中逃离成为人生的另一种反转,反转背后投射的是人性及其背面的幽光。《藏珠记》(乔叶,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2017年9月)叙述了人在历史与现实中的穿越,人性在灵肉之间的撕裂与纠缠。《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长篇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通过荒诞反观当下生存的黑色幽默本质,笑声中依然充斥着划破脑际的尖锐回声。
5.语言、非虚构:前行的风景与难度
2010年《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栏目,将非虚构文学正式带入主流媒体。梁鸿《中国在梁庄》、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李娟《羊道》、阿来《瞻对》成为中国非虚构写作最早的一批作品。其后何伟纪实中国三部曲——《消失中的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将非虚构写作推向又一波高潮。近几年,中国作家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写出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从不同的维度叙写中国当下的经验,这类写作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学表达。近期国内涌现了许多新兴非虚构写作平台,多以微信公众号、线上线下写作社群的形式出现,越来越多人关注非虚构写作,非虚构为影视输送故事,内容变现的能力骤然加强。2017李娟《遥远的向日葵地》(花城出版社,2017年11月)依然给读者带来惊喜。袁凌非虚构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月),收录了一百位中国社会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在痛感叙事中,作者对日常和现场进行还原和再现,用文字记录时光、疼痛和苦难。非虚构是当下重要的一种叙事方式(或写作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非虚构写作的生长性、不确定性和异质性又让写作者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非虚构写作尽管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写作现象,但是依然不能被称为“非虚构文学”。与此同时,从写作技术的角度,非虚构也面临着创作质量的提升,文本特征的辨析和文体风格的梳理和界定。尤其对于当下的汉语白话文写作来说,非虚构写作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源流和承继关系也有待更为深入的探讨。
总而言之,文学依然存在,然而文学写作和文学阅读的分化已经成为批评者必须正视的问题。和现代文明方式的转变一样,文学样态的转变已然成为现实一种。从传统文学的阅读角度来看,读者的阅读期待是多层面的,对于读者来说,文学意味着向火取暖,寻找到自己喜爱的作家和作品。对于批评者来说,阐释的目的是为了引介阅读,更是通过经典化让真正的杰作传之后世,当然,后者在当下是充满难度和挑战的工作。
我们希望通过文学写作和文学阐释来了解时代的本质真实,因为真实是用来反思的。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言,如果把“认识”和“思想”比喻为鸟儿在丽日晴空中翱翔,“反思”则是在鸟儿在薄暮降临时的悄然起飞。因此,作为哲思的文学依然还需要耐心地等待——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