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的“初心”与突破
史诗的重建其实在于信仰的重建,在于价值阐释与评判系统的重建,在于身份认同体系的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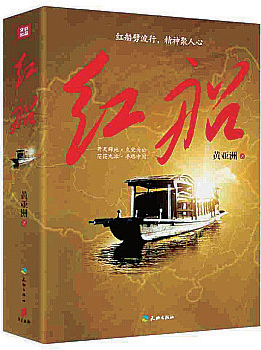
长期以来,弘扬主旋律的文学作品被创作者视为畏途,接受者亦视作鸡肋。从材料史实的耳熟能详,到讲述套路的语重心长、慷慨激昂、甚至悲愤苛责,阅读的陌生感和激动早已被审美疲劳代替了。简言之,我们要重建这一题材文学作品的魅力,首先要找到并直面其被空洞化的原因,进而开启与时俱进的新的探索路径。曾经的“三红”革命史诗、《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革命英雄传奇,具有巨大的召唤力和崇高的历史地位,但其接受语境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年的“民族仇、阶级恨”已不是新一代公民的成长语境与身份记忆,更已不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当代的“主旋律表达”面临着转型与重建的大课题,当代人的精神混乱、信仰缺失有其根源,恰也从反面呼吁着主旋律艺术二度阐释与重建的迫切性。
正是在此背景中,黄亚洲长篇小说《红船》的出现就显得格外重要。史诗的重建其实在于信仰的重建,在于价值阐释与评判系统的重建,在于身份认同体系的重建,换句话说,在于对“诗”的呼唤,在于对诗这种审美表层意象之后的“魂”的重建。历史上,立足于阶级性基础上的“民族仇、阶级恨”曾是这样全民共振的魂,而新的历史格局呼唤新的魂,这个魂是“托古而改制”的,是脱生于旧魂躯体之中,是对旧魂的继承与发展。有了魂,才会有诗,有诗才能带史,有了史诗,才有全民的认同共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旧魂与新魂转型的归纳,是对“初心”的阐释,也是“使命”下对“始终”的期待。不识“初心”,就无真魂,就只知教条与威权,就不敢开拓,也不敢创造,当然不会有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也遑论自由感与幸福感。船只是一个地点、一个物品,船是人的代称,精神更是人的特质,所以,艺术需要把住精神实质,就是首创、奋斗、奉献的抽象精神,进而来完成艺术化的自主理解和独特创造。这本身就是突破禁区,就是思想解放,需要史实、史识、史胆。
黄亚洲所说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正是有了这个魂,才能把握实质,打破以往的僵硬化、脸谱化痼疾,将陈独秀、毛泽东、孙中山、马林等众多人物群像塑造得灵动活泼,个性鲜明,放开人性的自由。“初心”其实就是一个梦想,是对于人性自由和社会解放的期待与奋斗,以往以阶级性为魂是历史的需要,是破坏旧制度和斗争的需要,而今天将阶级性上升为人性则是继承和发展的需要,是建设和改革的需要,是“初心”的具体实现。有了这个活的魂,人物才能活起来。人物活起来,已经熟稔的历史故事才会重新鲜活起来,群像与史实互动,灵魂与个性贯通,才会重现大气磅礴的历史画面,才能实现现实的激动与精神召唤,史与诗得以汇合共生。
有了魂,就有了胆,有了胆,就有了创作自由。《红船》充满了妙喻,如借陈独秀之口将马林称之为“牛林”、又称之为“猫林”,就大胆而生动贴切,中国革命的本土化、独立化要求与共产国际的合作、斗争,充满悍霸之气的陈独秀由愤懑反抗到屈服盲从的变化,马林的丰富斗争经验,以及串联起来的丰富的故事等,都尽在一词道破。此类妙喻层出不穷,举重若轻,正是创作者自由人性的任性挥洒,是文学难得的自由与解放。
活的人是有魂的,这魂大言之表现为信仰,小言之则表现为日常化和细微处的情怀和情感。小说中坚定的信仰求索其实正是在日常细节的情怀与儿女情长的情感中得以真实具体地建构起来,这不是反英雄,而是真英雄自风流。豪情、悲情、温情,均有多处感人场景,陈独秀父子情、邓颖超母女情、毛泽东新婚燕尔的温情与“我失骄杨”的凄切缠绵,均化为读者“身边人”的感动。侠骨柔肠、铁肩道义与儿女情长并不矛盾,而是相得益彰的。
《红船》的史诗品格建构断非一日之功,有作者20年来的增删,历《开天辟地》《日出东方》《建党伟业》等几步阶梯的探索,此外也还得益于多种艺术门类之间的滋养与融合。黄亚洲既写诗,也写影视剧本。作品中人间性的丰富、画面感的突出、形象化的绚丽,叙事节奏的张弛有致,笑点、泪点的迭出,都可以鲜明看出影视创作的养分。在妙喻意象的举重若轻与信手拈来间,结构、情节全篇开阖有致,对宏大历史实现了形象化的巧妙勾连。于是,作品有了魂、有了人、有了情、有了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