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生态美学”
与其说许辉是位作家,不如说是一位乐水的“智者”,一位有情趣的“生态美学家”。
许辉的“湖湾”是独特惟一的,沈从文的“湘西”、梭罗的“瓦尔登湖”也是独特惟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独特惟一”就是成功。然而,许辉又似乎并不看重这种成功。“人有时间、有精力、有情绪、有心境,在水边走一走,自愿地晒晒太阳,只能说是人生的一种成功,而不能说是人生的一种失败。能够支配自己的人生,还不就是一种成功?”毫无疑问,许辉更为看重并已然获得了这种支配自己人生的成功,这是智者的“成功学”,也是人人慕求的一种境界、一种“生态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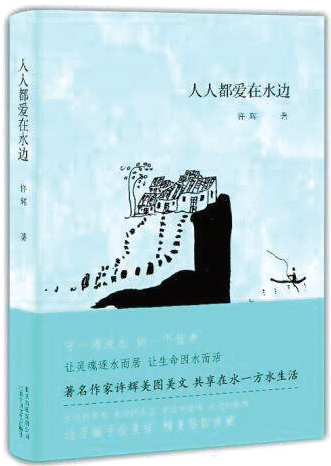
日复一日地“一个人在湖湾的湿地边行走”,在湖岸边“想东想西想迷离”,走着走着,想着想着,许辉便有了这本图文并茂的“自然之书”——《人人都爱在水边》。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活在水边是古人的首选,也是许辉的必然选择,因为在他看来,“近水就是近柔,近柔就是即色,即色就是平衡,平衡就是心态,心态就是人生,人生就是天地,天地近在水边”。一个人在水边行走,观看、冥想,或以我观物,或以物观物,或进到自然万物的生命根底,或沉入四季轮回的时间深处,不悲不喜,不忧不惧,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一切安然、淡然、自然而然。与其说许辉是位作家,不如说是一位乐水的“智者”,一位有情趣的“生态美学家”。
这是一本小书,因为它不到10万字,每篇大都只有几百字;然而,这又是一本大书,因为它容纳了“两个世界”,蕴涵了“一种美学”。
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常人司空见惯又习焉不察的“自然界”,蒲草、楮树、牛筋草、毛谷谷草、空心莲子草、打碗花、牵牛花、田旋花、鸡爪花、芦花、红蓼、荇菜、芡实等各种植物在这里生生不息,野水鸡、野斑鸠、牛背鹭、喜鹊、湖鸟、蜻蜓、黄鼠狼、鱼虾等诸多动物在这里繁衍不断,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只是些“鸟兽草木之名”罢了,而对于作者却是“满脑子里最关心的事物”。恰恰是这些在常人眼中微不足道的事物、平淡无奇的自然,让“我”不由得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超凡脱俗、返璞归真的“心灵界”。在行走中减负,在观照中去蔽,在坐忘中澄明,“身体里负面的东西可能也都在行走、观察、用手机拍照、看水面、看天空、看树林的过程中释放掉了,因此觉得十分轻松、通畅”。很显然,“物”“我”两个世界并非绝然对立、各行其道的,而是相互催动生发、彼此应和融合的,如刘勰所言“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或如许辉所言,“我能听见草毯山一起一伏的呼吸与我的呼吸同步,我能看见山川大地的脉动与我的脉动合拍”。如此,便有了些“天人合一”的意味。这种“天人合一”亦即蕴藏其中的“一种美学”——“生态美学”的旨归所在,也就是说,建立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这对于充斥着市场拜物、工具理性泛滥、环境严重污染、心理疾患漫延等等问题的当下而言多么难得,又多么令人心驰神往!换言之,这是许辉一个人的美学实践,又何尝不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生活”呢?
所以,许辉是智慧的。他既懂得“植物自然有它们成长的禁忌、领域和规律”,也懂得“它们并非是为让我们意识到而存在在那里、而坚守在那里的”,更懂得“生命无论大小高矮,都是伟大的,了不起的”,因而,他只是旁观这些生命的变化重生,尊重其天命,从不干扰它们的生命进程,并由是而反观自己的生命。对于许辉而言,“观物”即“观我”,“近水”即“近道”,这“道”主要指向道家之“道”。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谈到儒道互补时曾说,“千秋永在的山水高于转瞬即逝的人世豪华,顺应自然胜过人工造作,秋园泉石长久于院落笙歌。”人世不及山水长久,人工不及自然天成,故道家之“道”意在投入自然怀抱,寄情山水,归依天地,在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之外,建构起一种“自然观照、物我合一”的审美价值系统,从而摆脱美丑、善恶以及生死、是非等种种对立,享受与天地同一的超越之情。喜欢和巢湖、淮河单独在一起的许辉显然深谙此道,一方面通过对天地万物的无限可能性的描写与揭示,获得一种切实有效的生命感,并显出“我”在无数个生命世界中仅是一个渺小存在;另一方面,在赞叹湖水之广阔、花香之无限时,把自己融入“天地之大美”之中,成为一个“赤裸的我、本真的我、天地的我”,一个忘却自我、抛弃现实功利、从天地之大美中获得“真美”和“纯美”的“智者”。这个过程,用冯友兰的话来说,就是从“功利境界”向“天地境界”攀援,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就是从“悦耳悦目”走向“悦心悦意”“悦神悦志”。
当然,许辉也是有“仁者之心”的。在他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有它的进化节奏和独特性”,那些打鱼的种菜的夫妇、那些不为人知的人生,同样是值得关注和尊敬的,更何况这种在山水自然间求安放的心境的获得,其实也是导源于其修养自我道德精神的儒家内功。
在读《人人都爱在水边》的时候,我不免习惯性地想到屠格涅夫、梭罗,想到沈从文说“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较大的关系”,想到朱光潜说“站在后台看人生”,诸如此类。转念一想,比较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每个作家就和每种人生一样,都是独特而惟一的,许辉的“湖湾”是独特惟一的,沈从文的“湘西”、梭罗的“瓦尔登湖”也是独特惟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独特惟一”就是成功。然而,许辉又似乎并不看重这种成功。“人有时间、有精力、有情绪、有心境,在水边走一走,自愿地晒晒太阳,只能说是人生的一种成功,而不能说是人生的一种失败。能够支配自己的人生,还不就是一种成功?”毫无疑问,许辉更为看重并已然获得了这种支配自己人生的成功,这是智者的“成功学”,是人人慕求的一种境界、一种“生态美学”。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