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似断非断的时刻——评王咸《去海拉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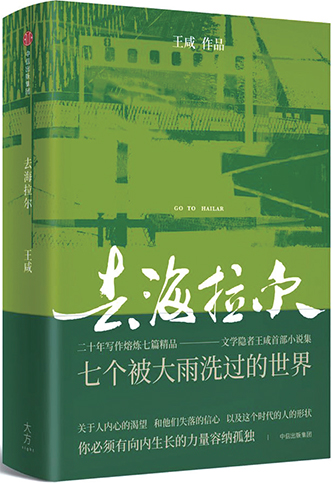
王咸在小说集《去海拉尔》中摘下了短篇小说戏剧性的翅膀,他回避了现代主义文学在技术上留给小说的遗产,将日常生活视为小说的全部对象。于是,身体的污垢、灵魂的伤口与岁月的盐,在《去海拉尔》之中凝为了一体。
这是一步险棋。不夸张地说,短篇小说至少有一半魅力是由想象力与戏剧性提供的。然而王咸选择压抑小说中戏剧性因素的发育,松开小说紧绷的结构,展平在小说中被压缩变形的时间,真刀真枪地来。于是,小说的叙事时间放缓了,缓慢地近乎日常时间的流逝,人物也从奇形怪状的面目变回了平凡的模样。小说从一种矢量艺术恢复为不可变易的位图艺术。
从日常生活中提取诗意,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存在”本来就是十分困难的,何况是在变幻莫测的当代。当代中国的小说家善于在日常中看到频出的奇景与怪象,但不善于发现恒常的朴素诗意。王咸反其道而行之,以无为的姿态,抓住了“万变不离其宗”的“宗”,也就是日常生活的延续性。当小说家以为延续的日常是无聊的、非小说性的时候,他用7个故事更正了这一偏见。
小说没有一个故事在表面上是惊心动魄的,但王咸化腐朽为神奇的方式是在每个故事当中都埋进了一颗“子弹”:《回乡记》里儿子小原的隐疾、《邻居》里郭大哥的肺癌、《相见欢》里诗人好友的早逝、《去海拉尔》里地上的斑斑血迹、《去买一瓶消毒水》当中的杀人事件……总之,是一种意外、灾祸、危机的象征性存在,一种破坏性的戏剧性力量,一种引诱小说变形的非日常因素,一颗悲剧性的种子。
王咸从头到尾都在极力抑制着这颗种子的生长,他的方式是让自己的主人公“忍着”。在《盲道》中,这颗种子刚刚萌芽,它挠着“我”和妻子的无意识深处,引起了我们对文学青年小安的厌恶。《回乡记》中,因为孩子的病是悲剧性的,布满死亡阴影的存在,所以一定要用喜剧性的、无聊的、枝丫横生的日常对话压住。日常对话越单调越平静,悲剧性因素的心跳声就越清楚。这种日常与非日常之间的摩擦,刀子一样深刻着我们的心弦。要断了,要断了,我们为此不住地提心吊胆。但就在似断非断的那刻,王咸笔锋一转,让故事平淡地结束了。《邻居》最后没有交代郭大哥病情如何,而是以郭大哥给“我”和妻子送来枣子结尾:“红枣非常甜,阿米说,还是北方的枣像枣。”生活中的苦涩够多了,他不想让小说也那么郁郁寡欢。
但王咸似乎也意识到了,“子弹”一旦射入人的体内,总会炸响。因此,越到最后几篇小说,这颗顽强的悲剧性种子越难被隐藏。《去买一瓶消毒水》中,这颗种子破土而出。主人公杜原目睹了血,看到了杀人的现场。但王咸以令人意外的方式化解了小说当中的恐怖:“杜原看着眼前上演的皮影戏,过了很久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样虚写一笔,让杀人的现场在主人公的眼中变得虚实难辨,如同幻梦。
从《去海拉尔》开始,类似的虚笔就出现了:“我”在单位大院里看到了凌霄花,走近再看,却发现不过是斑斑血迹。《拍卖会》的结尾,我如愿以偿得到了想要的木箱子,回家之后才发现箱内空空如也。这一个个细小的幻觉,如同多米诺骨牌中突然倒下的那一张,转瞬间摧毁了整个故事的稳定性。小说家在读者身上苦苦栽培的对于故事的信任,被王咸轻而易举地放弃了。王咸想要达到的显然不是所谓的“震惊美学”,他看透了生活千百年来所恪守的遗忘原则,这种遗忘是一种潜藏在每个人心底的秩序的力。这秩序的力能熨平生活当中一切小概率的褶皱,直至将褶皱点化为子虚乌有的幻觉。
对于王咸的小说,我们要有跳出这些细节的视野。只有在这个高于日常细节的视野当中,我们才能看到这些虚实恍惚的、不可把握的表达,构成了某种整体性的不可言说的意义,这就是“恍兮惚兮,其中有象”。这无形的“象”,也许是人生的幻灭感与时代迅速衰亡的变幻感,在渺小个体的内部引起的回声。这回声无影无踪,却久久不散。
王咸有意让自己的故事保持在一切如常中,保持在某个“云深不知处”的地方。因为在他看来,文学不过是一场游戏,一个叫做“虚空”的靶子。这“虚空”正好可以替代“真实”的生活承受来自子弹的伤害——让子弹停留在故事的肉体里,现实生活中的肉体就可以安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