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馋是一枝花》(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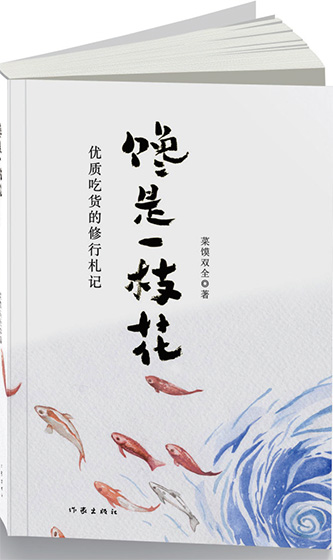
《馋是一枝花》简介
禅是一枝花,馋亦是一枝花。
本书共分五辑。
故乡吃不尽:起点。解读生命中最初的味蕾密码,一起潜入回不去的童年。
美味在路上:旅途。或孑孓独行,或呼朋唤友,看风景,饮美酒,但有青春做伴,快意与豪情不散。
101场饭局:盛宴。曲会终,人已散,那些有趣的朋友和温暖的情谊总会浮现眼前。
孤独美食家:品味。美食家都是孤独的,他们的舌头太敏感,他们的胃太超前。
吃货的哲学:思考。一食一餐皆有感悟,人生的所有道理都藏在饭里。
谁的童年不“有机”?
入夏时,我在“豆瓣阅读”发表了一组短文章,取名“偷吃”,写的是儿时趣事。序言里,我把自己弄得很惆怅:“那时候河里还有清澈的水,以及活蹦乱跳的鱼,我们经常溜进人家的瓜地,爬上人家的果树,寻摸各种美味,所有的食物都甘之若饴,人们很少使用农药,我的记忆因而全是有机的。”
有机的——这不是胡说。
村西的河叫箕山河。待入夏,河水涨起来,河面异常开阔,那时候水清,清得几乎可以看到河底,水草在阳光的照射下异常碧绿清透,随着河水轻轻摇摆。
两岸的芦苇荡,绿油油地往上冒,直到没了人头,风一吹,簌簌声没完没了,里面不时传来或尖厉或悠长的鸟鸣。有种叫不上名字的鸟儿,飞速极快,一个俯冲扎到芦苇里就再也看不见影踪。
光屁股的小孩子,排着队站在桥上挨个儿往水里跳,一个个猛子扎下去,“扑通扑通”,跟下饺子似的,溅起一簇簇大水花,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几分钟后,才见从远处露出头,大口喘着粗气,有人手里还举着一条鱼。那鱼来回挣扎,终于折腾累,见没有逃脱的可能,只得乖乖就范,到岸上,顺手把它丢进备好的水桶里。
小孩子跟水最有缘分,一玩就是老半天。等彻底玩累玩饿,才依依不舍上岸,那些抓到的鱼儿,就成了我们口中的美味。
通常的做法是烤。大家分头捡些干树枝,点火,用报纸将鱼层层包起来,弄湿,丢进火里,过一刻钟,便闻到烤鱼的香气,大家一起分而食之。哪个逮的鱼多,就拥有向众人分鱼的权力。获得分鱼权的小伙伴,满脸骄傲没话说,跟部落酋长一般神气。
烤不完的鱼,大伙儿分了,回家交给大人,做鱼汤喝。
河里的鱼,品类繁多,草鱼、花鱼、鲢鱼、青鱼,等等,有大有小,小的拃把长,大的足足有十几二十斤。小孩子面对大鱼时,基本不敢靠近,只能躲着游。但凡有些胆儿肥的,想要抓条大鱼,要么被鱼咬一下,要么一尾巴甩身上,被甩的地方瞬间红成一片,生疼生疼。
有一种被家乡人称为“硌轧”的鱼儿,万万不能靠近,它身上有尖尖的刺,分分钟扎得你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每个夏天都有小伙伴被扎,我们对这硌轧恨之入骨。
某次和几个小伙伴在水里扑腾,突然见条大鱼,足足半米多长,左冲右突,凶猛异常,吓得我们赶紧上岸,生怕被它拖走吃掉。
河里有太多好东西,最常见的是河蚌,它们藏在水底污泥里。抓河蚌最容易,先用脚踩准它的位置,然后沉水,两只手抓住它,用力一抠,就出来了。刚抓的河蚌,紧闭双壳,有装死的意思,偏偏有残忍的小朋友,拿树枝硬插进它壳里,掰开,扔在河边。经太阳一晒,又腥又臭。
事实上,河蚌肉质肥美,营养丰富,苦在不好处理,它腥味重,方法不当会叫人大倒胃口。所以,小朋友抓河蚌,大多只为要它的壳玩。
对小朋友来说,有水处皆为好玩之地,不只是河,还有小溪、水渠等。有次和父母走亲戚,回家途中遇见路边小溪,闹着要洗把脸凉快会儿,到溪边一看,才惊呆,那清亮的溪水中竟有好多田螺,随便抓了一袋子回家,用清水洗净,直接上锅用白水煮,不加任何佐料,尝一下,Q劲十足,肉质清香,还有浅淡的甜。
童年生活的美好所在是,不用去集市,也不用自己养殖,直接去向河里抓,跟自然索取,一样可以吃到美味。童年解馋,几乎全靠自己。
有时总怀疑,我是否过度美化了童年,真的有那么幸福吗?真的有那么快乐吗?真的有那么开心吗?
沉思之后,只好说,真的。
读初中后,箕山河一天天变脏,县城化工厂的污水,令鱼虾再无回归可能。童年的美味,就这样说了再见。
想想,现在村里的娃儿也真可怜,没在河里游过泳,没下水里逮过鱼……没有那些本应该属于童年的生活乐趣。
他们算什么农村娃。
这世界上的许多真理,都掌握在吃货手里
翻翻中国文化史,冷不丁发现一个道理,“吃得越好,贡献越大”。
菜馍君仔细推敲了一下,逻辑大约是这样的:吃饱穿暖,才有精力干活,诗词歌赋、著书立说,礼啊乐啊这一套,说到底是有闲有钱的人鼓捣出来的。
吃得越好,证明越有钱,对文化的贡献便越大。
有人反对,你胡说八道。
曹雪芹流落香山了,不照样写《红楼梦》?
曹雪芹不能叫穷,人家好歹是落魄的贵族。即便曹氏惨到被抄家,曹雪芹还有个王爷亲戚好嘛,表哥是平郡王福彭,姑妈是福彭的亲妈,有这门亲戚怕神马?即便平郡王败落,曹雪芹流落香山,身边还是有几个资助人啊。
菜馍君还发现另一个道理:越能吃,越会吃,连讲个道理都用吃打比方的,就越受人民群众欢迎。
今儿要说的,就是能吃会吃又爱用吃打比方的两个顶级吃货。若缺了他们,中国文化就太无趣了。
老子活了100多岁,也有说200多岁的,反正很长寿就是了。
电视上经常有记者采访长寿老人,一成不变的话题是,“平时都吃些什么?有什么养生秘诀?”
要追究老子吃什么,实在难为了咱们,不过还是有一点蛛丝马迹。比如他那句著名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暗藏着他曾食用过“小鲜”的信息,小鲜是什么,有人说是小鱼,有人说是小虾,也可能是小蚂蚱什么的,我估计他常吃小鲜,按此推理下去,他家附近可能有个池塘,或者有个售鱼虾的菜市场。
老子是图书馆馆长,算拿俸禄的公职人员,估计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比平民百姓的生活条件还是高出几个档次的,吃几回小鱼小虾也正常。
鲁迅在《出关》里讲到老子西出函谷关,关令尹喜送给他“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想来也不是瞎写,倒是符合老子倡导的简单朴素之生活作风。胡麻就是黑芝麻,估计是和盐混在一起捣碎了蘸着饽饽吃,菜馍君小时候,老家的人们在缺菜季节就吃这个,取名“芝麻油盐”。
老子饮食,想必是个极有原则的人,讲究也不少。
他特别强调,无味才是真味,山珍海味神马的,没必要天天吃,也没必要多吃。我就猜,老人家年轻时一定吃过不少山珍海味,一直吃到伤胃,既有这般深刻教训,才可能云淡风轻地写出“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这种饱含哲理意味的句子。
想想看,一个从未吃过鱼翅的人,天天跟别人抱怨鱼翅很难吃,有说服力吗?
怕年轻人不听他劝,又特别强调,“五味令人口爽”,山珍海味吃太多,最终会坏胃口,得胃病,进医院,很痛苦。So……你们看着办。
注意,老子是说不要多吃,但不等于说不吃。
老子还是养生家,讲究饮食适度,切忌暴饮暴食,都很符合现代的健康理念,他说“为腹不为目”,吃饱即可,不必贪多,如果看到的都想吃,那就坏了。
孔夫子是个有意思的人,学生交不起学费,那就送十条干肉吧。为嘛是干肉,因为那会儿冷链不发达,鲜肉不禁放。我估计,夫子家里的干肉一年到头吃不完,怎么办?
以他悲天悯人的个性,怕又要拿出来分给学生和邻居呗。
夫子吃肉有严格的标准,即所谓“八不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这个标准,大可以挪到时下,颇有点健康饮食理念的意思。
臭鱼臭肉,腐烂变质,当然是不能吃的,大概是当时经常发生食用臭鱼臭肉的情况,老人家才提出这样的警告。特别是夏天,鱼或肉放小半天就会变味儿,很多人家舍不得扔,引发了肠胃炎或其他病症。
难看的不吃,难闻的不吃,过生过熟的不吃,不是当季的不吃。
至于割不正,大多数人都以为是刀工不好,将肉割得歪歪斜斜。这可能搞错了夫子的本义,这里的“割不正”,很可能是不按当时的规矩切割,而增加了动物的痛苦,这样的肉也就不能吃了。
说到菜馍君的心坎里去了。
赵元任先生的夫人杨步伟曾批评夫子,“他只吃方方正正的肉,那谁吃他割下来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这实在是对“割不正”的误解。
夫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表面上理解,似乎是食物越精致越好,肉切得越细越好,个人觉得,这是老人家的营养学,食物精致,肉丝细溜,都有助于消化和吸收。
在夫子那个时代,中国人还没有开始喝茶,除了运动也无其他的助消化方法,所以,食物的精细是很有必要的了。
对食物要求越严格,各种病毒就越无机可乘。想想夫子能在战争频仍、缺衣少食的生活状态里活到73岁的高寿,“八不吃”自然功不可没。
八不吃之外,他还讲究肉食和粗粮的搭配,他强调说,餐桌上肉再多,但所吃不能超过主食之数量,肉吃多了不好消化嘛。
倒是对喝酒,夫子并无严格限制,且希望大家喝到尽兴,但尽量不要喝醉就行了。想来老人家的酒量还是不错的,身边那么多学生,一人敬他一杯,足够他喝一壶了,但很少听说他醉过。
饮食有标准,吃饭讲礼仪。
夫子说,“食不语”,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即便吃的粗茶淡饭,开饭前也要祭一祭祖先或鬼神。
在他看来,这是基本礼仪,是必须遵守的日常行为准则。
别看他对食物如此重视,他所喜欢的生活态度却都是简单质朴的——比如“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就被他拿来大加赞赏。
那他讨厌什么?
当然是“耻恶衣恶食者”,在老人家眼里,一味追求生活享受的人,是没资格做学问讲道德的。
(摘自《馋是一枝花》,菜馍双全著,2017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