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我为何选择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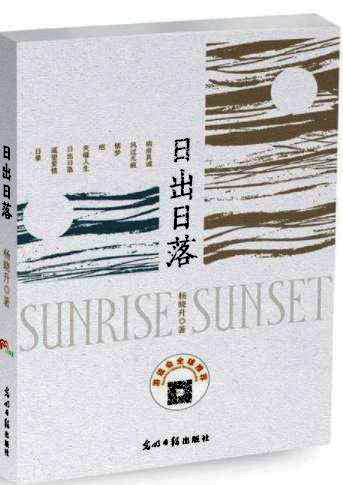
这些年,不少朋友见到我,都会好奇地问:你大学学的是理科,怎么从事起文学创作?
没错,我大学学的是理科,但那算得上是人生的一场误会。
从上学开始,我就很喜欢语文课,也热爱写作,作文还时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里宣读。及至中学,作文就更加突出,不仅时常被老师讲课时作为范文,还被抄写到学校的黑板报上,以至后来我也顺理成章成为学校黑板报的主笔和主编。学生时代最风光的一次,是全县范围的高中语文汇考,我的作文和语文成绩全县第一,这无疑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语文、进而对文学的热爱。我的理想是上大学中文系。然而,那时候“文革”刚刚过去。一方面,文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和命运仍让大多数人心有余悸,父母和老师都不希望我考文科;另一方面,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不差,这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口号深入人心的年代,考文科成了考生万不得已的选择。如此,家长和老师自然是不主张我去考什么大学中文系的。
就这样,我“随波逐流”,高考时报考了理科,并于1980年考上了位于武汉的华中师范学院生物系。奇怪的是,那一年我的高考志愿既没有填报这所学校,也没有填报生物专业,便稀里糊涂被录取了。事后究其原因,我是在报考院校的最后一栏填写了“服从分配”。收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我既高兴又郁闷,高兴的是自己终于考上了大学,郁闷的是录取结果非我所愿。我内心抵触、拒绝,想复读重考,家境却不允许,因为我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在读,当乡村教师的父母工薪微薄,难以支撑我复读。我只得认命。
上了大学,素来学习认真的我虽然也按部就班地钻研起生物学,内心却念念不忘自己喜爱的文学,而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正好满足了我的兴趣和愿望。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有机会广泛涉猎、阅读中外名著,左拉、司汤达、海明威、莫泊桑、欧·亨利、杰克·伦敦、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等一系列中外优秀作家的作品像涓涓细流进入我的视野,滋润着我的心灵。读多了,我也跃跃欲试,课余时间偷偷学着写作,并于大学一年级的寒假向校报投寄了自己的散文习作《拜年》,不料校报几乎一字不改地发表了,这无疑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除了努力完成生物专业规定的课程任务,我的课余时间基本用在了文学的阅读和写作的练习上,并先后在校办的大学生文学刊物《摇篮》发表了《最宝贵的》《七月流火》《归宿》三篇小说,我由此还成为《摇篮》的编委,同时还成为生物系学生会宣传部长。也正因为大学时光这段看似不起眼的经历,才使我大学毕业时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1984年5月,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到武汉地区高校挑选两位应届毕业生,一位文科一位理科,这个理科生的机会便降临到我头上,该刊前来考察的副总编王文起和资深编辑夏岱岱,在看了我发表的几篇习作之后当即拍板,想录取我,但他们担心我是否同意到北京工作,希望学校与我联系。其时,我正随生物专业的老师在咸宁地区的鸡公山作野外生态调查,准备写毕业论文。通讯落后的年代,学校的老师自然无法联系上我,时任学校团委书记兼《摇篮》主编的唐昌宪老师却自告奋勇,拍着胸脯替我作主:“你们放心定下来吧,这么好的机会,杨晓升肯定愿意。”
就这样,塞翁失马,大学学生物的我阴差阳错来到首都北京,当上了《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和记者。要知道,《中国青年》是中国大陆现存创刊最早、历史最悠久的杂志,创刊于1923年10月,首任主编恽代英、肖楚女,他俩都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者;要知道,《中国青年》历史上推出过雷锋、邢燕子、向秀丽、王杰、张海迪等一系列英模人物,声名鹊起,是青年的一面旗帜;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青年》,刚刚因为潘晓一封“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来信引发全国范围的问题大讨论而正大红大紫,每期发行量达到了400余万册,能够有幸成为这家知名杂志的编辑和记者,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到《中国青年》当编辑记者,既让我刚一毕业就“背叛”了生物专业,也让我一开始就干起了自己喜爱的文字工作,这既是我专业的重大转折,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这次转折,让我有幸为自己做了迄今自认为正确的人生定位。编辑和采访工作之余,我业余时间开始写小说,收入这本集子的短篇小说《真诚》,发表于《作品》1987年第5期,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发表作品,也就是说,《真诚》是我真正的小说处女作,责任编辑是时任《作品》副主编的廖琪。此后我连续在《作品》《萌芽》《湖南文学》《芳草》《草原》《长江文艺》等发表小说,大约有二三十万字。与此同时,由于工作的原因,为《中国青年》作深度报道所采访的素材,时常被我充分利用、深度开掘,写成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拷问中国教育》《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等先后出版。6万字的中篇报告文学《21世纪,巨龙靠什么腾飞——中国科技忧思录》发表于《北京文学》1998年第2期头条,很快被创刊不久的《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多年之后还被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评为新中国60周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为此我也与《北京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2000年,经当时的《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她也是我那篇报告文学的责任编辑)引荐,由北京市文联考察并报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批准,我于当年10月从《中国青年》调入《北京文学》任执行主编,负责《北京文学》的编辑工作,并开始主持《北京文学》的改版和改革。从《中国青年》调到《北京文学》,领第一个月工资时我才发现,我的月收入一下减少了一半,从原单位的4000余元减少到2000余元。这还不算,没过多久,某个月快到发工资的时间,漂亮的女财务愁眉苦脸透露:社里的账户都快没钱发工资了……尽管如此,我听后也只是愣了一下,一笑置之,很快又埋头钻进稿堆之中。自此以后,日复一日,我自得其乐,且乐在其中。记得我还将当时的感触写成随笔《人生的级别》,发表在2000年10月15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我在文章中这样写——
我所要去任职的单位,是一家文学杂志。如果按照世俗的标准,我真的是够傻帽儿、够落伍的了,因为这家文学杂志,尽管在文学界举足轻重、影响力仍在,品牌仍在,但却像其他许多的兄弟文学杂志一样,发行量不大,经济窘迫。但在我看来,文学杂志的窘迫,不等于文学的窘迫,更不等于文学生命力的丧失……所以对于个人而言,重要的不在于你选择的领域怎么样,而在于你选择之后怎么做。
之所以选择看似清贫的文学杂志,缘于我对文学一直以来的兴趣,也缘于我对当今文学现状和文学读者市场的分析判断,更缘于对自身潜力的认知和对未来发展的打算。对于我所选择的这家文学杂志,我清楚地看到了它潜在的发展空间,更清楚地看到了我自身的用武之地。
在我看来,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不在于你单位的高收入和高级别,也不在于你轻而易举地拥有荣华富贵,更不在于不劳而获、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为你创造的优渥人生。最为重要的,在于你在生命过程中能身心愉快地劳动、付出与创造。
当你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事业,在一个相对宽阔的舞台上最大限度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最大限度地挖掘着自身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并能时常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愉悦与快乐的时候,你难道还会去理会自身的级别和收入?你难道还会去理会什么贫贱富贵?
——这样的人生,难道不就是最高级别的人生吗?!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是中国大陆作家首获这个历史悠久、享誉世界的奖项,此事一时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热点,就连平时不关心文学的人也议论起莫言的获奖。某天我在电梯里听到两位陌生人的议论,一个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听说奖金很高啊!”另一位听罢皱了皱眉,说:“嗯,是不少。可这奖金也就能在北京三环以里买一套两居室吧,还只能是二手房!”他俩的议论让我陷入了沉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学又是文化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难道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吗?进而,我冒出一个不错的策划。2013年第1期开始,我在《北京文学》发起了以“寻找文学的意义”为主题的大众文化问题讨论,每期开辟专版选登各界读者的优秀来稿,讨论一直持续到年底,大家畅所欲言,从不同角度、以自身的经历和理解发表了对文学意义的看法。讨论结束时,有读者问我:你自己如何理解文学的意义。我想了想,在新浪微博公开作了如下归纳——
1.文学是倾诉与表达思想情感的最佳方式;2.文学能让你一定程度获得心灵的自由与自尊;3.文学创造艺术精神财富的同时能让你留下生命的文字印记;4.文学能最大限度延长你的事业寿命直到生命终结;5.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为读者提供美的享受与思想的启迪。
当然,以上5点,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的。想当初我调到《北京文学》,除了自己对文学的喜爱,以为《北京文学》的工作可能会轻松些、自由些,工作氛围也可能更有利于我自己的写作。然而事与愿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工作不仅一点不轻松,相反是越来越忙了。2016年第3期的《作家通讯》发表了我的《文学编辑:说不尽的辛苦,谈不完的快乐》一文,文中我这样写道:“……面对日月轮回,面对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一期期出版的报刊,编辑更像是一轮轮、一圈圈推磨的毛驴,周而复始,没完没了,或许只有改行或一直干到退休,才有可能得以歇息。”但同时,我也写道:“编辑也有编辑的乐趣。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年终回首,白纸黑字,飞红流黄,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那一期期的杂志,那一篇篇文章,那一个个作者,那一群群读者,此刻纷纷闪现在你的眼前,或飘着墨香,或精彩纷呈,或喜笑颜开,或欢呼雀跃……活脱脱又一个庆丰年……编辑工作,还使我们有幸不分地域、不分行业地结识原本素不相识的一茬茬作者,一群群读者,一批批朋友,这些作者和读者朋友,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大江南北。每逢节假日,问候的短信雪片般纷飞而来,接连不断,吱吱喳喳,几乎要将手机挤爆。出差的时候,无论走到哪个省份,我几乎都可以找到作者或读者朋友。……每每此时,我常常感动、欣慰。每每此时,我看到了编辑工作的价值,感受到了编辑生涯的乐趣,也享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人生的快乐。”
一晃数十年过去,如今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职业编辑,业余写作。尤其是近几年,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我仍努力挤出时间,断断续续地写,虽然写得很慢,但每年也保持写两个中篇小说的速度,并且所写的小说也都发表了,有的还被选刊、报纸转载或连载。从时间上看,这本《日出日落》算得上我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虽然中短篇小说集《身不由己》已由作家出版社同步出版,所收入的作品也并不重复,但是从作品的构成上看,《日出日落》所收入的作品,时间跨度大,作品发表的时间也大都较早,最早的是我的小说处女作《真诚》,最新的是2017年初发表的中篇《病房》。正因为时间跨度大,这部集子收入的9篇小说,风格各异,视角、题材、内容都不尽相同,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无论从技巧还是从思想深度上讲,有的可能还不尽成熟,但都留着我数十年来小说创作的足印,而且都异常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