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娆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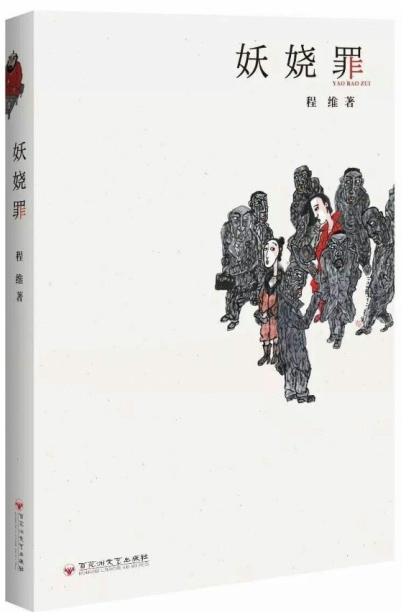
《妖娆罪》
作者:程维 著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9月
作品简介
《妖娆罪》是中国当代“十佳诗人”、“新古典主义诗歌”代表人物程维暌违十年的新作。此书的出版既集结了作者新时期诗歌创作的精品佳作,也重新定义了程维丰富而迷人的诗歌表达——在文学想象的辽阔疆域里,重构生活、重述神话、重建现实,成为不受尘世束缚的伟大灵魂!
《妖娆罪》中的诗作,即便精短,亦内容开阔而深邃,拥有寻常诗歌少有的细节元素与色彩斑驳的奇妙画面感,包含了诸多意味。尤其可贵的是程维的诗歌语言已突破书面语与口语诗歌创作的画地为牢,“不计口语、意象、雕饰,尽量返璞归真,凡词语皆为我用。大开户牖,放山河入我襟怀;泥沙俱下,便见黄河雄浑;不故作高深,就直见性情”。如此一册诗集,更见汉语妖娆。

作者简介
程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昌文人书画院院长。著有长篇小说《海昏:王的自述》《皇帝不在的秋天》《戈乱》《双皇》、散文集《画个人》《南昌人》《水墨青云谱》《独自凭栏》《沉重的逍遥》《书院春秋》《豫章遗韵》、诗集《他风景》《古典中国》《纸上美人》等,作品被译为英、法、日、塞尔维亚等文字,应邀出席第42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作家会议。获中国作协第八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好图书奖,第一、三、五届江西省谷雨文学奖,第二届江西文艺成果奖,第二届陈香梅文化奖,首届滕王阁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天问诗歌奖,中国地域诗歌奖等。早年从事绘画,得名师指点,近年以“新写意人物画”系列受到广泛关注,《中国书画周刊》《艺术中国》《收藏天地》等百余种报刊以专版专访推介其画作,英国伯明翰大学、香港艺术馆、日本岐阜大学艺术馆、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艺术中心及海内外收藏家收藏其画作。
卷一
上帝的旅行箱
(2015年诗选)
天神醉了
雪山在天空飞翔
要去追赶穿红袍的神,把飞机甩在后面
我从舷窗朝它打个招呼,快到江西地界了
它仍端着火红的酒坛,要扯住神的大袖
一起降到梅岭的山头来共饮
我看见西边彩霞满天,一定是天神醉了
要倒在西山酣睡,雪山早变成了薄锦,虚掩在它身上
从昌北机场出来,我也带着酒劲
浴仙记
昨天黄昏,我试图到赣江游泳
被水中的鱼咬了一口,我赶紧上岸
天边的云已脱光了衣衫
扑通一声跳下了水,圆滚滚的乳房
使江水涨了三寸
令我犹豫不决的是,我是再次下水
还是跑到天边,去偷走她的衣衫
西 山
落日朝西山去了,新建县一带
一片辉煌,仿佛天堂失火,燃着了西山
等待神仙前来扑救
又像许真君得道,鸡犬升天
一个仆人从镇上赶回来,边跑边喊主人把他捎上
他脚跟离地
如同一只塑料袋刮到了天堂
后 记
这些诗,大部分是这一两年的产物,我却仿佛写了一生,是我一生心灵的记录。
——这是我最好的诗篇,这是我最差的诗篇。时间将证明:如果我是一位好的诗人,它们就是好诗;如果我是一个差的诗人,它们连诗都不是。而我是要编一部在今后的岁月中不至于让我脸红并惭愧的诗集。
我是将内心当作白纸写下每一行诗,这是我虔诚面对上苍的写作,上苍有眼,它使我的肉身更紧贴于大地。
大地在我已不再虚妄,正如天空是我必须面对的检视我良知与灵魂的大神,而大地是山川草木与众生,更是我立足与容身的地方——是我的脚步所到之处,是我行走、站立、坐下、躺着与起来的地方。而这——更多是在我的故乡南昌,是近年我居住的沙井——我在这里思考并写作。
这些年我甚至少有涉足城区了,我所指的城区,是赣江南岸南昌老城——我在那里生活了四十余年,现在的居所与出入之地乃赣江北岸新城,与故城一水之隔,人却步入半生之后。由此而始,我也似乎有了更多清静时候,仿佛与已往的热闹、拥堵,与喧嚣的生活发生了抽离——从此岸到彼岸,变得意味深长。
我知道这是一种告别,也是一种更新。我的写作也起了变化,我写下的每一部长篇乃至每一篇诗行,都是一种告别,也是一种更新。明乎此,我反而有了些许的从容与清醒,我要将自己的写作与过去分别开来。我要让每一日变得合乎自然,让每一次写作变得在时间中更有效,这就是让它合乎万物生长之律与天人合一之道,而不拘泥于小术。这些诗,也就从内心生长而出。它属于阳光、雨水,也属于黑夜与雾霾。它生长出来,只是选择了我的大脑和身体。对于诗而言,不存在个人的才华,而存在什么样的诗,选择由什么样的人来写出。如果这些诗是微不足道的,其人也微不足道。如果这些诗是杰出的,自然写它的人也唾手可得一个杰出诗人之名,这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我这些诗写出来的过程都不太难,我二十年前在一家刊物上提出的“难度写作”似乎荡然无存,与手上写作的长篇小说相比——很少写作者正视长篇的体积所要求的更多繁复的技巧与元气淋漓的饱满状态及结构能力,一个真正的长篇足以穷尽一个作家之能。诗相对于我所认为的长篇写作,令我恍然产生了轻而易举之感——这无疑是一种自我虚拟的假象——此前我已畏敌如虎般进行了数十年诗歌写作的严格训练,诗作已发遍了大大小小的刊物,赢得了一些过早的薄名。我停顿十余年之后再度写诗,就是要将自己的写作与一度的“薄名”切割,回归一种面对上苍与内心交代的无名状态的写作。这种无名状态的写作,因无功利之累,便也看似轻松,但当我每一次复读这些诗,都感到其如同天体般与万物的紧密联接,是无法轻易用一个词来判定的。我感到它合乎万物生长之律,而不是相反。如果你的写作违反了万物之律,它必然纠结万般,会陷于物是人非的泥沼。我必须说明的是,当一个写作时期开始之前,我已停笔十余年没有写诗了。那是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一种迁徙,从赣江之南迁到赣江以北,从写诗迁移至长篇小说,当然我的长篇小说在赣江以南就已开始写作并且已经出版,而诗的转折与再度进入是在赣江北岸,且密集地发生在我写作长篇与不停绘事的同时,它们抢着生长,并呱呱落地。我是惊喜而惶惑的,但我明白我做了什么。
我头顶天堂,匍匐在神灵的土地上,为这些诗篇接生,如此而已。
如果这是一个大师的时代,或许大师已先我而诞生,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对于大师的练习。此外,我必须感恩于天地万物,其神形完备,让我存活并写作,感恩父母亲人与每一口粮食与书页。同时感谢我引以为一生的知友姚雪雪,这位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美丽的女船长,我们经历过诗歌的黄金年代,并为其余响而存留着一颗诗心,感谢她作为一位诗人、杰出散文作家与出版人出版这部诗集《妖娆罪》——让诗再度妖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