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锋”到“锐利”——评陈希我新作《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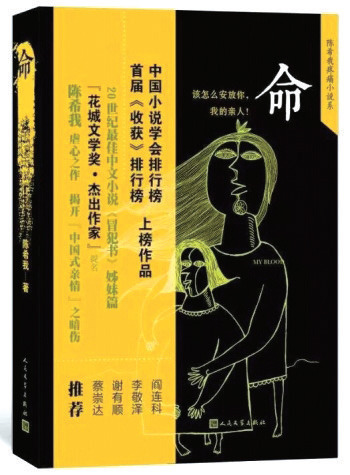
不少人觉得陈希我呈现在《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中的写作完全变了,特别是当《冒犯书》再版,两部集子拿来一对比,突然发现他蜕变成了一个“亲情作家”。这是作家本人学乖了吗?还是曾经的极端狠辣最终被岁月化为了一腔柔情?《命》中发生的事,是儿子找父亲的事(《父》),是父母送孩子出国的事(《家》),是要不要生二胎的事(《子》),是小屁孩保卫宠物的事(《宠》)。它们看上去都不再和“性”有关,反而染上了十足的烟火气,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絮絮叨叨地过起生活来了。果真如此吗?
似乎并不是。我注意在新书的宣传语上,陈希我“先锋作家”的身份仍然赫赫在列,在这个“后先锋”时代,一个写作了30多年,积累了百万字的作品,已到知天命之年的作家仍然被冠以“先锋”头衔,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纵观近年来引领文学潮流的作品,无外乎两个特征:一、题材上紧追“现实主义”的标准,二、叙事上紧跟史诗化、宏大化的风格。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这个东西素来是有情结的,把握历史,把握当下,展现人的精神,思考人的命运。这不仅是中国作家的远大抱负,似乎也是全世界所有作家的共同目标。但并不能说陈希我的先锋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因为他坚持认为所有的作品最终都应该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对人的境况的书写,就是一种根本上的基于现实的写作。
20世纪对虚构作品写作路数上的扩宽,变形也好,意识流也罢,魔幻现实主义也好,现代派也罢,如其核心没有对现实的观照、对人类生存的拷问,仅为路数而路数,为方法论而方法论,那么这种脱离了根本目的的写作就应该宣告失败。所以他笔下的“现实”,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不同,他关注的是内在的现实,即人的内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必须使用意识流、意象法或其他什么叙事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其实从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作家们对西方文学中的先锋元素也是津津乐道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向往和沿袭变成了一种创作主流。这些年来,虽然这股曾经的狂潮不再,但作家们写作,对技巧的追求已然慢慢化为一种自觉,基本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做到完全不受影响,但在《命》中,这种影响却几乎没有被明确地表现出来。作者绝大部分的小说语言其实是非常日常的,题材也十分琐碎,这或许与他长期亲近日本文学有关。陈希我小说的文本本身,并不是典型的先锋文本,他的先锋,或者换个更明白的词,叫“锐利”,是体现在其文本的价值层面上的,而在这一层面上,他追求的又是一种绝对的现实主义。那么这就势必会与传统意义上的“先锋派”和“现实主义”同时发生分歧,文本层面上的日常与意义层面上的先锋同时背叛了主流文坛价值观所能认可的“文本层面上的先锋和意义层面上的现实”,让作品产生疏离感。
至于对“史诗”的迷恋、对宏大叙事的追求,乃至对作品体量的迷信,这种潜藏在行内的普遍心态更是多年来左右着文字的产出和效益。但陈希我却固执地钟情于对“小单位”人伦关系的书写,比如男女、父子、母女等等。《命》中的所有小说,人物关系再复杂都不会超过一个家的范畴,对小范围内的个体生存的关注可以说是他写作永远的出发点,关系越是简单,越是一对一,越是封闭,小说的价值就确实丰厚,越是纯粹,越是深刻。大多数的作家是喜欢在长篇里把故事铺开来写,而陈希我却喜欢把小说“榨”出来写,尽可能去掉不必要的枝蔓,即便是长篇,仍然拥有结实的主体结构和高浓度的情感表达。“人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人的生活是充满黑暗的”,这种脆弱和黑暗,必须用非常小的切口来呈现,用非常扎实的文本来揭露,这或许就是其自觉远离“史诗写作”的原因吧。归根到底,使用什么样的题材、语言,塑造什么样的文本风格,与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是直接相关的,“写什么”是一个源头性的问题。
从写作的根源上出发,陈希我的“先锋”和文坛约定俗成的“先锋”就是错位的,而他的“现实”与主流价值观所追求的“现实”也是相悖的。他的另类,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另类,很难改变。


